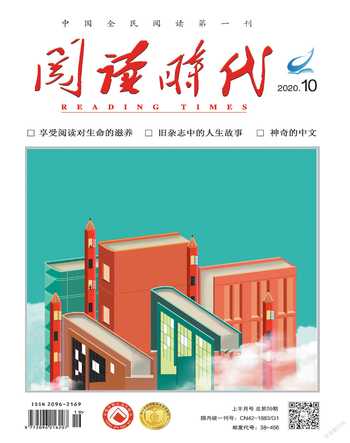馮驥才的枕邊書
宋莊

馮驥才的屋子里到處都是書,臨時想看的都放在了枕邊。常年放在枕邊的幾本書,有唐詩宋詞和唐宋八家的散文,還有《浮生六記》。而馮驥才最喜歡看的是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他說:“豐子愷的譯本比別人翻譯得好,好就好在,隨便翻哪一頁都能看。最好看的書是從哪一行都可以開始看的書。我看《獵人筆記》主要是看寫景。2003年去俄羅斯訪問,我去了托爾斯泰的莊園,還專門去屠格涅夫的老家一趟,發現真的和他書里寫的一樣。我看到了樹林、原野、河灣,飛來大片野鳥的野地,濕漉漉的森林……他說小蚊蚋成群地盤旋,在陰暗的地方發亮,在太陽光里發黑——我還想找小蚊蚋,可惜沒找到。”
這些枕邊書,讓馮驥才有常看常新的感覺。那種心里上的愉悅,是一種很美的文學享受,瞬間給人意境上的感染。
馮驥才還有幸保存著自己孩提時代閱讀的證物——圖畫書和小人書。比如上海兒童良友社彩色膠印的《黑貓的假期》和《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有上海國光書店出版的《珊珊雪馬游月球》,都是民國三十八年(1949)出版的書。當時的馮驥才只有六七歲,這些書都是母親買給他的,是他一生中看得遍數最多的書,至少幾百遍,書中每個形象至今還印在腦袋里。
少年時的馮驥才有一段時間十分迷戀武俠小說。天津是武俠小說家鄭證因、宮白羽和社會言情小說家劉云若聚集之地,到現在他還有一些這類書的藏本。后來,馮驥才轉而熱愛古典文學,與學畫有關。那時學畫由臨摹古畫起步,必然會接觸到畫上常常題寫著的詩文,要弄懂這些詩文就要學習。經人介紹,當時二十一二歲的馮驥才跟著吳玉如先生學古文,從《古文觀止》學起,到《古文辭類纂》和杜詩,講的都是系統的知識。
吳玉如先生的教學方法,讓馮驥才印象深刻,“他講《赤壁賦》不看書,背著講。他一邊講,講到一個地方,一邊拿毛筆寫。寫到某一個字,用說文解字講。講一大段,然后讓你背,再往深處再講一段。吳先生講得太好了,對仗、音律,講得講究、精道,入心了,八九不離十能背下來。和老一代大家接觸,深受的影響就是他們的文人氣息。那時候的書房,有琴棋書畫,有很濃的書卷氣。不僅有書,還有文玩,每一樣小東西的品質、內韻都有講究。”
馮驥才愛書,藏書,也喜歡收藏一些“怪書”,都是罕見的、奇特的東西。比如說他收藏的一部手抄本,民國初年搞口頭戲劇演唱的成兆才的畫本,是演唱的時候必須用的臺本,臺本里有小戲、民間傳說、順口溜、快板……一二百種,非常有意思,光看那個東西,能看出江湖中的百態眾生相。在《書房一世界》中,談到自己的書房“四壁皆書”,馮驥才坦言,自己喜歡被書埋起來的感覺。書是他的另一個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書里,世界沒有的一切也在書里;過往的幾十年里,書與他攪在一起;讀書寫書,買書存書,愛書惜書,貫穿了他的一生。
馮驥才與書緣分太深,雖多經磨難,焚書毀書,最終還是積書成山。他把絕大部分圖書搬到學院給學生們看,建了一個圖書館,叫作大樹書屋;還有一部分捐到了寧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館。他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書了,留在家里和書房里的只是極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數千冊。
當然,能被馮驥才留下的書,總有道理。比如常用的書、工具書、怕丟的書,還有一組組不能失群的書,比如敦煌圖書、地方史籍,還有“劫后余書”和自己喜歡的中文名篇的選架上的書本和外文名著的譯本。其中一架子書,全是他自己作品的各種版本。
寫作的人都很隨性,各類圖書信手堆放,還有大量的資料、報刊和有用沒用的稿子。馮驥才說,書房不怕亂,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費勁就好。書房正是要這樣亂糟糟,才覺得豐盈。像一個世界那樣駁雜、深厚,乃至神秘。
責編: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