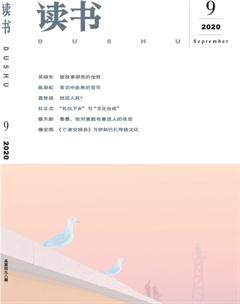梅貽琦日記中的 “珊”
徐韞琪
梅貽琦于抗戰烽火中勇挑重擔,擔任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主席直至一九四六年七月聯大結束,被譽為聯大的 “船長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記錄了他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六年間的心路歷程,除了每日為校務奔走操勞、周旋于政界學界,日記還透露了他熬夜看竹、把盞聽戲的生活細節,呈現出梅校長 “寡言君子 ”之外的風雅一面。日記中還隱藏著他與 “珊”之間貫穿十年的情誼,展卷而思,足可體悟前輩學人于亂世中的隱忍與堅守,感受人性的復雜與高貴。
一、 云中誰寄錦書來
梅貽琦本人性格謹慎,他日記中的記述也大多短小精悍,罕見感情流露。正如其子梅祖彥所說,“先父在公開場合一向不喜歡發表議論,所以在寫日記時也不多作議論 ”,甚至關于 “一二 ·一”慘案,李公樸、聞一多暗殺案等重大政治事件的記載也頗簡略。盡管如此,關于 “珊”的記載貫穿了他六年的日記,梅貽琦詳細記述了和 “珊”之間每次通信及會面的細節,在與 “珊”有關的記述中,多見真情的流露。
在梅貽琦為聯大四處奔走的艱辛歲月中,同“珊”的通信似成為他困頓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一段值得特別珍藏的記憶。以收錄最完整的一九四一年日記為例,梅貽琦明確提及 “珊”有十六處之多,無論是寄信還是收信皆有明確記錄,常伴隨著對她的思念與擔憂。如一月十六日記:“早發與珊短信,前晚所寫者,伊又久未來信,不知是否又病了!”三月十八日記:“上午在聯大,接 Z.S.十一日短信,伊情緒頗苦,而信紙似亦缺乏矣。”梅貽琦接到對方信件后的快慰亦流露于筆端,在繁忙的事務中,“珊”的來信為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十月一日記:“下午四點常委會,七點開完始晚飯。會中決設聘任委員會。接珊二十六號電,問‘無恙否 。”梅貽琦渴盼著對方的來信,當郵路阻隔導致收信延遲,他深感遺憾和焦慮。五月十七日記:“近一周接珊來信兩封,一為四月二十六寫,而一為三月二十七寫,乃竟至五十日始到,殊不可解,或為港方所稽壓,可憾之至。”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八月期間,梅貽琦與同事前往重慶接洽校務,視察敘永分校及中研院史語所,后又前往樂山、峨眉、成都等處參觀各大高校,在三個多月緊鑼密鼓的行程中,梅貽琦堅持抽出空隙與“珊”通信。旅途中影響了信件穩定地發出,往往是事先寫成若干封,得空便一同寄出,在梅貽琦關于發信的記錄中,“珊”的名字常列在家人、同事之前。他在五月二十六日與弟弟梅貽寶等人會談的間隙 “發信與凈珊、楊今甫、葉企孫 ”;六月三日在暑熱中 “四點余發二信:一與凈珊,一與祖彥(梅貽琦之子)”;六月十九日 “作信四封,寄與珊、彬(梅貽琦之女)、光旦、孟鄰 ”。回到昆明后梅貽琦忙于匯報行程和監督新校舍被炸后的復原工作,直至九月二十四日才與 “珊”通信,他在日記中寫道,“晚,常委會,十點散。作信與凈珊,此為回昆后第一封,恐伊必更懸念矣 ”,言辭間頗為自己久未致信而歉疚。
梅貽琦留給外人的印象往往是沉穩、理性的,葉公超曾用 “慢、穩、剛”形容他,陳寅恪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然而,在他關于
“珊”的記載中則呈現了自己感性、脆弱的一面。梅貽琦常在臨睡前寫信給 “珊”,如“晚未出門,為珊作復信 ”;“晚睡前作信與珊 ”;“歸后作致珊信,一點半睡 ”。他將為 “珊”寫信作為一項事務鄭重其事地對待,當漫漫長夜,天地寂靜,我們仿佛看到梅貽琦于燈下走筆的孤獨剪影,他等待著心靈的知己,將所思傾瀉于筆端,繼而融入無邊的月色:“月色頗好,惜無共賞者爾。”月夜的幽寂與懷人之感傷蔓延于胸中,更激起無限愁思:“三信寫完已過一點,院中涼月滿階,階前花影疏落,一切靜寂。回憶珊信中語句,更覺凄悶,不知何日得再相見也。”抗戰勝利后 “珊”隨家人遷居南京,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梅貽琦記 “晚座間蘭花盛開,香氣頗覺襲人,折一朵寄南京,以寄意耳 ”,頗有 “折芳馨兮遺所思 ”之古意。這些凝結著古典詩意的溫情瞬間展露了他豐富的情感世界,在記載推杯換盞的應酬與大大小小會議的文字中,顯現出難得的文人情致,讀來令人動容。
二、所謂伊人
關于 “珊”的身份、容貌以及二人相識過程,梅貽琦并未在日記中多加敘述,事實上,“珊”“Z.S.”,反復出現在日記中的 “凈珊 ”“山”即朱經農的繼配夫人楊凈珊。朱經農的長子朱文長提到繼母曾在婚前與陶曾谷任教于上海某私立中學,可見其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楊凈珊的相貌亦頗出眾,畫家譚化雨在《不速之客朱經農》中回憶四十年代初見到的 “朱太太 ”舉止大方得體,待客周到細致,其出眾的美貌更令作者在五十年后記憶猶新,足見其魅力。
梅貽琦與 “珊 ”的往來,繞不過朱經農。朱經農家世顯赫,一九一六年他赴美深造時與胡適相談甚歡,胡適有《贈朱經農》一詩,并曾在日記中寫道,“經農為中國公學之秀,與余甚相得 ……革命后,國中友人,音問多疏,獨時時念及湯保民及經農二人 ”,足見二人交情之深。朱經農歸國后投身教育事業,一九三一年以后擔任湖南省教育廳長十二年之久,王云五稱賞其為 “全面教育家 ”,具有 “公而忘私的精神,明敏的頭腦,動人的口才 ”。官員與學者的身份之外,朱經農更是一位頗具情懷的詩人,《愛山廬詩鈔》匯集了他二十年代以來的舊體詩作,《寄內》等作與凈珊的緣情之篇尤見真摯。箋注者朱文長提到詩集原名《碎錦集》,后來改名 “是采的 ‘仁者愛山 的意思,但據我猜測,大概也是因為我繼母的名字叫靜山(筆者注:凈珊別稱)的緣故 ”,似隱含朱對于楊的一往情深。一九四八年朱經農參加聯合國文教會議時,身上只帶了日記和《愛山廬詩鈔》,可見此集對他極為重要,此后朱經農再未回國,直至一九五一年在美國病逝。
據《愛山廬詩鈔》箋注,朱經農與楊凈珊于一九二四年結婚,他在一九三三年用 “同心十載艱難里 ”概括十年的歷程,“一片天真惟我知,錦函語語可成詩 ”更飽含對愛妻的深情,然而二人婚后的生活卻暗藏波瀾。事實上,楊凈珊在結識梅貽琦之前,對丈夫的好友胡適產生過情愫。張書克《“是誰記念著我?”》(發表于《東方早報》,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文解密了楊凈珊在一九三二年匿名寄給胡適的水仙花與賀卡,以及兩封寫于一九三四年的署名 “Zing-shan”的英文信札。楊在信中稱胡適為 “親愛的適之 ”,傾吐了期盼與其會面的心意,但遭到胡適的婉拒。胡適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作一信與 Z.S.Y,此人即是前年以來之 Unknown Correspondent。此書勸其決絕。”接到胡適的拒信后,楊的情緒頗為失落,感嘆 “除了想象和夢,我什么都沒有了 ”。盡管如此,她還是對胡適抱有最后一絲幻想:“又:適之,我能不能有一個請求?求你再寫一封信給我,就一封,一封好的!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嗎?”
在這段婚姻中,楊凈珊似乎并不能獲得情感上的滿足,這與丈夫濃情蜜意的《寄內》詩形成了難以忽視的張力,也為后來她與梅貽琦的密切通信埋下了伏筆。據梅貽琦日記中有限的記載推測,楊的來信內容包括傾訴生活的苦悶、行程安排、家庭事務、對梅的關切,時而彌漫著感傷的氛圍,似乎將梅貽琦視作無話不談的心靈摯友。那么,梅貽琦是何時與 “珊”結識的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梅貽琦日記中有 “回憶九年結識 ”之語,而一九三六年前后朱經農正擔任湖南省教育廳長,與楊凈珊在長沙居住。平津淪陷后,國民政府將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時任教育廳長的朱經農免不了常與梅校長打交道。很有可能在此期間梅貽琦與楊凈珊結識,而他在戰亂中運籌帷幄的才干無疑令人心生欽慕。后因戰勢緊迫,國民政府將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西南聯大,梅貽琦從此常駐昆明,楊凈珊仍留在湖南,直至六年后隨丈夫遷居重慶。
三、君子之風
梅貽琦主掌西南聯大期間,需要經常赴重慶匯報校務工作,一九四四年起朱經農擔任教育部次長,梅貽琦與他有了更多往來。據一九四五年日記,梅貽琦當年共五次飛往重慶,在渝期間,梅貽琦幾乎每日都前往朱宅,或用餐,或辦公,或會客,“至朱宅 ”成為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引人注意的是,作為朱家客人的梅貽琦在日記中關于楊凈珊行跡的記載尤其周備,無論是訪而未遇,還是送行細節,都有明確的記錄。
在通信不暢、物資緊缺的戰爭年代,朋友相會并非易事,楊凈珊當時常往來于朱宅與青木關之間運送物資,故相見往往需要特殊的機緣與默契。梅貽琦在九月十九日的日記中提到,“五點,珊自青木關來,意謂曾待吾或于前數日前往關上者。吾亦曾有此意,惜未得便耳 ”,足見二人的期待與懊憾。十月五日楊凈珊提前歸來,梅貽琦難掩驚喜之情,“晚飯后珊竟自青木關歸來,初聞其須下星期一方能運物歸 ”。在渝期間,梅貽琦默默關注著楊凈珊的健康狀況。四月一日他特別記下 “珊傷風頗重 ”,十月七日記 “珊仍患嘔吐,不能多進食 ”,兩天后又記 “珊病似仍未愈,但興致甚好 ”,似稍欣慰。盡管對楊凈珊頗有好感,梅貽琦畢竟是一位正人君子,根據日記所載,二人很少長時間單獨會面,一同出行也往往有他人在場,如二月二十六日 “午珊與曉峰(楊凈珊弟楊志恩)來約食餅面,購物 ”,十月十日 “晚飯與志恩小飲,珊則以茶代酒 ”,日記中的表述流露出相當的克制與坦誠。
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往南京,此后政界學界處于動蕩之中,梅貽琦亦為北上復校計劃輾轉奔走。一九四六年日記較完整地記錄了他的赴渝始末與滬寧行程。二月十五日飛抵重慶后,梅貽琦前往朱宅用餐,其間 “珊等正忙于收拾箱籠,始知數日后即將往南京矣 ”。匆匆握別后,梅貽琦依然掛懷,三天后開始寫信給楊凈珊。計劃趕不上變化,二十六日梅貽琦收到教育部密電,催其速歸昆明嚴防罷課風潮:“吾雖覺或非嚴重,而又感在渝任務未完,但只好決計歸去,此責他人亦難負也。”此時他無疑體現了作為一校之長的擔當。如果說這次重慶之行略顯倉促,那么三個月后的南京之行則洋溢著重逢的喜悅。
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后,朱經農一家亦從重慶遷往南京。五月二十四日下午梅貽琦由上海抵達南京下關,“珊與文華、文光則于站柵外始得見 ”。一個 “始”字,蘊藏著不足為外人道的牽掛與喜悅。在南京期間,梅貽琦于應酬公務之余得空 “與珊等看竹 ”,“晚飯后與珊及文光、文衡偕有騫至龍門茶室聽西樂,飲啤酒、咖啡 ”,度過了一段頗為愜意的日子。他與朱經農一家乘汽車出游中山陵,“孩輩搶登紀念塔,余、珊、經在草地上休息 ”,夏風習習,晚輩的歡聲笑語掠過耳畔,三人誠摯的友誼定格在青綠的草坪上。這一溫馨的時刻成為梅貽琦日記中的吉光片羽,在多年后依然閃爍著動人的光芒。離開南京的前一晚,梅貽琦托楊凈珊購買煙草,并與之鄭重話別,凌晨方睡。第二天一早,梅貽琦懷著不舍飛離南京,這也是日記中二人的最后一次會面。兩個多月后,梅貽琦曾 “作致珊信,一點半睡 ”,此后日記原件斷缺,關于二人交往細節不復得知。
自始至終,梅貽琦體現著 “發乎情,止乎禮 ”的君子風范,他將心緒訴諸文字,對友人與友人之妻抱有深厚的敬意,而朱經農亦有君子之風,頗為大度。朱經農與梅貽琦的私交是純粹而篤實的,在政見上亦多有相合之處,對學術自由的崇尚更奠定了二人友誼的根基,在風波詭譎的斗爭形勢下,他們始終堅守著知識分子的底線與立場,終成莫逆之交,朱宅更成為梅貽琦奔忙旅途中安頓身心的港灣。
作為日記的讀者,我們一方面為梅貽琦與楊凈珊在抗戰烽火中的深厚情誼感到可貴,另一方面也難免產生 “不如憐取眼前人 ”的慨嘆。梅貽琦的青梅竹馬之戀、夫人韓詠華曾在《同甘共苦四十年》一文中深情追憶了 “白飯拌辣椒 ”的艱辛歲月,她在昆明物價飛漲之際做 “定勝糕 ”售賣以補貼家用的故事更傳為一段佳話。遺憾的是,梅貽琦日記中很少述及梅夫人及自己的婚姻生活,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七日 “校中同人卅余人欲作銀婚之祝 ”,但被梅貽琦婉拒。這或許與梅貽琦本人低調的行事風格有關,又或是對至親之人羞于表露情感。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九日,韓詠華在臺灣陪伴梅貽琦走完了他病榻上的最后一程。據新竹清華大學教務長朱樹恭說,梅貽琦逝世后建造的墓穴本是夫妻雙人穴,但安葬時梅師母 “以梅校長和她都是基督徒,日后會在天國相晤,她自己隨處可安,不必留墓穴,所以梅校長遺體安放墓中央 ”。盡管韓詠華的身影很少出現在丈夫的日記中,他們半生的相濡以沫仍令人深深感佩,這種患難與共的夫妻之情是永遠無可替代,也是不可磨滅的。“同心十載艱難里 ”的背后,正是無言的親情。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中華書局二○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