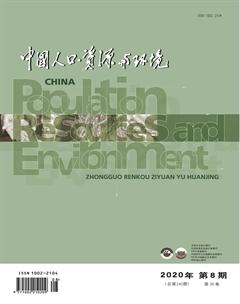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能化解產能過剩嗎?
于斌斌 吳銀忠



摘要 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投資失調所導致的就業-產業結構失衡是工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國2002—2016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采用差分GMM估計方法檢驗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影響工業產能過剩的直接效應及產業結構、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的調節效應,并分析了直接效應和調節效應的門檻效應。研究發現:①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具有顯著的化解效應,但呈現“倒U型”的影響路徑。②調節效應的結果顯示,非效率的產業結構升級與有偏的技術進步升級抑制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而人力資本升級不僅促進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還能有效改善了就業-產業結構對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不利影響。③門檻效應的結果表明,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變遷,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呈現“先促后抑”的影響路徑,而技術進步升級在跨過經濟發展門檻值前后,則呈現出“先抑后促”的影響路徑。以上研究結論意味著,現階段促進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與加快人力資本升級,可以成為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新思路。
關鍵詞 就業結構;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產能過剩
中圖分類號 F42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0)08-0128-12DOI:10.12062/cpre.20200114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能過剩問題一直貫穿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尤其是從“三期疊加”到“經濟新常態”,再到現如今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不將產能過剩的化解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產能過剩猶如立于中國經濟發展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無論是短期抑或長期的產能過剩都會帶來諸如經濟波動加劇、市場惡性競爭、資源配置失調、金融風險上升、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1]。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產能過剩具有周期性(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經歷三次大規模的產能過剩)、普遍性(傳統行業蔓延至新興行業)、結構性(供需結構不匹配)、體制性(政府過度干預與政企合謀)等顯著特征[2]。盡管政府在化解產能過剩方面持續不斷地出臺相關政策,但卻收效甚微,甚至陷入“過剩→調控→再過剩→再調控”的惡性循環。
關于產能過剩形成的原因,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式產能過剩主要是由供給側的投資失調所致。一方面,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企業作為市場的直接參與者極易產生共同預期致使投資過度集中于某一行業[3];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市場的調控者,其利益集團出于自身政績的考量,會通過補貼、貸款等方式對企業投資行為與市場進入、退出施加干預,進而扭曲要素市場配置,最終導致產能過剩[4]。不僅如此,技術創新作為企業爭奪市場份額的重要手段,在中國技術基礎較低的背景下,有偏的技術進步會產生“投資誘導效應”,從而固化了產能過剩[5-6]。由此可見,資本的不當使用是中國式產能過剩的一大成因。需要指出的是,資本的使用需要相應的勞動投入進行匹配,然而資本錯配卻致使勞動力大量堆積于工業部門,造成就業結構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發展,阻礙了過剩勞動力的釋放,因而就業-產業結構不匹配就成為阻礙產能過剩化解的一個重要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的就業結構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轉型,其本質是社會生產力的擴張無法彌補勞動生產率提升所帶來的“就業排擠效應”[7]。一方面,就業結構本身就是收入結構的體現,就業結構的“重心”下移意味著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這不僅會抑制需求端消費能力的提升,而且不利于需求結構的升級[8-9];另一方面,就業-產業結構失衡意味著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要素的錯配,而在技術進步與資本深化的背景下,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需求不斷上升,就業結構滯后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從而“拖累”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轉型升級,阻礙了產出結構優化,不利于產能過剩的化解[10-11]。因此,當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時,其能否化解產能過剩?如果可以,其以何種方式來化解?其進一步演化的趨勢如何?對于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能夠為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化解提供一個新思路。
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一是在理論分析上,探討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直接效應及產業結構、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的調節效應,為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提供了一個新思路。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利用產業結構、人力資本及技術進步與核心解釋變量的交互項逐個構建計量模型,考察了三者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三是在實證檢驗上,本文采取動態面板模型對上述理論分析框架進行了實證檢驗,驗證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倒U型”的影響路徑,并通過門檻面板模型,從動態視角分析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就業-協調發展對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1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直接效應
在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就業問題是政府的心頭大患,政府為了“保就業”不得已通過財政手段干預企業決策,從而將勞動力“囚禁”在低技術偏向的大型制造業中[4],這既會誘發就業結構低技能化,致使勞動收入份額降低,也會導致就業-產業結構失衡,弱化勞動要素的再配置效應,造成產能過剩現象。而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強調勞動力的“各得其所”,無論是從擴大勞動收入份額,還是從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來看都顯得至關重要。具體而言,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產能過剩的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就業結構調整會增加勞動收入份額,促進消費能力提升。在工業就業結構臃腫的背景下,要素價格偏離其邊際產出,造成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12],而就業結構調整的本質是勞動力由低效率向高效率的演進過程,尤其是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優化了勞動力配置,改善了行業間勞動要素的邊際產出,有助于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從而為產能過剩的化解奠定需求基礎。第二,要素再配置效應是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典型特征,也是產能過剩化解的關鍵。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正是利用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來引導各類生產資源從產能過剩行業中退出,這既化解了產能過剩,又為其他行業的發展提供了物質生產資料,有助于供給側產出結構的優化,更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遷。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IV: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直接效應顯著為正。
1.2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
在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升級是就業結構調整的目標和方向,這意味著產業結構升級必然會影響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產業結構升級的本質是生產要素在生產率不同的部門間流動,從而引發了要素再配置效應,其效應的強弱和方向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產出和流向[13]。在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要素市場基于不同產業的要素邊際產出,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等途徑促使勞動力由低邊際產出行業流向高邊際產出行業,進而將勞動力從產能過剩的行業中釋放出來,提高了生產要素的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14]。同時,產業結構持續升級的最終結果是工業現代部門與服務業現代部門的比重不斷提升。一方面,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必然會帶來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其中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比重上升能夠促進有效供給,優化產出結構,進而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緩解“需求飽和式”的產能過剩[6]。另一方面,產業結構合理化促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相互協調,其中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金融支持、物流通信、科技服務等途徑降低制造業交易成本,進而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15-16]。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Ⅱ:產業結構升級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為正。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必然涉及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但與資本不同的是,勞動力難以無摩擦地進行跨產業流動,因而人力資本在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中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市場會增強對人力資本的需求與依賴,誘使大量勞動力向具有更高勞動報酬的崗位轉移,進而縮小了從業者間的收入差距,有助于居民消費能力提升。不僅如此,人力資本升級還可以加速社會形成新的供需關系[17],為勞動力流動提供新的平臺,這既能擴大就業規模,緩解就業壓力,也能提升勞動收入份額,擴大消費需求,從需求端緩解了產能過剩。此外,在人力資本升級過程中,教育投資與健康投資可以優化勞動力的空間分布[18],這種勞動力流動方式催生了社會對于公共品的強烈需求,而單純依靠市場供給難以滿足這種需求。此時,通過人力資本升級,可以引導政府財政投資流向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部門[19-20],填補社會公共品的短缺,減少不利的重復建設,優化產出結構。更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資本所具有的邊際收益遞增特征將會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21]。與因信息不完全所引起的“潮涌現象”不同的是,人力資本升級引致的投資可以促進公共服務部門的發展,優化生產要素的產業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Ⅲ:人力資本升級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為正。
在中國步入經濟新常態之際,就業問題的解決已經不能僅依賴于傳統的“三駕馬車”,應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就業格局轉向技術進步驅動的就業格局。然而,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技術進步會促進生產工藝的升級,催生新產品與新行業的誕生,這既能夠提升供給質量,優化產出結構,還可以增強就業吸納能力,擴大就業規模[22];另一方面,隨著技術不斷深化,智能化與自動化逐漸成為社會生產的主旋律,這勢必會造成傳統產業部門的衰退,致使就業規模縮減,甚至會引發工資的降低[23]。因此,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取決于其就業創造效應與就業破壞效應的相對大小,并會通過影響就業規模與就業結構,進而影響勞動收入份額與社會產出結構。除此之外,技術進步的偏向性也是決定勞動收入份額的重要因素[24]。Karabarbounis和 Neiman[25]利用國家層面的數據研究發現,資本偏向型的技術進步解釋了約50%的全球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居民消費能力。在技術進步與資本深化的背景下,有偏的技術進步會對不同要素的相對邊際產出形成非對稱的作用,造成不同要素間的收益差,并誘使企業以高收益要素擠出低收益要素,進而改變勞動收入報酬。由此可見,技術創新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取決于其就業效應的正負以及技術進步的偏向性。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Ⅳ:技術進步升級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存在不確定性。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產能過剩的機制見圖1。
2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工業產能利用率的測算與分析
2.1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的測算
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著總量與比例兩方面的關系,但總量分析無法準確反映兩者協調匹配度,因而本文選取比例分析法。目前,學術界對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比例關系的測算方法主要有比較勞動生產率、結構偏離度、就業彈性與協調系數等。具體而言,比較勞動生產率和結構偏離度偏重微觀層面的協調性分析,就業彈性則更多用于衡量就業吸納能力的強弱。相較前兩者而言,協調系數從中觀層面分析了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整體協調性,更適合本文的研究。但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的協調系數實質上是向量夾角的余弦值,其取值范圍為0到1,無法充分描述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演進方向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改進的協調系數IH來度量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協調匹配度[26],該指標克服了傳統協調系數僅能描述兩者同向趨勢的缺點,將指標的取值范圍擴充至-1到1,利用變量的正負性來體現演進趨勢,更為貼近中國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協調演變過程。
定義x= (x1,x2,x3)與y= (y1,y2,y3)表示第t年的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其中xi yi,yi,i=1,2,3分別表示第i產業對應的就業結構比重和產業結構比重。通過對上述指標進行如(1)所示的CLR計算可以得到向量CLR(x)和CLR(y),其中
g(x)=n∏ni=1xi 。
CLR=lnxi-lng(x)(1)
改進的協調系數IH的計算公式如下:
2.2 工業產能利用率的測算
生產與消費是產品必須經歷的兩個階段,生產決定了企業對于生產要素的使用程度,生產能力的不足則意味著供給側產能過剩,而消費決定了社會對于產品的需求程度,消費能力不足則意味著需求側產能過剩,任一方面的能力不足都將導致產能過剩的出現。因此,本文欲采用產能利用率,綜合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維度來測算工業產能利用率。
對于需求側工業產能利用率(EPC_C)的測算,新聞界往往用“需求不足”“供大于求”等字眼進行描述。鐘春平和潘黎[1]也認為,產能過剩是社會實際生產能力遠高于市場需求的表現。由此可見,需求與供給的比例關系是需求側產能過剩的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現有文獻往往從消費、投資及凈出口三方面對總需求進行度量[27],對工業品的需求涉及較少。故此,本文借鑒楊振兵[5]、Yu和Shen[28]做法,從工業品消費市場出發,利用各省的工業銷售產值(Sales)與工業總產值(Supply)之比表示需求側產能利用率,具體計算如下:
EPC_Cit=Salesit/Supplyit(3)
關于供給側工業產能利用率(EPC_S)的測算,學術界主要有峰值法、結構向量自回歸法、函數法、協整法、前沿分析法等方法。而前沿分析法是當前的主流測度方法[2,29-30],主要包括數據包絡分析(DEA)與隨機前沿分析(SFA), 其原理是通過對前沿面的測算,估算相對于前沿面的無效率部分,進而得出產能利用率。但需要指出的是,DEA方法并未考慮企業的跨期決策,各個時期的生產前沿面存在跨期不可比性,且忽略了要素間的替代彈性,致使測算結果存在一定誤差。而SFA方法則通過設定生產函數的方式,引入了時間變量,并考慮了生產要素的相互替代性與技術進步差異,能夠較好地克服測算偏誤。因此,本文借鑒Kirkley等[29]的處理方法,將生產函數設定為:
其中,Y為各地區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并以各年份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進行平減;K為工業資本投入量,通過永續盤存法Ki,t=(1- δ) Ki,t-1+Ii,t計算,式中折舊率設定為10.96%[31],當期投資I為相鄰兩年固定資產凈值差額;L為工業勞動投入量;E為工業能源投入量,本文以萬噸標準煤為單位的地區能源消費總量作為替代變量;υ、μ分別為服從獨立同分布的隨機誤差項及服從正態分布的技術誤差項;γ為隨機擾動項中技術無效所占比重,通過極大似然法估計,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結果顯示,大部分參數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本文設定的生產函數模型有效。無效率項μ、總體方差σ2、γ檢驗值均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中國工
業存在整體性的無效率現象,且組合誤差主要源自技術無效率,但這種源自技術無效率和隨機因素的生產波動的程度并不大。因而,選用SFA較為符合當前中國工業生產效率的演變過程。
接下來,通過對需求側產能利用率EPC_C和供給側產能利用率EPC_S進行如式(8)的處理方式,可以得到綜合的工業產能利用率EPC。
EPCit=EPC_Cit×EPC_Sit(8)
3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
3.1 計量模型設定
根據理論分析,本文將重點探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機制及效應。因此,本文以工業產能利用率(EPC)為被解釋變量,以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IH為核心解釋變量構造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EPCit=β0+β1IHit+ηXit+ui+εit(9)
其中,i表示地區,t為時間;EPCit為工業產能利用率;IHit為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Xit為控制變量集;μi為不隨時間變化的個體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由于企業生產行為和社會消費行為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特征[5],當期生產計劃往往建立在前期基礎之上,因此本文引入工業產能利用率的滯后一期構造如下動態模型:
EPCit=β0+xEPCi,t-1+β1IHit+ηXit+ui+εit(10)
Acemoglu和Guerrieri[32]認為,工業部門就業份額與工業化進程存在一種“倒U型”的演化路徑,即存在“庫茲涅茨事實”,而大量研究證實勞動收入份額與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U型”的影響路徑[9,25]。這意味著在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存在一個“轉折點”,而這勢必會影響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為驗證“轉折點”是否存在,本文引入IH的二次項,構造如下趨勢效應模型:
EPCit=β0+xEPCi,t-1+β1IHit+β2IH2it+
ηXit+ui+εit(11)
理論分析表明,產業結構升級(Hit)、人力資本升級(Cit)、技術進步升級(TPit)可能影響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為了進一步考察上述三者的調節效應,本文引入IHit與各變量的交互項,建立以下三個模型(本文稱之為模型一、模型二與模型三),具體如下所示:
3.2 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與核心解釋變量分別為工業產能利用率(EPC)與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IH)。這兩個變量直接采用上文的計算結果。另外,關于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升級與技術進步升級三個調節變量的測算方法如下。
首先,關于產業結構升級(Hit)的測度,為了體現產業結構升級的服務化與效率化兩個層次,本文對Moore結構變動指數進行改造,以勞動生產率替代權重進行加總,具體計算方法如下所示:
θj=arccos(∑3i=1(xji×xoi)
(∑3i=1x2ji)×
(∑3i=1x2oi)(15)
H=∑3i=1Ej×θj(16)
其中,x0i為產業結構空間向量X3= (x01,x02,x03)的第i個分量,xji為基本向X1= (1,0,0)、X2= (0,1,0)與X3= (0,0,1)的第i個分量;Ej為第j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其中勞動生產率用各產業的增加值除以相應從業人數表示。
其次,關于人力資本升級(Cit)的測度,本文運用Moore結構變動指數對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進行處理。本文將就業人員受教育程度設置為5類: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含高等職業教育)、大專及以上,其中θj的算法與式(15)相同,其余公式如下所示:
Cit=∑5j=1Wj×θj(17)
其中,Wj為θj的權重。
最后,關于技術進步升級(TPit)的測度,本文綜合自主創新(RD)與技術引進(FDI)兩個維度進行評價。自主創新主要提供的是產品層面的創新,本文以研發支出占財政支出表示;而技術引進是技術轉移與組織管理技術等方面的創新,本文以實際FDI占全社會固定投資比例表示。最終,本文以式(18)的公式計算技術進步升級,具體如下所示:
TPit=RDit×FDIit(18)
另外,控制變量選取如下:一是市場化程度(mar),采取各省份私營企業就業人員與個體企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表示。市場活力的體現主要在非公有制經濟,當其成分越高時,越能通過競爭機制發揮市場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二是城鎮化水平(urb),以各地區非農人口占比表示。人口城鎮化能通過人口集聚的外部性推動產業集聚,創造需求進而化解產能過剩。三是政府干預度(gov),以財政支出與GDP之比表示。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可能通過財政、貸款、土地等方面對要素市場進行扭曲,導致了產能過剩的淘而不汰[4]。四是社會消費力(con),以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占GDP比重表示。居民的收入不外乎儲蓄與消費兩種途徑,而該指標反映了社會居民消費能力,體現了國內市場需求的程度。
本文選取中國2002—2016年3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由于數據可獲得性,西藏除外且不包含港澳臺)的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對象,并以2001年作為基期,各項指標均以相應平減指數進行平減,缺失的個別數據用插值法補齊。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及各省份的《統計年鑒》。
3.3 基準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混合回歸、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FE-2SLS模型和RE-2SLS模型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系數估計,結果見表2。在各模型估計結果中,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均存在顯著的正效應,這表明就業-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能比較穩健地提高工業產能利用率,即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可有效化解工業產能過剩。F檢驗與Hausman檢驗的結果表明,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優于混合回歸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FE-2SLS與RE-2SLS模型中過度識別檢驗(Hansen檢驗)的結果表明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問題。
本文進一步采取LLC檢驗、IPS檢驗、ADF-Fisher檢驗、PP-Fisher檢驗等四種方法對數據平穩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一階單整序列均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由于變量均滿足一階單整,因此本文借助Kao檢驗、同質Pedroni檢驗、異質Pedroni檢驗對模型進行協整檢驗,結果顯示三種檢驗的均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不存在偽回歸的現象。
3.4 動態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
考慮到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工業產能過剩可能存在相互影響,即一方面,工業產能過剩會扭曲社會資源配置,影響潛在競爭者進入,進而誘發就業結構與產業結
構調整;另一方面,就業-產業結構的變遷會加速資源重新配置,從而影響工業產能過剩。因此,本文以滯后的工業產能利用率、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為工具變量,利用差分GMM估計法對上述模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在各模型中,工業產能利用率的滯后一期系數均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工業產能過剩的“路徑依賴”現象極其顯著。在動態回歸結果(除模型二)中,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一結論驗證了假設Ⅰ的合理性,意味著推動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確實有利于化解工業產能過剩。原因在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促使勞動力配置與產業結構變遷相適應、相匹配,而合理的就業結構將堆積在產能過剩行業的勞動力轉移到其他行業,減少了資源的錯配,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并促進產業結構由不合理向合理化轉變。
通過進一步比較基準模型與趨勢效應的估計結果發
現,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一次項系數顯著為正,而二次項系數顯著則為負,這表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存在“倒U型”的變化過程。這意味著,在勞動力的重新配置過程中,在尚未達到閾值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總是有利于化解工業產能過剩,而在達到閾值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反而不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這可能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與工業化的推進,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將更依賴于服務業的深化[33]。在服務業深化的過程中,工業生產中的服務部分將轉移到生產性服務業,釋放了過剩的生產要素,但也導致了就業-產業結構的不協調發展。這一可能性推論將在下文進行拓展分析。
模型一的結果顯示,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產業結構升級交互項的系數在10%水平下顯著為負,不符合假設Ⅱ的預期。本文通過將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分解為服務化(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產值之比)與效率化(采用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之比),估計結果如表3列5與表3列6所示。服務化的估計結果說明,產業結構服務化不利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產能過剩的化解。而效率化的估計結果表明,當產業結構高級化促使勞動力從低效率的部門流向高效率的部門時,其可以通過優質的生產性服務業為工業部門提供相匹配的服務,促進不同部門的相互融合[16],進而促進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對產能過剩的化解。這意味著,在中國農業與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服務業的背景下,經濟結構的服務化拉低了全社會勞動生產率,影響了國民收入、投資、消費等,不利于產能過剩的化解,即產業結構“逆高級化”或“逆服務化”更有利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
模型二的結果顯示,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人力資本升級交互項的系數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且為正,表明人力資本升級可以增強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能力,這一結論驗證了假設Ⅲ的合理性。一方面,人力資本升級可以提高從業人員的通用技能與專業技能,減少了因供求錯位而導致的再就業壓力,促進就業結構調整,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另一方面,人力資本升級所引致的一系列公共部門投資,可以強化私人投資的擠入效應,減少重復產能的建設,優化資源配置[2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人力資本交互項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人力資本升級還可以有效緩解了就業-產業結構非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不利影響。目前,中國就業結構的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發展,而任何生產活動均需要相應人力資本投入來實現,不匹配的就業結構阻礙了這種機制。因此,這種“就業結構拖累產業結構”的負面影響就在人力資本層面得以彰顯。
模型三的結果顯示,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技術進步升級交互項的系數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且為負,表明技術進步升級抑制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這種負效應的根源在于要素互補型生產函數下技術進步的資本偏向所帶來的勞動力冗余、產業無序轉移[34]。在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日益升高的背景下,企業偏好使用相對廉價的資本以替代高成本的勞動力,致使勞動力大量溢出,造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居民消費能力不足,而有偏的技術進步卻依舊推動著產能持續擴張,使得社會供需脫節,進而不利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產能過剩的化解。
在控制變量方面,市場化程度(mar)在所有結果中均顯著為正,表明市場化在化解產能過剩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資源配置方式更合理,更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城鎮化水平(urb)在所有結果顯著為正且通過顯著性檢驗,這進一步佐證了于斌斌和陳露[30]的研究結論,即推進城鎮化可以從經濟、人口、社會、環境四個維度多層次化解產能過剩。政府干預度(gov)的系數也均顯著為正,說明政府干預是可以提高工業產能利用率,其原因是政府對高技術產業的專項投資促使非國有企業產生了更強的就業創造效應,從而優化了就業結構,減少了因企業異質性而引發的產能過剩[35]。社會消費能力(con)在模型三中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且為負,說明當前中國社會消費能力仍然不足,供求失衡狀況較為嚴峻,無法從需求端為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提供動力。
4 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影響工業產能過剩的門檻效應
前文分析表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于工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存在一種“倒U型”的變化過程,這可能與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朱平芳和王永水[36]研究發現,在經濟發展初期,工業化進程較快,勞動力大量涌入工業部門,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勞動力將逐漸向消費性服務業轉移。然而Francois 和 Hoekman[37]指出,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制造業的生產與營銷將更依賴于生產性服務業的規模與質量。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初期,勞動力大量涌入工業部門,促使工業產能不斷擴張,此時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同步式擴張有助于企業生產能力的正常發揮,即就業-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有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的規模與質量成為制約產能過剩化解的關鍵,偏向消費性服務業的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無法滿足制造業的服務性需求,從而不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根據上述理論分析,本文認為就業-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利用率的影響過程中可能存在若干個“經濟門檻”,即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受制于經濟發展階段。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以Hansen[38]的面板門檻模型為基礎,以人均GDP(gdpit)為經濟發展水平的門檻變量,討論其是否存在非線性的人均GDP門檻效應,設定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IHit)與工業產能利用率(EPCit)的面板門檻模型為:
EPCit=β0+β11IHit×I(gdpit≤γ)+
β21IHit×I(gdpit>γ)+ηXit+μi+εit(19)
接下來,本文利用Bootstrap對上述模型進行反復抽樣以估計單門檻、雙門檻、三門檻,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中可以看出,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的雙門檻、三門檻均未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單門檻檢驗效果顯著,且通過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人均GDP在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影響工業產能過剩的過程中存在顯著的單門檻效應,門檻值γ為53 165.769 5元/人。由于工業產能利用率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既取決
于當期因素,也取決于前期的產能過剩。因此,本文將滯后一期的產能利用率引入門檻模型,構造動態門檻模型如式(20)所示,并利用差分GMM估計法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動態門檻模型的結果顯示,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是存在上限的,其呈現“先促后抑”的影響路徑。究其原因在于,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與城市化的推進,服務業的地位愈加重要。一方面,社會的需求結構從實物消費轉變為服務消費和實物消費并重,體現了服務業在需求側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現代農業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將更依賴于服務業的深化,展現了服務業在供給側的重要性[33,37]。
動態門檻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處于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地區,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對產能利用率起著不同的作用,這可能是由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所致[38]。對于未跨過門檻值的地區(如河北、山西、黑龍江),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呈現顯著的正效應,且通過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由于這些地區處于工業化中期,經濟發展依托資源和能源的大量投入,導致了就業-產業結構錯配,因而促進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可以優化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社會配置,有利于消費與投資的良性循環,化解工業產能過剩。在調節效應方面,產業結構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負,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階段,應更注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所帶來的產能過剩化解效應,而非一味追求產業結構的服務化調整。人力資本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正,表明加速人力資本升級可以引發新的社會投資,有效提高勞動報酬與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有利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產能過剩的化解。技術進步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負,其原因在于,不同地區產業層級存在較大差異[6],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技術密集型企業占比較低,技術進步的“投資誘導效應”促使企業生產規模和產能持續擴張,繼而產能利用率相對下降。
對于跨過門檻值的地區而言,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具有負效應且通過10%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首先,對跨過門檻值且工業產能利用率較高的地區(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由于處于后工業化或服務化階段,農業與工業的現代化發展將更依賴于生產性服
務業的發展,而服務業的規模擴張會產生正的外部性,有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同時,在經濟發達階段,服務業的就業吸納能力相較農業與工業而言更強,致使就業結構更傾向于服務業,從而造成了就業-產業結構的不協調發展。該結論也再次驗證了上文中的推論,即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農業與工業的發展將更依賴于服務業的深化,農業與工業生產中的服務部分將轉移到生產性服務業,釋放了過剩的生產要素,但也導致了就業-產業結構的不協調發展。其次,對于跨過門檻值但工業產能利用率較低的發達地區(如內蒙古、吉林、湖北等地),由于處于工業化中期,此時雖然就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已形成協調的趨勢,但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對工業依舊偏低。盡管消費性服務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但這種就業結構調整實際上無法滿足工業部門的生產性需求,“過早地去工業化”反而不利于產能過剩的化解[39]。在調節效應方面,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升級與技術進步升級均不顯著。但值得注意的是,跨過門檻值的地區在引入產業結構升級交互項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轉變為正,表明當產業結構升級偏向高級化與效率化時,有利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同時,技術進步升級對跨過門檻值的地區具有正的調節效應,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的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較高,因而技術進步升級導致的結構優化有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
5 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02—2016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影響效應,并分析了產業結構升級、人力資本升級與技術進步升級對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調節效應。通過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在考察期間內,中國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與工業產能利用率呈現同步的上升趨勢,但中國工業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工業產能利用率在56%~70%。實證結果表明,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存在正的直接效應。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可以促進過剩勞動要素從產能過剩行業中流出,從而提高了勞動收入份額與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
第二,產業結構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負效應。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國農業與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服務業,非效率的產業結構升級使得資源流向效率較低的部門,阻礙了落后產能的蛻變,并且過快的產業結構升級拉大了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偏差,削弱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所帶來的產能過剩化解效應。
第三,人力資本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正效應。人力資本升級所帶來的就業創造效應與投資擠入效應可以從就業安置、投資導向分別對勞動收入份額、資源配置效率進行優化,進而緩解就業-產業結構非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不利影響。
第四,技術進步升級的調節效應顯著為負效應。一方面,資本偏向型的技術進步導致勞動力大量冗余,拖累了就業結構的優化,不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從而抑制了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對工業產能過剩的化解效應;另一方面,有偏技術進步改變了不同要素的邊際產出,誘使企業利用資本要素進行生產,造成企業產能規模的不斷擴張。
第五,對于未跨過經濟發展門檻的地區,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為正的直接效應,但非效率的產業結構變遷與有偏的技術進步仍是就業-產業結構協調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制約因素。對于跨過經濟發展門檻的地區,就業-產業結構協調度對工業產能利用率具有負的直接效應。究其原因在于,在經濟發達階段,服務業的規模擴張有助于農業與工業的現代化發展,化解工業產能過剩,但服務業較強的就業吸納能力卻導致就業-產業結構的不協調發展。
從上述研究結論中得到以下政策啟示:第一,堅持“人才強國戰略”,推動人力資本升級。目前,中國就業結構調整滯后于產業結構發展,而就業結構升級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人力資本升級的問題。一方面,政府應在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上雙管齊下,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積極推動人力資本存量提升,增強勞動要素的流動性,為就業結構優化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資源,進而擴大勞動收入份額,實現內需擴張;另一方面,政府要注重健康人力資本的維護,建立和健全醫療保險制度,并通過適當的衛生經費支出,合理引導社會投資流向,優化產業間的要素配置,產生利于產能過剩化解的“新潮涌現象”。 第二,堅持效率優先原則,逐步推動產業升級。政府應當理性地對待產業結構升級問題,在尊重當前中國不同產業存在效率差異的前提下,對產業結構進行適度的調整,通過工業逐
步帶動服務業發展,尤其注重生產性服務業對于制造業的推動作用,將服務業的發展重心置于現代服務業部門,以圖通過優質的服務業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化解產能過剩。第三,積
極推進產教融合,實現供需良性循環。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產教融合是促進人才鏈與產業鏈有機契合,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方面,政府要鼓勵企業與大學等教育機構進行合理的人才對接,提高人才配置效率,更好地促進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的相互耦合,實現勞動供給與需求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政府要破除要素流動的制度壁壘,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勞動要素的“各得其所”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進而有效提高勞動收入報酬,優化產出結構,推動需求端與供給端的協調匹配,實現產能過剩的化解。
(編輯:王愛萍)
參考文獻
[1]鐘春平,潘黎. “產能過剩”的誤區——產能利用率及產能過剩的進展、爭議及現實判斷[J]. 經濟學動態,2014(3): 35-47.
[2]張少華,蔣偉杰. 中國的產能過剩:程度測算與行業分布[J]. 經濟研究,2017,52(1): 89-102.
[3]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 “潮涌現象”與產能過剩的形成機制[J]. 經濟研究,2010,45(10): 4-19.
[4]劉航,孫早. 城鎮化動因扭曲與制造業產能過剩——基于2001—2012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4(11): 5-17.
[5]楊振兵. 有偏技術進步視角下中國工業產能過剩的影響因素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6,33(8): 30-46.
[6]肖明月,鄭亞莉. 供給質量提升能否化解中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基于結構優化與技術進步視角[J]. 中國軟科學,2018(12): 126-139.
[7]何德旭,姚戰琪. 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效應、優化升級目標和政策措施[J]. 中國工業經濟,2008(5): 46-56.
[8]KUIJS L. How will China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J].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0(32): 1-32.
[9]郭熙保,朱蘭. 中等收入轉型視角下的中國需求結構演變[J]. 世界經濟文匯,2019(1): 1-16.
[10]CHANG T H, PETER J K.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The quarterly joumal of economics, 2009,124(4): 1403-1448.
[11]宋錦,李曦晨. 產業轉型與就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6(10): 38-57.
[12]劉亞琳,茅銳,姚洋. 結構轉型、金融危機與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J]. 經濟學(季刊),2018,17(2): 609-632.
[13]PENEDER M.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2, 14(4): 427-448.
[14]李雪冬,江可申,夏海力. 供給側改革引領下雙三角異質性制造業要素扭曲及生產率比較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35(5): 23-39.
[15]AMRITA R.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nd the service sector: evidence from Indian states[J]. Indian growth &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8(1): 73-92.
[16]劉奕,夏杰長,李垚.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制造業升級[J]. 中國工業經濟,2017(7): 24-42.
[17]HANLON W W. Human capital transferabil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C]// The Jerusalem Summer School in Economic Growth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Conference Proceedings. 2008.
[18]夏怡然,陸銘. 城市間的“孟母三遷”——公共服務影響勞動力流向的經驗研究[J]. 管理世界,2015(10): 78-90.
[19]JEROME V, AGHION P, MEGHIR C. Growth, distance to frontier and composition of human capital[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6, 11(2): 97-127.
[20]FUENTE A D L. Human capital in a global and knowledge-based economy, part Ⅱ: assessment at the EU country level[R]. 2003.
[21]唐東波. 擠入還是擠出: 中國基礎設施投資對私人投資的影響研究[J]. 金融研究,2015(8): 31-45.
[22]JOES M B, RODOLFO 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08, 20(2): 318-329.
[23]ACEMOGLU D,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chine and man: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6): 1488-1542.
[24]GROWIEC J, MCADAM P, MU′CK J. Endogenous labor share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8,87: 74-93.
[25]KARABARBOUNIS L, NEIMAN B.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1): 61-103.
[26]胡玉琴,胡玉萍,薛留根. 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系數測度方法的改進[J]. 統計與決策,2017(9): 5-9.
[27]BHADURI A,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4): 375-393.
[28]YU B, SHEN C.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capacity utiliz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46: 1-13
[29]KIRKIEY J, PAUL C J M, SQUIRES D.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common-pool resource industrie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22(1-2): 71-97.
[30]于斌斌,陳露. 新型城鎮化能化解產能過剩嗎?[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36(1): 22-41.
[31]單豪杰. 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算: 1952—2006年[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25(10): 17-31
[32]ACEMOGLU D , GUERRIERI V.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8, 116(3): 467-499.
[33]PREISSL B. The german service gap or re-organising the manufacturing-services puzzle[J]. Metroeconomica, 2007, 58(3): 457-478.
[34]劉航,孫早. 有偏技術進步與工業產能過剩——基于開放格局的供給側改革[J]. 經濟學家,2017(1): 47-54.
[35]劉和旺,鄭世林. 高技術產業化專項投資就業效應的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3(7): 47-60.
[36]朱平芳,王永水. 變參數狀態空間模型下服務業滯后效應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3,30(8): 51-64.
[37]FRANCOIS J, HOEKMAN B. Services trade and polic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0, 48(33): 642-692.
[38]HANSEN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Econometrica, 2010, 68(3): 575-603.
[39]魏后凱,王頌吉. 中國“過度去工業化”現象剖析與理論反思[J]. 中國工業經濟,2019(1): 5-22.
Ca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olve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YU Bin-binWU Yin-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imbalance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aused by the maladjustment of investment in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tial GMM estimation method to test the direct effec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nalyze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both.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resolv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but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influence pa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ineffici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hibit the effec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and the upgrading of human capital not only promotes the effect, bu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The result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shows that the resolving effect on overcapacity b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demonstrates an influence path of ‘promoting first and then restraining along wit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while the upgrading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hows an influence path of ‘restraining first and then promoting when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bove conclusions mean that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upgrading of human capital can be a new way of resolving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Key words employ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overcapacity
收稿日期:2019-10-17 修回日期:2020-01-25
作者簡介:于斌斌,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產能過剩與環境治理。E-mail:bxybby@163.com。
通信作者:吳銀忠,碩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能過剩與環境治理。E-mail:wyz429097426@foxmail.com。
基金項目: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新型城鎮化視角下化解工業產能過剩的機理與對策研究”(批準號:20NDJC12Z);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新型城鎮化下中國經濟增長路徑研究:基于結構調整與效率提升的雙重視角”(批準號:71703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