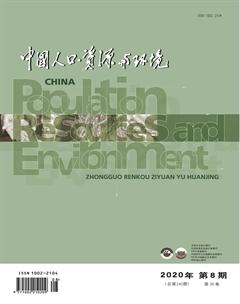政策與法律雙重維度下生態補償的法理溯源與制度重構

摘要 目前中國生態補償實踐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在部分領域已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法理研究比較薄弱,主要表現為對政策和法律層面運行邏輯的混淆,公法原理與私法原理的雜糅。生態補償政策與法律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當性。本文基于這一思路分析了政策和法律視角的生態補償制度現狀與原理,并以公法和私法原理解釋其制度邏輯,從而探尋法理基礎。生態補償政策的異化根源于傳統國家治理體制,目前以“項目制”行政撥款和治理方式為基礎,地方將中央撥付的補償資金用于環境治理后收到環境保護實效的同時,消解了中央撥付資金的意圖。在法律層面,生態補償并未產生規制行政權力以及調節私人利益的制度效果,導致法律調節長期被政策所主導,處于“失語”狀態。生態補償的法理探討應當區分公法規制與私法調節的范圍,在公法層面確定規制行政權力的基本理念,拓展行政補償的理念與實體制度范圍,并將其應用到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構建中;私法層面,應當在遵守公法設立的管制性規范的前提下,承認一定良好程度的生態環境的經濟價值和可交易性,進一步發掘合同法、物權法以調節個體環境利益的制度空間。在生態補償制度的完善方面,政策層面的生態補償應在明確事權劃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地方或區域環境協同治理的空間,法律層面應以立法為核心,行政補償進一步精細化,私法相關制度應體現“綠色”理念。政策與法律雙重維度的生態補償制度各自發揮功能,避免出現互相交織的局面,同時也為正在推進的《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撐。
關鍵詞 生態補償;權力規制;權利限制;生態服務付費
中圖分類號 D91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0)08-0148-10DOI:10.12062/cpre.20200311
中國的生態補償制度經過十幾年的探索,目前已經積累了較多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從各地的多種類型生態補償實踐探索,到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中一系列相關措施如環境資源產權制度等的推進,再到《生態補償條例》的論證起草,都體現了我國生態補償制度探索的重要進步,但同時也將我國生態補償制度的研究需求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基于目前的實踐探索和理論研究現狀,有必要對生態補償制度的法理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
2018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九部委聯合發布了《建立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行動計劃》,其中明確提出“要健全資源開發補償、污染物減排補償、水資源節約補償、碳排放權抵消補償制度,合理界定和配置生態環境權利,健全交易平臺,引導生態受益者對生態保護者的補償。”2019年11月15日,國家發改委印發《生態綜合補償試點方案》,確定十個省、自治區推行生態綜合補償試點,規定創新和發展森林、流域、生態優勢特色產業的生態補償制度,并“厘清生態保護補償主體和客體的權利義務關系,規范生態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明晰資金籌集渠道,不斷推進生態保護補償工作制度化和法制化”。從目前的實踐與理論現狀來看,生態補償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從政策與法律雙重維度進行分析,以求對其進行全面、系統定位。
1 撲朔迷離的生態補償制度范疇
概念界定是生態補償法理研究的起點,決定了生態補償制度的存在空間和基本范疇。對生態補償的概念進行規范的法學界定,進而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是環境法學者研究這一問題應當秉持的基本進路。在既有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生態補償的正當性如公共信托理論、外部性理論等以及制度運行層面如籌集資金、分配資金、政府間補償資金分配問題等等[1]。實際上,生態補償制度在如今的理論界更像一個“怪胎”,缺乏法理支撐,使得多種環境治理或資源市場交易均被冠之以“生態補償”,如環境治理與生態修復資金、資源產權交易、特定區域的保護與管護等,其范圍與手段幾乎可以運用到所有的環境治理措施中。在名稱上,存在“資金”“基金”“轉移支付金”“補助金”“補償費”等多種表述,在資金使用方式上,存在“獎勵”“補償”“賠付”等的混用。從表1可以看出,僅在中央立法層面,各類的資金名稱都不一致,且用途也多種多樣。地方立法中,情況更是復雜多樣。已有的法律解釋也僅限于“簡單套用法律關系分析、權利義務對等理論”[2]等資金分配描述,而非法律原理深究。
由于缺乏明確的概念界定,生態補償的制度范疇也十分模糊,目前正在推進的環境資源開發利用各類稅費試點與改革、環境資源產品交易、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生態環境
修復、中央的各類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保護方面的補助等等,均與生態補償制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不僅牽扯到法律制度體系內部本身的關系問題,更涉及法律和作為法律外部系統的政策體系之間的關系問題。
2 生態補償在政策與法律中的實踐樣態
我國立法中較多采用了“生態保護補償”的表述,《環境保護法》第三十一條、《水污染防治法》第八條均規定了“生態保護補償”,兩部法律規定該補償主要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等方式進行,《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一條則將其表述為“生態效益補償”。但值得注意的是,《環境保護法》第三十一條同時規定了“國家指導受益地區和生態保護地區人民政府通過協商或者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生態保護補償。”該規定可以說牽出了我國現階段生態補償在政策與法律層面的制度構建雙重路向,依此可檢視我國生態補償在實踐中的現狀。
2.1 生態補償政策的失敗與成功
我國當前的生態補償政策中,區域環境治理是生態補償的重要內容,尤其是重點生態功能區、飲用水源保護區等具有重要生態價值和功能的區域。從生態補償制度的功能需求來看,隨著我國環境資源保護和污染防治法律體系的逐漸建立與完善,對一般性、普遍性的環境問題的防治都可找到制度依據,但是部分特殊區域卻仍然面臨著制度缺位問題,特別是相關的環境經濟手段嚴重短缺。在此背景下,生態補償的實施成了保障環境治理目標達成的資金保障措施。其在一定程度上是為解決區域性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而提出的,根本目的是維護、改善或者恢復區域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但是,這種治理思維下的生態補償實踐具有濃厚的行政目標色彩。在《環境保護法》修訂之前,絕大多數生態補償實踐均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方式,這為地方環境治理帶來了顯著的影響。
目前中央偏重于以條塊分割為主要手段,用項目制治理方式分配資金,以形成治理合力,達到治理效果[3]。但由于環境資源的整體性,地方接受的中央下達的各類資金在使用上難免存在交織。地方財政部門在面對如此復雜的資金體系時,頻繁出現“拆東墻,補西墻”的方式靈活使用資金,使得本具有生態補償功能的資金在地方總是被集中起來解決最緊迫問題,導致中央用財政方式全面統籌治理和改善生態環境的方案落空。如某地同時獲得中央財政的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金和林業發展改革基金,地方獲得該基金后,通常將其集中統籌建設環境污染治理項目,這樣的情形在各地方并不少見。這使得中央通過轉移支付下達給地方的資金數額很難固定化,只能按照地方每年的花費酌情給付,與此同時,地方始終期待中央相對穩定的撥款。有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依現行耕地生態補償制度,實際生態補償資金遠遠小于應得補償[4]。因為受償主體太多、太復雜,而補償資金來源相當單一,這種粗糙的制度缺乏對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將制度構建的希望寄托在單一的政府財政上。這種現狀可能與我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起步階段密不可分,中央的生態補償專項資金到了地方搖身一變成為了集中建設特定項目的工具,各類資金之間的互相借用成為常態。結果是“地方政府通過多年制度性試驗,盡力爭取把問題擴大并上交中央,出現了國家財政為部分地區特別實施法律買單的現象,引起了地區性不平等。”[5]生態補償成了地方政府之間為爭取中央生態補償資金的博弈游戲。因此,由于地方政府對生態補償資金缺乏預測性,在補償資金分配和使用表現出極大的隨機性,加之其必須要面對當地復雜多變的環境保護基礎建設投資,導致經常出現借用資金的問題。
近年來,地方生態補償實踐開始出現了精細化發展的勢頭,主要表現為地方政府間達成的橫向補償協議,如省內以及省際流域生態補償中的“水質對賭”。省內的實踐以安徽省為典型:安徽省環保廳按斷面屬性,以環保部、省環保廳確定的監測結果,每月計算各補償斷面的污染賠付和生態補償金額。斷面水質某個污染賠付因子監測數值超過標準限值0.5倍以內,責任市賠付50萬元;超標倍數每遞增0.5倍以內,污染賠付金額增加50萬元;斷面水質類別優于年度水質目標類別的,由下游市或安徽省財政對責任市進行生態補償[6]。省際的“水質對賭”實踐典型的有江西和湖南于2019年7月25日簽訂的《淥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兩省商定:以位于江西省萍鄉市與湖南省株洲市交界處的國家考核金魚石斷面的水質為依據,實施淥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若金魚石斷面當月的水質類別達到或優于國家考核目標(Ⅲ類),湖南省撥付相應補償資金給江西省;若金魚石斷面當月水質類別劣于國家考核目標(Ⅲ類),或當月出現因上游原因引發的水質超標污染事件,江西省撥付相應補償資金給湖南省。補償資金實行“月核算、年清繳”[7]。在大氣污染防治中也有地區間空氣質量考核與補償制度,如2019年青島市生態環境局聯合市財政局出臺了《青島市2019年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方案》,這是青島市連續第6年出臺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方案,該方案“針對各區市主要污染物濃度和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情況,將每月公布上一個月改善程度及經濟獎懲結果”[8]。這可謂我國生態補償實踐的重大進步,地方不再拘泥于單純爭取中央生態補償資金,而是充分發揮地方生態環境保護的主動性,將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與當地政府間的財政資金分配通過協議的方式進行掛鉤,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研究表明,“實施跨省流域橫向生態補償是流域水污染強度下降的主要原因。”[9]同時,這也從側面反映出生態補償進一步精細化發展的趨勢,即更加注重區域間因環境保護力度與效果不同而采取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但應當做好與法律的功能銜接,利益的評價和歸屬問題不應當違反法律所規定的具體環境質量標準。
2.2 生態補償法治實踐的異化
我國立法除了規定構建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方式的“生態保護補償”制度之外,《環境保護法》第三十一條規定的“受益地區”和“保護地區”可以認為是法律賦予地方政府之間按照環境保護的目標進行利益分配的自由。我國目前的生態補償實踐主要由立法位階較低的部門規章、規范性文件或地方立法和規范性文件主導,在制度設計中表現為極大的不確定性。以森林生態補償為例,從2001年財政部頒發的《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資金管理辦法(暫行)》到2016年的《林業改革發展資金管理辦法》,共頒布過7個文件,補償基金名稱先后經歷了“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資金”“中央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中央財政林業補助資金”“林業改革發展資金”等表述方式。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生態補償機制也經歷了頻繁變動的過程,從2007年財政部頒布的《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財政專項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到2015年財政部、環境保護部頒布的《水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管理辦法》(2016年修訂,至今有效),共發布過六次不同的文件,每一次頒布新辦法的同時廢止舊辦法。這反映出在缺乏一般法律原理的指引時生態補償資金撥付管理機制的隨意性。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生態補償制度的法理旨趣并未被完全揭示,既有的法律體系中生態補償難以正常“歸位”,導致生態補償制度長期游離于現有的法律體系之外,成為一種多用途的、沒有制度邊界的替代性政策工具,在地方實踐中往往被當地政策吞噬,喪失了法律調整的基本功能。在“生態補償”的語義構成中,“生態”注重環境公益的維持或提升,“補償”注重對個體利益的平衡與協調,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生態補償制度的運行目的。區分環境公益與個體利益區分的功能就在于,二者的法律調整原理有所不同,環境公益主要通過制定政策或行政法定職權行使等方式實現,而個體利益的保障與調節應當盡可能地訴諸法律途徑。這就決定了在研究生態補償的制度構建時必須兼顧政策與法律之運行邏輯與原理,使得二者在合理的空間內各自發揮作用。可以認為,目前我國的生態補償法治實踐出現三個方面的異化:一是側重于實現短期的環境污染治理而非環境質量維持或提升的長遠目標,二是側重于整體性生態環境質量而非個體生存發展利益保障,三是忽視對限制個體權利過程中行政權力的行使進行必要的規制。因此可以說,生態補償制度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一種對既有環境保護制度運行失靈的補救措施[10]。
上述對近現代行政法有關補償問題的基本脈絡梳理可以看出,在對私有財產權進行限制并予以補償與限制行為本身的限度有直接關系。反觀生態補償中行政機關因生態環境保護而限制私人財產權的行為(如限制生產規模、限制排污量、限制采伐或開采量等),從近現代行政法對補償范圍的擴張解釋可以看出,這無疑是屬于行政補償的范疇,在未來相關立法中應當予以確定。但是生態補償中的權利限制的重要特殊性在于其更多是對發展機會的剝奪,如禁止特定類型的開發利用行為、特定區域禁限制開發等等。
3.1.2 補償與否的判斷基準:義務排除補償
在公法層面,補償與否的判斷標準與權利限制的合法性、正當性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均與行政機關限制權利的法律依據有直接關系。但是,在補償與否的判斷方面,還要考慮權利主體,主體獲得生態補償金應當以其履行義務為基本前提。主體履行公法設定的相關義務的行為,雖然表面上看是其權利受限、發展機會的喪失,但在實質上是義務內核,應當被排除補償范圍,以此來厘清生態補償與損害賠償、損害修復之間的界限,將其限定在正外部性的范圍內。至于該義務如何界定,環境標準可以作為權利限制的正當性界限并進而決定是否給予補償的重要依據。以水質標準為例,基于水質提高的需要,在履行了一般義務的基礎上基于“協議水質”,即流域上下游政府在達到“強制性水質”的法定責任之后,可以通過平等協商按照“保護者受益,受益者補償”的原則,對超過“強制性水質”標準部分的額外優質的水質承擔補償責任[19]。權利主體履行法律規定的合規排放義務、遵守核定的重點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標而導致的財產損失和喪失的發展機會均不屬于補償的范圍。
綜上,公法中的權利限制與補償在維護生態環境質量的目標上并不充分,因為該層面的生態補償實質上還是僅限于對生態環境資源經濟價值的開發利用主體層面,并不能主動發起對生態價值的享用和維持的交易以充分發揮權利主體參與的制度空間,這就可能使得生態補償存在生態效益維持或提升的空白地帶,該部分應當交由私法制度處理。
3.2 私法層面:利益的法律調節
傳統的規制目標存在“規制的公共利益理論”,該理論認為,在公法上,為行政決定過程所創造的一套精細的制度結構,尤其是司法審查和公眾參與,只要其所施行的政策和實踐能夠促進“全體公民的福利”,則該制度設計就是合理的[20]。這種理念在環境法研究中表現得較為突出,在公共利益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對私益的調節在法律層面的關懷明顯不足。以治理手段替代利益調節目的的生態補償制度就是公共利益保障的正當性掩蓋了私益調節的客觀需求。在該思維下,生態補償的資金轉移往往通過縱向或橫向的財政轉移支付為主要形式,以解決特定區域環境治理過程中的資金問題,其資金如何精確補償生態價值產生的微觀原因方面并沒有明確的制度實踐。因此,缺失對私法層面相關主體利益關系的認知,導致公法層面的行政權力限制私主體權利的行為也無法納入法律規制的范圍,這進一步導致生態補償的利益調節功能長期被排擠出制度實踐范疇。我國現行的生態補償制度實踐實質上是以政府統籌資金的方式,以既有的開發利用權利的行使將資金的使用進行了合理化分配。由于政府主導的生態補償的對象僅僅為整體性生態效益,所以單純的生態補償制度有可能也因為資金短缺而難以為繼。雖然政府對生態服務的直接支付是改變生態系統服務損失的誘因,但不能被視為保護的靈丹妙藥[21]。
生態補償的利益調節主要針對的是在區域環境治理中因環境目標維持或提升而引發的經濟利益失衡問題。必須認識到,因生態保護需要而對個體權利進行的限制對不同類型的開發利用主體來說并不在同一個起點上。生態補償規則之設計在對權利限制的性質進行定位之后,應當進一步解決所限制的權利來源問題。對權利限制是否給予補償的核心問題不應當局限于傳統公法中的“特別犧牲”“財產權的社會義務”“警察權”“管制性征收”等公法層面的理論框架,更應該上溯到私法中權利的源頭,從權利的來源問題上對限制問題進行更為基礎的解釋。現有研究已經提出過生態補償實質上就是權利受限導致的發展權喪失[2],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系統的論證,建議設立一種發展權性質的生態補償權利[3]。這些研究均在為生態補償在微觀主體層面發揮利益調節功能尋找正當性基礎,體現出生態補償制度法理研究的重要進步。
3.2.1 法律調節的前提:遵守管制規范
生態補償的對象為正外部性,在法律調節中體現為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主體的權利受限在符合管制性規范基礎上更進一步施加的權利負擔。該負擔已經超出權利主體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特別犧牲”,屬于“外部限制”,因此需要啟動法律的二次分配,給予補償。平等的民事權利主體之間的生態服務交易必須在符合公法管制規范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環境質量而產生的利益失衡問題,應當落入私法調節的范疇。
3.2.2 補償的標準:意思自治
由于私法中的補償是以遵守公法管制規范為前提的,因此,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補償標準除了政府給予技術指導之外,更多靠民事主體之間的意思自治進行平等協商。在交易成本較低、發生交易成為可能時,民事主體可以在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的前提下,理論上可以達成補償標準的共識。
4 生態補償在法律制度的實現路徑
4.1 公法中的補償
環境治理要認識到以人類、社會、公共為名的各種抽象的整體性利益與各種具體利益、個體利益的復雜關系,認真考慮不同群體的環境代價并予以平衡與補償[22]。所以,生態補償不應當淪為針對生態破壞而采取的被動性宏觀治理的資金保障措施,它“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平衡與利益補償機制”[2]。從環境法本身的屬性分析,檢驗環境法是否為良法的標準應當在于“其是否能夠為人的體面生存與發展的實現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和可持續的大舞臺。”[23]因此,在生態補償法律制度中,行政機關實質上是在面對和處理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是為了彌補單純考量環境質量的提升而忽視對個體利益照顧不周的制度缺陷。
環境法在利益調節方面的理念是“‘兩害相比取其輕,是強調損失最小化”,損失最小化包括兩個要素:“一是確實受到損失,而且這個損失是必須付出的;二是損失是他人的所得,利益的獲得者必須支付對價”[24]。
首先,權利限制應當按照一定的價值位階進行。公法被認為是利益分配的“排序法”,即“按照對其價值的權衡而優先保障某些人利益的法律”[24]。因此,在權利限制方面,行政機關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性,按照一定的原則進行利益分配的“排序”,如生存權優先保障、其他類型的利益實行緊缺利益優先等。該類限制立法僅能做原則性規定,司法也不宜過度侵入該領域。
其次,公法應當確立對行政權限制私主體權利行為的規制規則。該規制規則必須以對環境資源開發利用行為的類型化為基礎。這一問題至關重要,也十分棘手。對企業基于經營獲利的排污與個體基于生存發展的種植、養殖行為背后的權利限制并不能等同對待,對當前開發利用者的限制和對未來開發利用機會的限制同樣不能等同對待,這也是環境法領域利益分配的難點所在。陳慈陽將環境保護領域行政權力對基本權的限制區分為三類:對作為基本權利的財產權形成的限制、對執業自由的限制和職業選擇自由的限制。三者在法律體系中分別需要立法確定補償、理性與無恣意的憲法法益衡量、顯著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相應的,三類限制行為中,司法審查密度越來越嚴格[25]。由于環境法中并沒有建立起系統的環境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多種類型的環境資源開發利用行為對相應主體生存發展的影響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均存在著十分顯著的差別。因此,對環境質量目標達成過程中的行政權力的規制應當走向精細化、類型化。
4.2私法中的利益調節
由于公法中實難確定補償的標準,此時可以轉變思維,可以充分利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則消解掉公法層面中是否予以補償以及補償標準的確定等復雜的技術難題,將復雜的權力——權利關系化約為民事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具體路徑有兩種:一是將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本身作為獨立的標的進行私法交易,通過政府的管制措施設立生態環境服務的可交易性,并將其納入私法交易的范圍中;二是將良好的生態環境質量所依附的環境資源物權的行使相關聯,將良好生態環境質量所代表的經濟價值與物權客體打包處理。因此,前者屬于合同法調整的范圍,后者屬于物權法調整。
4.2.1 合同法調節
未對公民設定環境權利并不意味著相關利益在法律中就得不到體現。此時可以透過權利外表,對于不能直接支配的利益客體,雖然不能設定權利,但是可以直接分配利益客體本身[26],即賦予相關主體一定限度內對該利益客體的行動自由以取得獲取該利益的可能性。通過私主體的契約自由,在不違背公共利益(一般為特定的環境質量)的情況下,直接將生態利益背后的生態效益的維持或提升作為交易的對象,法律僅需承認這種契約的法律效力,即告完成對生態效益維持或提升的保障。該措施可克服生態補償法律構成中必須以資源的經濟利益為中介保護生態環境的效果有限性。“生態服務付費”(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services, PES)是21世紀在國外興起的一種協調生態利益享用與開發利用之間沖突的制度,拉丁美洲的實踐較為充分,有超過15個國家實施了某種形式的生態系統服務計劃,其實踐在哥斯達黎加最為成熟[27]。“生態服務付費”的核心思想是,環境服務外部性的受益者對當地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的直接的、約定的有條件的付費以換取生態系統保護和恢復可接受的行動,……其并不預設雙贏的解決方案,而是明確地認識到很難權衡土地開發利用壓力下的生態環境,并通過尋求補償來調和利益沖突。其主要針對四種生態服務:①碳封存和儲存(例如北部電力公司向熱帶農民提供種植和維護額外的樹木);②生物多樣性保護(例如,保護捐助者為當地人民留置或自然恢復地區創建生物走廊);③流域保護(例如下游用水者向上游農民收取限制砍伐森林、土壤侵蝕、流失風險等的土地利用限制費用);④景觀美化(例如,支付當地社區的旅游經營者不要在被用于游客觀賞野生動物的森林中捕獵)[28]。理想情況下,生態服務付費將阻止服務提供者搭便車,或服務受益者傾向于利用環境服務而不提供公平的補償[27]。“將環境相關權利的交易納入有名合同的調整可以充實當事人權利內容,事實上擴充民事主體意思自治的范圍和空間。”[29]但由于涉及的關系較為復雜,該制度也具有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在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直接公開購買土地來保護資源似乎要比生態系統服務收費中購買有限的土地使用權更加合理[28]。這是生態系統服務受合同法調整的重要障礙。該制度與我國生態補償的“受益者付費”理念一致。當然,交易的前提是維持或提升生態效益,所以在交易的范圍上,只有當對服務提供構成威脅的活動是合法的,政策制定者要求績效高于現行標準時,才應適用這一政策。否則,解決的辦法就是現行法規的執行[30],這也與生態補償的范圍相暗合。所以,廣義上講,這也可以構成我國生態補償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
4.2.2物權法調節
生態補償背后的利益受物權法調整是著眼于作為環境資源的“物”不僅具有經濟價值,更具有生態環境價值。“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均為同質同源的正當利益,不能輕言環境利益優先或經濟利益優先,應當通過兩種利益的共生協調和雙贏。”[31]生態補償直接作用于環境質量的提升,而忽視了環境資源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必要的因果聯系。生態補償是將對環境資源的實在性開發利用行為指向資源的經濟價值產生的外部性(含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進行內部化的方式,是在國家代表公共利益對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追求過程中造成生態價值減損后果的權利進行的限制。該過程中,環境資源以經濟價值的存在方式進入到開發利用權利層面,并以對開發利用權利限制的方式維持或提升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在生態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以維持或輸出生態效益的方式實現生態補償的目的。
(1)“生態惠益”的物權登記。通過物權法的相關制度調節利益的限度和范圍依附于特定的環境資源物權,即在環境資源開發利用過程中對經濟價值的影響。在經濟價值的獲得方面主要是通過對既有的實體權利起到前提性作用,如物滿足最基本的經濟利用價值,或者對物的經濟利用價值起到增進和保障的作用,即在滿足物的最基本的可使用性所需要的生態價值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升,借以提升物的附加價值。在養殖業中,環境質量更高的環境中出產的畜禽比環境質量較差的環境中出產的畜禽經濟價值高,此時的環境利益直接體現為對開發利用權利人直接收益的提升;在精神性的享用方面,實質上環境利益還是圍繞著物權法中的提升“物”的利用價值的,環境質量越好,對人類的滿足程度越高。所以,在同等條件下,依附于環境資源本體的環境質量更好,其物權客體的價值也就越高。將棲身于物權的具有實在經濟價值的環境利益有必要在法律中進行識別并分配,該種利益可稱為“生態惠益”[32]。
由于生態環境質量所代表的利益并未上升為私法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此,在相關主體因生態環境保護而付出代價,而另一些主體則享用生態惠益的情況下,不能因缺乏法定權利為由終結生態惠益在法律制度中表達。此時,可依附傳統私法體系建立起來的權利體系直接分配該利益。具體做法為,在不動產登記簿中載明自然資源客體之上生態惠益狀況,進而通過物權意思使環境生態惠益在傳統物權中予以實現[32]。在自然資源統一確權登記表中,在記錄自然資源的邊界、面積、用途等基本情況的情況下進一步明確記錄該自然資源的環境質量狀況、環境承載力狀況以及審美等方面的享用價值,一方面將生態惠益融入物權法所確認和調整的范圍當中,另一方面則有利于在一定的時間節點上確定自然資源的生態狀況,以便掌握生態效益的維持或提升狀況以及權利主體的享用情況。當然,該意義上利益調節僅僅限制在生態環境對物的價值提升的范圍內。
(2)地役權。學理上提出的“公共地役權”“法定地役權”“環境地役權”以及美國的“保存地役權”等均與我國生態補償的功能有所契合。該類地役權實質上已經脫離了私法中地役權的基本理念,成為政府對私人財產權行使的環境管制,只是該類管制對象已經超出了傳統行政法中“不當行為”的標準而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在法國,公共役權主要是公共工程需要而對私人土地的臨時占用,稱為“臨時占用役權”[33]。環境資源上可以同時存在公共地役權與私法權利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利,私法物主的私法財產權只在不損害公共地役權的范圍內才存在,因而是一種“剩余財產權”[34]。也有觀點認為,我國目前所實施的生態效益補償措施與地役權的制度邏輯有所契合[35]。客觀上,地役權與生態補償的確存在功能上的重合。但是由于地役權是以土地為核心展開的,并不能完全適用于生態效益保護中產生的利益調節需求。但是地役權在私人之間達成協議的范圍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義卻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地役權范圍擴張的趨勢下,在地役權中融入權利主體環境保護的公法義務不僅有利于形成對個體財產權受侵害的防御功能,而且有利于“以公法的私人實施手段提高行政行為的執行效率,降低行政執行成本”[34]。
5 生態補償政策與法律的發展與完善路徑
建構復雜性的前提是以一定的原理解釋復雜現狀背后的共性問題,以減小復雜性,要將復雜的主體和利益關系問題化約為法律規范話語體系的分析對象。基于前文對生態補償政策與法律調節基本原理的分析,立足于生態補償制度的多重目的,其保障環境公益的功能與調節因此而產生的私益關系的功能在政策和法律互相銜接和支援的理想狀態下應當同時得到彰顯。“只有當各方相互妥協而在生態服務的法律和政策上達成一個緊密結合和強有力的制度體系,并且開始把生態服務與資源性產品、制造的產品和由人提供的服務融合成一個完整的框架,那么,所有與之相關的一切爭議才會平息。”[36]政策擅長以靈活多變的方式(如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環境資源開發利用規劃、產業政策、市場激勵、技術指導、稅費優惠等)保障環境公益利益,而法律則應側重于以相對確定的原理和穩定的機制調整復雜的利益關系,二者在運行過程中應當在區分功能的前提下各自發揮作用,雖然可以產生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作用,但這是基于二者的相對獨立運行為前提,不應當過度交織。
5.1 政策發展方向:事權劃分相對明確化
政策層面的生態補償由政府按照既定的財政體系分配生態補償資金,而財政支出責任的劃分以事權的明確劃分為前提。從目前的生態補償資金撥款情況來看,上級政府向下級政府撥款的不確定性是影響生態補償制度化的最大障礙,資金撥付缺乏穩定性必然導致資金使用的隨意性。因此,生態補償“以政府補償為主導,以厘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職責為關鍵。”[37]按照我國目前的體制,除了外交、國防等極其典型的事權歸中央外,其余事權幾乎都屬于中央和地方共享[38]。該背景不變,生態補償的政策不會發生根本變化,只能繼續依托現行的行政發包性質的“項目制”。因此,首先,特定區域、流域治理是政策方式的生態補償發揮環境保護功能的主陣地;其次,政策應當進一步厘清與法律調節的范圍,將符合法律調節的范圍“交還”給法律。
5.2 法律制度完善的路徑
政策以政府在特定領域治理的專業性為支撐,對法律制度的定型和演進起到先導和指引作用。生態補償的法理正當性源自其與法律在功能上的耦合,并通過環境政策法的形式對抽象性環境政策進行立法確認,從而使國家環境保護的基本價值理念和方向得到法律的正式宣示[39]。因此,在生態補償制度法律調節的推進進程中,立法是核心。立法需要解決的問題首先需要將行政補償進行精細化研究,明確傳統行政補償適用到生態補償中的缺陷,明確事實上的“管制性征收”的范圍,并將對私權限制的權力行使納入法律規制范疇。在此基礎上,《生態補償條例》應當以行政補償基本理論為根基構筑起生態補償的基本法律規則,民法典合同編以及物權編應當融入環境保護的相關制度以體現“綠色化”理念。至于目前倡導較多的市場化補償、社會化補償等應當落入政策調控范疇。
生態補償制度從提出到十多年的探索,其制度原理尚未被完全挖掘出來,這與我國傳統的國家治理體制密不可分,同時,我國傳統部門法理研究的匱乏也是重要原因。在實際操作層面,仍然有十分巨大的理論研究空間。在制度構建中,必須首先解決的是與既有法律制度體系的兼容性,這一點十分重要,本文就是在做這樣的探討。從本文對國外和我國的生態補償原理探究可以看出,國外很少有對生態補償理論的系統論述或專門制度的實踐經驗,其原因是我國的生態補償已經于功能上在其公法或私法領域中得到了體現。現實中出現的因生態效益增量的激發而實行的環境管制或私法中的PES與地役權均可涵蓋生態補償的客觀范圍。但是,由于我國的環境法律體系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各項資源的保護均散見于各類型、各位階的法律文件中,因此,生態補償法律制度仍然有存在的空間。基于此,筆者大膽揣測生態補償在我國未來發展的趨勢:如果現有的公法與私法體系依本文的設想完全融入生態補償理念,那似乎意味著生態補償已經被現有法律制度所“吞噬”,成為一種統合各類為保護生態而產生的利益調節相關制度的概念;但如果生態補償制度另辟蹊徑,比如以發展權等作為理論根基進行重新構建,將有可能在法理上貢獻重要觀點。但可以確定的是,依據我國目前的實踐樣態,生態補償制度的構建與完善應當以既有的國家治理體系和現有的法律制度為基本背景,應當正視政策與法律各自的作用范圍,不可輕言一味用法律調節吸收政策調節,也不可以政策方式完全抹殺法律調節的空間,二者各自發揮功能才是生態補償制度的合理運行方式。
(編輯: 劉照勝)
參考文獻
[1]李愛年,彭麗娟.生態效益補償機制及其立法思考[J].時代法學,2005(3):65-74.
[2]史玉成.生態補償的法理基礎與概念辨析[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6(4):9-16.
[3]杜群,車東晟.新時代生態補償權利的生成及其實現——以環境資源開發利用限制為分析進路[J].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2):43-58.
[4]劉利花,楊彬如.中國省域耕地生態補償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2):52-62.
[5]高利紅.論財政體制與我國環境法的實施責任——以丹江口市為例[J].法學雜志,2016(3):8-18.
[6]孫振.安徽推行“水質對賭”生態補償模式[N].人民日報,2018-01-12(04).
[7]魏星.贛湘簽訂淥水水質“對賭”協議[N/OL].2019-07-26[2020-1-5].www.jiangxi.gov.cn/art/2019/7/26/art_393_706984.html.
[8]青島2019年環境空氣質量生態補償方案出爐[N/OL].2019-05-08[2020-01-05].http://www.qingdao.gov.cn/n172/n1530/n32936/190508090156939802.html.
[9]景守武,張捷.新安江流域橫向生態補償降低水污染強度了嗎?[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8,28(10):152-159.
[10]車東晟.論我國生態補償法律化的原理與規范路徑[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8(3):146-156.
[11]彼得·S.溫茨.環境正義論[M].朱丹瓊,宋玉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張翔.財產權的社會義務[J].中國社會科學,2012(9):100-119.
[13]理查德·A·艾珀斯坦.征收——私人財產權和征用權[M].李昊,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4]丹尼爾·H.科爾.污染與財產權——環境保護的所有權制度比較研究[M].嚴厚福,王社坤,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5]陳新民.德國公法學基礎理論[M](增訂新版·上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6]劉連泰,劉玉姿,等.美國法上的管制性征收[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7.
[17]丁文.物權限制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18]張翔.機動車限行、財產權限制與比例原則[J].法學,2015(2):17.
[19]杜群,陳真亮.論流域生態補償“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基于水質目標的法律分析[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4(1):9-16.
[20] AUSLANP M. Public law and public choice[C]//安東尼·奧格斯.規制:法律形式與經濟學理論[M].駱梅英,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56.
[21]STEEDB C . Government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lessons from Costa Rica[J]. Land use & environmental law, 2007,23(1):177-202.
[22]鞏固.環境法律觀檢討[J].法學研究,2011(6):66-85.
[23]柯堅.生態實踐理性:話語創設、法學旨趣與法治意蘊[J].法學評論,2014(1):75-81.
[24]李啟家.環境法領域利益沖突的識別與衡平[J].法學評論,2015(6):134-140.
[25]陳慈陽.環境法總論[M].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
[26]胡靜.環境法的正當性與制度選擇[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27]BOLLMAN M, HARDY S D. Institutional rules in ac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osta Rica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programme[J].Carbon & climate law review, 2011(3):357-370.
[28]WUNDER S. 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some nuts and bolts[R/OL].[2020-01-04]https://www.cifor.org/publications/pdf_files/OccPapers/OP-42.pdf.
[29]劉長興.論“綠色原則”在民法典合同編的實現[J].法律科學,2018(6):131-140.
[30]STANTONM S. Payments for freshwater ecosystems servic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J].Hastings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2012,18(1):189-290.
[31]李啟家,李丹.環境法的利益分析之提綱[J/OL].(2003-10-24)[2019-12-25].http://www.riel.whu.edu.cn/view/3602.html.
[32]杜寅.環境生態惠益的物權化研究[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4):18-26.
[33]王名揚.法國行政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4]耿卓.我國地役權現代發展的體系解讀[J].中國法學,2013(3):85-97.
[35]唐孝輝.濕地資源保護的物權法進路[J].理論月刊,2015(6):94-98.
[36]J.B.魯爾,斯蒂文·E.卡夫,克里斯托弗·L.蘭特.生態服務的法律和政策[M].楊代友,付瑤,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6.
[37]王清軍.生態補償主體的法律建構[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1):139-145.
[38]劉劍文,侯卓.事權劃分法治化的中國路徑[J].中國社會科學,2017(2):102-122.
[39]郭武,劉聰聰.在環境政策與環境法律之間——反思中國環境保護的制度工具[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4(2):134-140.
The legal 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under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olicy and law
CHE Dong-sheng
(School of Economic Law,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nxi 710063,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th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some fields, but jurisprudence research in this respect is relatively weak,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operation logic atthe policy and legal levels, and the mingl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The policy and law 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ve their legitimacy and necessity to exist. Based on this ide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principle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nd law, and explains its institutional logic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so as to explore its legal basis. The detachment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At present, based on the ‘project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appropriation and governance methods, when local governments use the compensation funds alloca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achiev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dispell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intention of allocating funds. At the legal leve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has not produced the institutional effect of regula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adjusting private interests, resulting inlegal regulation being dominated by policies for a long time and in a state of ‘aphasia. Hence, the discussion on the jurisprudence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hould focus on distinguishing the scope of regulation by public law and of adjustment by private law, determine the basic concept of regula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at the level of public law, expand 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and the scope of entity system, thus applying i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t the level of private law, to a certain extent, economic value and tradability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should be recognized on the premise of observing the regulatory norms established by public law, and Contract law and Property law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to adapt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of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t the policy level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space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locally or regionally on the basis of a clear di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t the legal level, legislation should be the core,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being further refined, and relevant system of private law should reflectthe new principle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with dual dimensions of policy and law functionsrespectively to avoid the intertwined situ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at are being promoted.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wer regulation; limitation of right; payment for ecological service
收稿日期:2020-01-16 修回日期:2020-03-30
作者簡介:車東晟,博士,博士后,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E-mail:cdscmd@163.com.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基本路徑和法律樣態研究”(批準號:19VHJ016);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第64批面上資助項目“我國生態補償法律調節的基本原理研究”;西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地方不良資產管理法律問題研究”青年學術創新團隊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