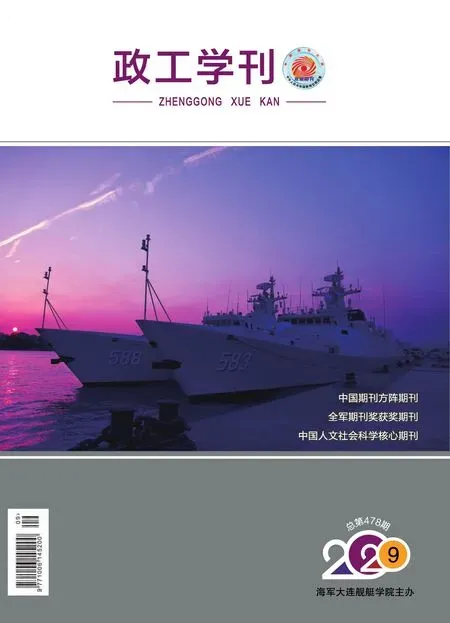“拔高”的稱謂難消受
☉鐵 坑

不明職務的領導怎么稱呼?交往之中,許多人都曾遇上這個難題。“稱謂喊高了總比喊低了強”,持這種觀點的并不少。
稱呼什么,既反映對方的身份、地位和職業,又體現自身修養。因此,稱謂必須符合實際、準確適當。如果故意“扶正”、刻意“拔高”,若非成心調侃,便有諂媚之嫌。而自己被冠以“過大的帽子”,卻沒有足夠的清醒甚至飄飄然,則有招媚之心。
《聊齋志異》有一篇名為《夏雪》的文章,便借關于稱謂的一件小事,生動而深刻地諷刺了權貴場“要高帽子戴”的現象。丁亥年七月初六,蘇州降下大雪,百姓驚恐,趕往廟里祈福消災。沒想到,上仙真有感應,附體在一個人身上說:“如今稱老爺,前面都要加一個‘大’字。難道你們認為我是小神,消受不得一個‘大’字?”百姓悚然,齊呼“大老爺”,雪馬上就停了。蒲松齡感慨:“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連神仙都喜歡諂媚,難怪為官的門前車馬往來、川流不息了。
稱謂有“輕重”,因時而不同。比如,“大人”的稱謂,最初只用于王公貴族、父母長輩,后來在使用中層級逐漸下移、范圍不斷擴大。如此一來,嫌“大人”不足分量、不夠尊貴的,便有人在。
稱謂之所以就高不就低,一方面是怕遇上那種嫌你給他戴的“帽子”不夠大的上司,他給你扣的“帽子”就大了:不懂禮貌、不明事理,目中無人、不敬上級。另一方面則是諂媚心理、語言賄賂,目的在于贏得好感、拉近距離。這種“慷慨”看似與金錢物質毫不相干,但投機取巧的心態暴露無遺。
稱謂的流動性,在清代王士禎的《居易錄》中可見一斑。他說:“京官各衙門相稱謂,皆有一定之體。蓋沿明舊。如內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中曰掌科,御史曰道長,吏部曰印君……余己巳年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老先生者矣。”這里的己巳年,是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年后的光景又不同,王應奎談道:“今則一登兩榜,未有不‘老先生’者。”
“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為什么官員的“帽子”會越戴越大?因為拔高的稱謂、諂媚的稱呼,權貴們聽得舒服、欣然領受,慢慢地流行開來、人人效仿。而一旦用的人多了,該稱謂便又顯得輕飄了。對于這種現象,蒲松齡感嘆:“竊意數年以后,稱爺者必進而老,稱老爺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稱謂之中見風氣。對上級的稱呼“層層逐高”,會助長官僚主義、投機主義。被恭維者欣喜、刻意討好者得利,對權力的認識就會扭曲,權力的行使就會跑偏。“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任憑這種現象泛濫橫流,風氣豈能不壞、規矩怎能不亂?“拔高”的稱謂難消受,為政者都要有這個清醒認識。
鄭逸梅《清宮軼事》中載,御史湯倓為了奉承雍正,稱皇上是“太陽之光”,臣下是“燈燭之光”。雍正向來崇尚務實,其間的諂媚之音、取巧之意豈能聽不出?他說:“太陽與燈燭各有其實、各有其用……如果借上奏之機,行營私之計,那就是在‘太陽底下點燈燭’。如此,豈非自尋羞辱?”湯倓聽罷,羞愧而退。
拒絕“高帽子”,對于上級來說很難得,對于下級而言更可貴。唐朝的張說懸鏡待人、佐佑王化,玄宗想封他為“大學士”。張說一聽,趕緊推辭:“學士從來就沒有‘大小’一說,大學士之名我可擔不起!”
我們黨有互稱同志的好傳統。以“同志”為稱謂,有利于增加信任、凝聚共識,也有利于純潔關系、提醒責任,既不拔高又很崇高。因此,在我們黨內,無論是否知曉對方職務,互稱同志都是一種很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