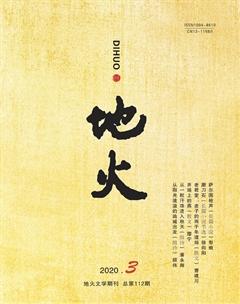逆行者
悅仲林
上世紀(jì)80年代和90年代,我們在烏魯木齊石化總廠化肥廠干的許多工作,以現(xiàn)在的標(biāo)準(zhǔn)看肯定是違規(guī)蠻干,是絕對不允許的。但套用正面的一個詞來說,我們曾經(jīng)是“逆行者”。
烏石化大化肥是國家重點項目,需要很多人。除了計劃分配來的我們這批77、78、79級大學(xué)生以外,還從前十三套大化肥工廠調(diào)了一批技術(shù)人員和熟練工人。改革開放初期,許多人奔往沿海城市、開發(fā)區(qū),而有一批人選擇了逆行。像我一樣來自內(nèi)地的,是計劃分配到新疆的,計劃經(jīng)濟時代,必須來。還有新疆籍的大學(xué)生是“哪兒來哪兒去”,占了來廠學(xué)生的大多數(shù)。調(diào)來的這批技術(shù)人員和熟練工人,他們拖家?guī)Э趤頌跏彩菫榱私鉀Q家屬的城市戶口。他們主要來自瀘天化、川化、齊魯石化、滄州大化、赤天化等大化肥廠和興平等幾個中型化肥廠。
烏石化大化肥項目,是以減壓渣油為原料生產(chǎn)合成氨和尿素的大型化工裝置,年生產(chǎn)30萬噸合成氨、52萬噸尿素,技術(shù)條件苛刻,操作和維修難度遠(yuǎn)超前十三套大化肥裝置。在試車和轉(zhuǎn)入正常生產(chǎn)過程中,我們經(jīng)歷過九九八十一難。春耕秋播正需要化肥時,可能突遇停工生產(chǎn)不出產(chǎn)品。我們急,自治區(qū)領(lǐng)導(dǎo)也急,要求每天匯報生產(chǎn)恢復(fù)情況。而我們終于創(chuàng)造出輝煌的歷史,廠里許多人受到自治區(qū)領(lǐng)導(dǎo)的接見和表揚。其中,來自內(nèi)地這批人的貢獻(xiàn)讓我久久不能忘懷。冉師傅是鉚工,在現(xiàn)代化化肥廠就是拆卸和安裝靜設(shè)備的。在一次氣化爐底部拆卸法蘭清渣的工作中,被噴出的高溫炭黑水燙傷,在醫(yī)院一躺就是許多年。李師傅電焊水平高,但不是在制造精密設(shè)備,而是冒著噴火爆炸的危險焊接堵漏,在漏洞周圍堆一點兒焊肉,尖錘往洞口敲一敲,再焊再敲,直到堵住。黃師傅當(dāng)班長十幾年,都50多歲了還一直在倒班,盧廠長獎勵了他一輛自行車,在廠里成了大新聞。盧廠長,是從縣級化肥廠調(diào)來的工程師,當(dāng)上廠長后仍經(jīng)常坐在總控室,停工開工的關(guān)鍵時段,腿都坐腫了,一按一個坑,他還在那里陪著。十幾年后,我到上海看望在公司總工程師崗位退休的盧廠長,他穿著大褲衩接待我們,老伴兒長期癱瘓在床,他除了陪著什么也干不了。工會于主席、程副廠長、郭科長、徐邦彥等這些管理和技術(shù)人員,帶來了兄弟單位的管理方法和經(jīng)驗,推動工廠檢維修工作走上了正軌,為邊疆的化肥事業(yè)做出了貢獻(xiàn)。他們已在新疆退休,成了永遠(yuǎn)的普通的“逆行者”。
李師傅堵漏采用的是傳統(tǒng)方法,單兵作戰(zhàn),我們還有多專業(yè)堵漏的許多例子。比如,有一年大檢修后開工剛出產(chǎn)品,外單位檢修的鍋爐人孔法蘭漏氣了,正壓鍋爐,內(nèi)墊的幾層隔熱材料很快就被吹沒了,人孔蓋隨即被燒得通紅。按現(xiàn)在的要求,安全第一,肯定是停工重修。那時的觀點和實際是,帶壓搶修,否則停工重修再開工,損失物料,還要花至少一周的時間。我?guī)煾祩冏隽艘粋€大的方盒子,正面帶排氣閥門,頂板先不焊接。然后,將方盒罩在人孔蓋上,三面先焊,上面灌耐火水泥,最后焊上頂板。搶修前火已通過法蘭往外噴,安全處長和總廠領(lǐng)導(dǎo)勸我們放棄,我們堅持試試再說。在消防、安全人員、總廠領(lǐng)導(dǎo)的監(jiān)督下,悶熱的鍋爐房里,安裝鉗工、焊工、筑爐工、保溫工、起重工一起行動,最終封堵了人孔,保證了生產(chǎn)的繼續(xù)。此處搶修還沒結(jié)束,另一臺鍋爐人孔法蘭也漏了。同樣的原因、同樣的方案、同樣的搶修,不同的是其他人都放心地散了,留下我們奮戰(zhàn)一宿,同樣封堵了人孔。
90年代初,新型帶壓堵漏方法出現(xiàn),北京總公司設(shè)備部門還舉辦過培訓(xùn)班。簡單說,就是做一個耐壓金屬卡套,卡套上留幾個注膠接頭,搶修時將卡套套在泄漏處,然后用高壓油泵將膠注入卡套內(nèi),不斷注膠,直到充滿卡套封住漏點。實際操作是復(fù)雜的,卡套是否貼合,膠會不會被泄漏的高壓介質(zhì)擠出,高溫也許讓膠提前凝固在卡套內(nèi)不能擠到泄漏點,等等。更嚴(yán)峻的是搶修的環(huán)境,有危害的氣體或液體。記得有一次在氣化工段二樓堵漏,大約每平方厘米80千克壓力的高溫氣體從卡套與法蘭之間往外滋,王師傅蹲在地上壓油泵注膠,突然就倒下了。我轉(zhuǎn)身想叫旁邊的張技術(shù)員一起施救,張技術(shù)員卻扶著柱子軟軟地正往下溜。我一陣猛喊,周圍操作工和其他工友一起趕來幫忙送醫(yī),好在一氧化碳中毒較輕,終未造成傷害。
每次看到王進(jìn)喜在井噴搶險中渾身被黑油澆透而映射著亮光的照片、看到克拉瑪依油井搶險中冰人的舞臺造型時,我都會想起對炭黑水法蘭堵漏的場景。冬天,管架下,高溫高壓炭黑水噴出,中心區(qū)熱氣升騰,地面黑水橫流。我們穿著石油工人的老式棉衣,渾身被炭黑水澆透,眼睛只能瞇著,喊著搶著,緊張激烈地堵漏,真像在井噴搶險中的情景。漏堵住了,回車間的路上,渾身濕透的我們成了黑冰人,沒有留下照片,但當(dāng)時的樣子永遠(yuǎn)定格在了生命里。經(jīng)過高溫高壓氧化反應(yīng)的炭黑,既細(xì)小又均勻,滲透了身體的每一個毛孔,棉衣是洗不出來了,身體用洗衣粉不知洗了多少遍才罷休。那時候除了肥皂香皂就只有洗衣粉,沒有沐浴液。肥皂香皂在身體上抹不過來,只有洗衣粉管用。
在機關(guān)工作還能立功,應(yīng)是不多見的。那天剛走到總控室外面,一聲爆響嚇我一跳。循聲看去,變換工段火光沖天。我立即跑過去,發(fā)現(xiàn)高大的加熱爐頂部和底部都在噴火,伴隨著劇烈的燃爆聲,保溫材料在空中亂飛。合成氨車間主任王永明來了、尿素車間主任李國光也來了。這是王主任的地盤,他知道處理事故的關(guān)鍵,李主任和我跟著他,快速關(guān)閉閥門。消防車呼嘯著趕來時,火滅了,更大的損失避免了。為此,廠里表彰我們,給我們記了功。現(xiàn)在想來有意思的是,王主任是77級大學(xué)畢業(yè)生,我和李主任分別是78、79級的,我們一起做了“新三屆”大學(xué)生的“逆行者”。
2001年9月的一天傍晚,已擔(dān)任化肥廠廠長的我正在參加大檢修會議,傳呼機傳來消息,二尿素液氨閥事故,裝置開工退回。烏石化于1997年建成第二套以天然氣作原料的大化肥裝置,技術(shù)更先進(jìn),安全更有保障。但外包單位的儀表工帶壓拆卸調(diào)節(jié)閥支架,致已經(jīng)斷裂的閥桿直接沖了出來。于是中壓液氨猛烈噴出,幾位儀表工迅速跑到隔板墻外面的二樓平臺后逃生,而我們的一位儀表工卻跑錯方向一直沒有出來。我站在二樓平臺上,周圍彌漫著水汽氨氣,右邊是消防員在向二樓框架內(nèi)噴水,左邊是安全科楊科長,倉促之下我們都沒有戴防護(hù)面具。楊科長捂住嘴匯報儀表車間張磊主任不聽勸阻,穿上防護(hù)服沖進(jìn)去了。正說著,隔板墻的門前出現(xiàn)了人影,有人喊張磊出來了。模糊中看到,有人穿了臃腫的防護(hù)服背著一個人艱難地往前挪,我們幾個人在消防水掩護(hù)下,趕快迎了上去。張主任也在參加大檢修會議,得到出事的通知后,他拼命趕往尿素車間,第一個沖進(jìn)現(xiàn)場,頂著彌漫的氨氣和面罩內(nèi)的哈氣,摸索著找到了倒在距離泄漏點十幾米遠(yuǎn)的閆姓儀表工。多年后,雖然已調(diào)離烏石化與同事們聯(lián)系很少了,但當(dāng)?shù)弥獜堉魅胃伟┩砥跁r,我非常難受,立即到醫(yī)院看望他,表示慰問和良好祝愿,更表達(dá)我對“逆行者”的崇高敬意 。
社會在進(jìn)步,對安全生產(chǎn)的要求越來越嚴(yán)格,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在生產(chǎn)和生活中都有很好的落實。但幾十年來,一個一個“逆行者”的身影時時在我腦海中浮現(xiàn),激勵我面對困難,戰(zhàn)勝困難,不斷取得進(jìn)步。“逆行者”,他們表現(xiàn)了一種本質(zhì),代表了一種精神,不能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