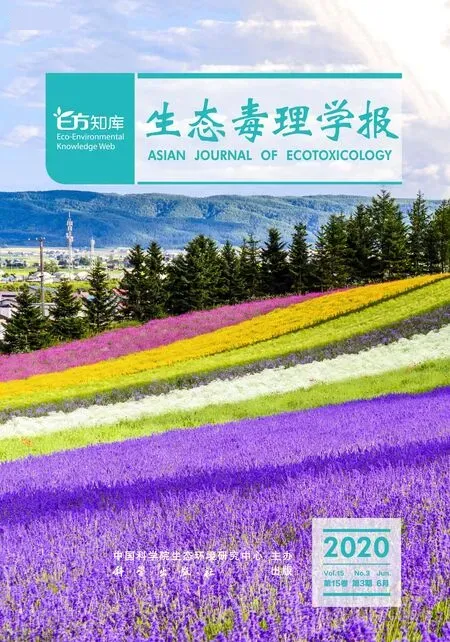中國藥物和個人護理用品污染現(xiàn)狀及管控對策建議
趙靜,蔣京呈,胡俊杰,王燕飛,菅小東,葛海虹
生態(tài)環(huán)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北京 100029
1 藥物和個人護理用品簡介(Introduction of 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藥物和個人護理用品(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最早由Daughton和Ternes[1]在1999年提出,隨后因其對人類健康和環(huán)境的潛在影響而受到關注,PPCPs作為藥品和個人護理品的專有名詞被廣泛接受。
PPCPs包括多種化學物質,涵蓋了所有人用和獸用的醫(yī)藥品(包括處方類和非處方類藥物及生物制劑),如抗生素、激素、消炎藥、抗癲癇藥、血脂調節(jié)劑、β受體阻滯劑、造影劑和細胞抑制藥物等,以及個人護理品,包括抗菌劑、合成麝香、驅蟲劑、防腐劑和遮光劑等,具體分類如表1所示[2]。
PPCPs主要是通過污水處理廠(STPs)進入環(huán)境[1],STPs中PPCPs濃度大多為ng·L-1至μg·L-1,常規(guī)廢水處理工藝,例如絮凝、沉降和活性污泥處理等工藝對PPCPs的去除效率有限[2]。污水處理廠排放污水中的PPCPs會對水體造成后續(xù)污染。PPCPs主要存在于水環(huán)境中,進入大氣的部分很有限。PPCPs也可能吸附到污水處理廠的活性污泥上,然后通過污泥再利用進入環(huán)境[1]。大部分PPCPs具有生物活性、高極性和光學活性,進入環(huán)境后可能會影響水生生物等的正常生命活動,最終通過食物鏈影響人類健康[3]。

表1 藥物和個人護理用品(PPCPs)分類及主要代表物[2]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main representative substances of 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2]
2 主要國家和組織對PPCPs的研究及管控(Research and control on PPCP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PPCPs及其代謝產物持續(xù)進入自然環(huán)境[4-6]。雖然,已報道的檢出濃度普遍較低,但在地表水、地下水、飲用水、土壤和污泥中檢出多種PPCPs,有些可以在環(huán)境中持續(xù)存留數(shù)月甚至數(shù)年[7],給人類和環(huán)境健康造成了潛在的隱患。在過去的十幾年內,國際社會針對PPCPs來源、環(huán)境歸趨、對人類健康的風險等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2.1 美國
根據(jù)美國國家環(huán)境政策法案(NEPA)規(guī)定,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從1969年開始針對藥品開展環(huán)境風險評估[8]。1998年,F(xiàn)DA的藥物評價和研究中心(CDER)發(fā)布了藥品的分級風險評估導則[9]。同年,美國環(huán)境保護局(US EPA)修訂并發(fā)布了制藥行業(yè)排放標準,控制制藥行業(yè)點源的污水排放[10]。20世紀90年代后期,US EPA和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開始對PPCPs的出現(xiàn)、來源、歸趨和對人類健康的潛在風險進行研究[11]。1999年Daughton和Ternes發(fā)表了第一篇關于PPCPs的文獻綜述[1],隨后2000年在北美召開了第一次相關會議,并出版了會議論文集[12]。2007年,US EPA發(fā)布了《環(huán)境監(jiān)測方法1694:使用HPLC/MS/MS檢測水、土壤、沉積物和生物體中的藥物和個人護理品》(Method 1694: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in water, soil, sediment, and biosolids by HPLC/MS/MS),該方法列出了70余種PPCPs目標分析物[13]。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PPCPs存在于地表水和底泥中,但是該類物質在魚類組織的蓄積數(shù)據(jù)很少。由于PPCPs在環(huán)境中的濃度很低,因此,產生的影響可能是微妙的。目前,關注的PPCPs污染問題主要是抗生素耐藥性的增加和內分泌系統(tǒng)紊亂。2006年,US EPA啟動一項關于魚類組織中PPCPs的試點研究,這是美國全國范圍內針對魚體內PPCPs的首次篩選研究。結果表明,在魚組織樣本中檢測到了7種藥物和2種個人護理品相關的化學物質,其中,抗組胺藥、抗抑郁藥和麝香最為普遍,大多數(shù)藥物的濃度為μg·kg-1級,麝香濃度為mg·kg-1級。基于試點研究的結果,US EPA在“國家河流和溪流評估(NRSA)”的框架下,通過開展全國范圍內河流中的魚類組織中PPCPs的研究,進一步分析了美國PPCPs污染的特征[14]。
2.2 歐盟
歐洲藥品管理局及人用藥品委員會(CHMP)和獸用藥品委員會(CVMP)于2004年發(fā)布了《獸醫(yī)用藥環(huán)境影響評估第二階段指南》[15],針對第一階段識別出的獸醫(yī)用藥(VMPs),為申請人在所有加入國際獸藥注冊協(xié)調會(VICH)的地區(qū)使用環(huán)境歸趨和毒性數(shù)據(jù)申請市場許可提供指導。指南使用分步驟的方法進行環(huán)境風險評估:第一層級(方法A),根據(jù)所關注環(huán)境區(qū)域中的暴露和影響,利用更簡單、更經(jīng)濟的方法進行保守的風險評估。如果預測出現(xiàn)不可接受風險,或因數(shù)據(jù)缺乏導致評估無法完成,則進入第二層級(方法B)以完善環(huán)境影響評估。
《人類用藥環(huán)境風險評估指南》于2006年正式發(fā)布,該指南是第一份關于人類用藥的環(huán)境風險評估文件,指導注冊申請人和銷售許可證持有者如何提供藥物警戒和風險管理數(shù)據(jù),從而滿足對新藥的風險管理要求。指南規(guī)定了評估的范圍和法律依據(jù),概述了一般注意事項和建議的分階段評估程序,提供了環(huán)境風險評估報告的總體框架,以及當風險無法排除時,需要考慮的預防和安全措施。評估共分為2個階段:第一階段評估是針對原料藥的環(huán)境暴露,基于行動限(action limit)可以終止評估;第二階段獲取對環(huán)境歸趨和影響的有關信息進行評估,該階段分為2個層級,A層級為篩選評估,基于水生毒性和歸趨數(shù)據(jù)進行初步的風險預測,B層級是基于排放量、歸趨和進一步的影響數(shù)據(jù)進行擴展性評估。對于多肽類或蛋白質類內分泌干擾物(SEDCs),因其對環(huán)境造成重大風險的可能性較小,暫不進行環(huán)境風險評估;對于其他潛在SEDCs,當其作用機制可能對生殖產生影響時,需開展第二階段評估[16]。
2.3 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
藥物管理局(TGA)是澳大利亞衛(wèi)生部所屬的藥物主管機構,主要負責評估新藥、對藥品制造進行許可、監(jiān)督藥品生產過程和抽檢藥品等,所有藥品在澳大利亞上市前,都需要在TGA登記注冊,并要求新藥注冊時需要評估藥品的環(huán)境風險[17]。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2011年發(fā)布《飲用水中的藥品》,介紹了飲用水中藥物的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及去除技術,對飲用水安全管理提出了建議[18]。
此外,2015年召開的國際化學品管理大會第四屆會議(ICCM4)通過了將環(huán)境持久性藥品污染(EPPPS)作為新興政策議題納入國際化學品管理戰(zhàn)略(SAICM)框架的提案,提出加強對EPPPS進行信息宣傳及意識提高至關重要。提案支撐文件指出,在全球環(huán)境中已檢測到631種不同藥物類化學品或其轉化物,包括抗生素、鎮(zhèn)痛藥和降脂藥等,大多數(shù)來自于排污廢水。EPPPS會對環(huán)境和生物多樣性產生不良影響,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尚無充足證據(jù)。目前,SAICM利益相關方正在制定關于環(huán)境持久性藥物的工作計劃[19]。
3 我國PPCPs應用與污染現(xiàn)狀(Application and pollution status of PPCPs in China)
3.1 PPCPs應用情況
PPCPs種類繁多,產生的污染物成分復雜,環(huán)境和健康危害較大。2019年,《關于印發(fā)<國家基本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的通知》正式發(fā)布,公布了國家基本醫(y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常規(guī)準入部分的藥品名單,其中常規(guī)準入部分共2 643個藥品[20]。2015年,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發(fā)布了2015版《已使用化妝品原料名稱目錄》,生產、銷售的化妝品所使用原料包含8 000多種化學品。
目前,比較典型的PPCPs主要包括抗生素類、激素類、消炎鎮(zhèn)痛藥等藥物以及人工合成麝香、殺菌清潔劑及消毒劑等個人護理用品。抗生素一般具有高生物活性,雖然其在水中半衰期較短,但大量、頻繁地使用使其呈現(xiàn)“假持久性”[21-22],人工合成雌激素多難以生物降解且具有內分泌干擾效應,消炎鎮(zhèn)痛藥應用廣泛且環(huán)境殘留情況突出[23]。人工合成麝香廣泛應用于化妝品、洗滌用品、香水和護膚品等產品,部分難生物降解,易生物富集[24]。相關研究表明,加樂麝香和吐納麝香的生物降解系數(shù)分別是0.071和0.023[25],二甲苯麝香、酮麝香和加樂麝香的生物富集系數(shù)(BCF)分別為3 800、760和1 584[26]。殺菌劑和消毒劑被廣泛添加于各類生活清潔用品中,可由環(huán)境進入食物鏈,蓄積在植物、動物和人體中[27]。
我國人口眾多,且畜牧及水產養(yǎng)殖業(yè)發(fā)達,PPCPs的生產和消費量居世界前列。據(jù)統(tǒng)計,全世界75%以上的青霉素工業(yè)鹽、80%以上的頭孢菌素類抗生素和90%以上的鏈霉素類抗生素產于我國[28]。2013年,我國使用16.2萬t抗生素,其中,獸用約占52%,人用約占48%[29];最常檢出的36種抗生素使用量超過9萬t,大部分通過人畜排泄至體外,一年有5萬t以上的抗生素排放至水土環(huán)境[30]。人工合成麝香根據(jù)其化學結構可分為硝基麝香、多環(huán)麝香和大環(huán)麝香等,其中,硝基麝香使用最為普遍。硝基麝香中用量最大的為酮麝香和二甲苯麝香,前者被廣泛應用于化妝品中[31]。我國是化妝品消費大國,據(jù)統(tǒng)計,我國化妝品市場銷售規(guī)模從2010年的2 045億元增長到2017年的3 361億元,復合增長率為9.05%[32]。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社會老齡化程度加深,藥品、保健品和個人護理品等被大量生產和使用,環(huán)境污染潛在風險會越來越大。
3.2 PPCPs環(huán)境污染情況
PPCPs含有的多種化學物質體現(xiàn)出不同的生物毒性,對環(huán)境生物包括人類產生氧化活性損傷、內分泌干擾性、抗藥性及生殖毒性等潛在危害。盡管環(huán)境中的PPCPs濃度很低,通常不易引起急性毒性,但會導致潛在的慢性毒性,毒性效應的不斷累積會使生物機體產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PPCPs的大量使用最終通過藥物直接和間接排放、污水處理廠二次排放、污泥回用及垃圾填埋、畜禽和水產養(yǎng)殖等途徑進入環(huán)境,排放源分散且難控制。藥物被人體或動物攝入體內后并不能完全被吸收和利用,大部分以原形或者代謝物的形式隨糞便和尿液排入污水系統(tǒng)或環(huán)境,而化妝品、洗滌劑、殺菌劑和消毒劑直接進入環(huán)境的量會更大。除直接排放外,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是PPCPs排放的重要源頭。我國城鎮(zhèn)污水處理中對PPCPs的去除率很低,因污水中藥物的殘留濃度較低,而且藥物種類更新較快,微生物難以適應,導致多數(shù)藥物在污水處理中很難生物降解,大部分吸附在污泥中[33]。人口密集的城鎮(zhèn)是PPCPs消費和排放的重點區(qū)域。據(jù)統(tǒng)計,我國2015年城鎮(zhèn)生活污水排放532.2億t,污泥產生和處置量約3 015.8萬t[34],污泥處置方式以填埋和土地利用為主。雖然城鎮(zhèn)污水中PPCPs含量不高,但污水和污泥產生量大,我國每年仍有大量PPCPs經(jīng)污水灌溉和污泥填埋、農用等途徑進入環(huán)境[35-36]。
PPCPs累積排放導致污染風險遞增,環(huán)境殘留問題日漸突出。PPCPs在沉積物及土壤中的分解速率較低,殘留時間長且穩(wěn)定,殘留濃度較高的PPCPs主要有抗生素和人工合成麝香。有研究表明,2009年廣州、深圳菜地土壤中均檢出了四環(huán)素類和磺胺類抗生素[37];2011年北京某污水處理廠脫水污泥中檢出佳樂麝香和吐納麝香[38]。除抗生素和類固醇外,已證實還有幾十種PPCPs在各種環(huán)境樣品和動物組織、人的血液中被檢出。我國廣州、珠江三角洲地帶河水中也普遍檢出了用作防腐劑的苯甲酸甲酯和對羥基苯甲酸丙酯、用作消毒劑的三氯生和鄰苯基苯酚以及洗滌劑代謝物壬基酚等PPCPs類物質,且濃度非常高,同時還檢出了非固醇類消炎藥布洛芬和水楊酸以及降脂藥物對氯苯氧異丁酸[39]。
4 我國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建議(Major problems in China and countermeasures)
美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PPCPs在環(huán)境中的遷移、轉歸以及由此產生的環(huán)境和健康風險,US EPA于2003年起開展了一系列PPCPs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研究工作,目前研究的重點是性激素對內分泌系統(tǒng)的干擾性。歐洲藥品局在人類服用藥物風險評估中也已引入了藥品的環(huán)境風險評估。我國在PPCPs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風險評估等領域基礎非常薄弱,污染防治形勢嚴峻。
4.1 存在的主要問題
(1)PPCPs污染底數(shù)不清。我國對PPCPs污染問題關注度不高,目前僅科研機構開展了有限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和研究,關于PPCPs排放、環(huán)境中的遷移轉化和環(huán)境與健康風險等數(shù)據(jù)信息嚴重缺乏,尤其是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檢測數(shù)據(jù)更少。隨著PPCPs在環(huán)境介質中的不斷累積,一旦污染問題集中爆發(fā),因其污染底數(shù)不清、風險情況不明,會增加治理難度和危害性。
(2)缺乏PPCPs相關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技術規(guī)范。美國基于清潔水法于2007年發(fā)布了PPCPs以及類固醇和激素在水、土壤、底泥和污泥中的檢測方法,并陸續(xù)開展相關監(jiān)測工作。我國PPCPs在環(huán)境中的殘留濃度較低,檢測難度較大,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檢測方法支持,很難系統(tǒng)開展監(jiān)測工作,環(huán)境監(jiān)測能力和監(jiān)管水平普遍較低,對PPCPs污染物的環(huán)境管理基本處于空白。
(3)對PPCPs的潛在環(huán)境風險缺乏認知,污染防控技術和政策研究明顯滯后。目前,我國對PPCPs的環(huán)境和健康風險缺乏評估和認知,已發(fā)布的80多項污染物排放標準中尚無針對PPCPs類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污水灌溉標準也未限制PPCPs的濃度或含量。由于對PPCPs污染問題整體缺乏防范意識,我國在PPCPs的遷移轉化研究、污染控制技術和管理政策研究等領域進展緩慢。
4.2 對策與建議
(1)啟動典型區(qū)域和流域的試點監(jiān)測。為盡快摸清我國典型區(qū)域和流域的主要PPCPs類物質賦存狀況,研究建立相關監(jiān)測技術規(guī)范,選擇長江下游流域、京津冀區(qū)域等經(jīng)濟發(fā)達、人口密集的地表水和飲用水源地,開展地表水和底泥、土壤和地下水中PPCPs的污染監(jiān)測。
(2)加強PPCPs有毒有害物質的篩選和風險評估。對我國生產、使用的PPCPs開展有毒有害物質的篩選研究,系統(tǒng)研究PPCPs的毒理學效應,包括對胎兒、嬰幼兒和非人類有機體(尤其是水生生物)產生的急、慢性毒性等,針對潛在危害較大的物質優(yōu)先開展暴露調查和風險評估,研究制定必要的風險防控措施。建立PPCPs上市前的環(huán)境風險評估制度,嚴格控制具有持久性、生物蓄積性和毒性的化學物質(PBT類物質)以及致癌、致突變和有生殖毒性的化學物質(CMR類物質)的添加和使用,從源頭防止其進入環(huán)境。
(3)加強PPCPs遷移、轉化及污染控制研究。開展PPCPs在水體、土壤和生物體之間的遷移、轉化等基礎研究,開展PPCPs及其代謝產物的環(huán)境效應研究。以城鎮(zhèn)污水處理廠和畜禽養(yǎng)殖場為重點,研究完善PPCPs污水排放、灌溉和污泥農用限值標準,加快推動城鎮(zhèn)污水處理和畜禽養(yǎng)殖場廢水處理中PPCPs去除技術的研發(fā)和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