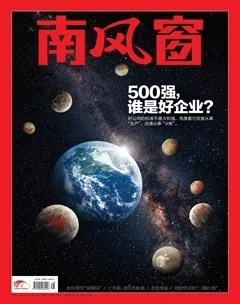國際營商環境的“歷史終結”
雷墨

2019年沃爾瑪營收5240億美元,超過世界排名13位的西班牙的財政收入
隨著美國大選的臨近,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海外企業的打壓逐步升級。美國大選期間打中國牌并不罕見,但這次不同以往。外界很容易看出特朗普政府在打壓手段上“不講底線”,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整個國際營商環境正在進入劇變時代。換句話說,隨著經濟全球化動能的減弱,國際營商環境的黃金時代也在走向終結。這個大背景,與特朗普的“不講底線”是有關聯的。
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前,國際營商環境就開始發生變化。如果把這種變化比作土壤,那么特朗普的“不講底線”,可以說是土壤里長出的“惡之花”。如果考慮目前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那么國際營商環境變化的趨勢,很難不令人擔心。對于跨國企業來說,未來國際營商環境的評估中,地緣政治因素的分量會越來越重。
“歷史終結”
提到“歷史終結”,很容易讓人想起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他的“終結論”談的是政治問題,即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將成為人類政治演化的終極形態。雖然后來關于“歷史終結”的討論變成了“歷史終結的終結”的結論,但福山提出這一理論的1990年代初,的確是經濟全球化高歌猛進的起步。國際營商環境的黃金時代,正是從那時起開始醞釀。
在說“終結”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黃金時代”是如何開始的。就經濟意義而言,冷戰的結束給跨國企業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使那些擁有雄厚資本、掌握先進科技和管理經驗的大型企業,能在全球范圍內布局公司業務、尋找獲利機遇。通過轉移生產、構建復雜的全球價值鏈,跨國企業升級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公司。某種程度上說,如今的世界經濟版圖,背后都閃現著那些全球公司的身影。所以,跨國企業的經營狀況,是感知國際營商環境的重要風向標。
在2017年前的5年時間里,發達國家排名前700位的跨國公司利潤下降了25%。這些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從歷史高峰時期的18%下降到2017年的11%。
今年8月下旬,蘋果公司市值超過2萬億美元的新聞登上國際媒體頭條。這意味著蘋果公司的市值,相當于2019年全球GDP排名世界第8的意大利。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公司的營收超過30萬億美元,接近世界排名前兩位的美國與中國的GDP總和。2019年沃爾瑪營收5240億美元,超過世界排名13位的西班牙的財政收入。有學者做過統計,營收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實體”中,公司企業占71個。
但是,這樣的事實掩蓋了潛于水下的趨勢。雖然目前依然有像蘋果公司這樣的超級賺錢機器,但跨國公司整體上的發展態勢,早已步入下滑的通道。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2017年1月做了一期封面報道,通過考察跨國公司的經營狀況與業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全球公司退潮”“跨國公司陷入麻煩”。這些變化早在特朗普入主白宮前就已經發生,但特朗普的特立獨行,加速了黃金時代國際營商環境的解體。
這些報道里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比如,在2017年前的5年時間里,發達國家排名前700位的跨國公司利潤下降了25%。這些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從歷史高峰時期的18%下降到2017年的11%。其中,40%的跨國公司凈資產收益率沒有超過10%,而這個比例是衡量一家企業是否創造價值、值得投資的基準。雖然大多數跨國企業都屬于西方國家,但位于新興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凈資產收益率同期也僅為8%。
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16年全球跨國投資下降了13%。資本的本性是逐利,投資下降的另一面是逐利空間的縮小。跨國公司在投資上的收縮,本身就反映了國際商業環境的變化。《經濟學人》的數據顯示,世界排名前500位的跨國公司中,80%的公司銷售業務擴張速度不及國內同行,60%的公司凈資產收益率比國內同行更低。該報道認為,對于很多跨國公司來說,布局海外已經變成了一個負擔,而不是優勢。
“長達30年的套利窗口正在關閉”,《經濟學人》的結論比較悲觀,甚至認為“跨國公司很可能成為商業歷史上的一段插曲”。在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者大衛·蒂斯看來,這樣的判斷或許過于夸張,但的確具有極強的警示意義,“隨著經濟全球化日益顯現的不確定性,跨國企業面臨越來越大壓力,需要重新審視全球價值鏈、重新評估跨境投資戰略、重新考慮創新與科技的流動,以及以新的視角來重新思考戰略伙伴。對于跨國企業來說,田園牧歌的時代已經遠去。
國家之手
“‘全球整合型企業將像一個單一實體而非松散聯邦那樣運作,當其在世界范圍內融合生產與價值時,將超越所有國家邊界。”這是美國IBM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帕米薩諾在2006年說的一句話。對于像IBM那樣大型的跨國企業來說,當時的世界還是平的。這些企業強大的影響力,甚至讓某些國際政治學者們認為,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時代已經終結,跨國企業的權力已超越了民族國家。這也是國際政治學里新自由主義的重要元素。
但世界并不是平的,歷史維度越長,越能看出崎嶇不平。跨國公司的權力超越民族國家,要么是一種幻象,要么是特定歷史中短暫的一瞬。在南風窗最新出版的《重新認識美國》一書中,對世界經濟有這樣的一個結論:從國際貿易的歷史來看,主導國家在塑造世界經貿秩序上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在經貿規則上,權力之手與市場之手誰更有力,歷史并沒有完全站在市場一邊,更多的是遵循權力政治的邏輯。換句話說,國際營商環境的演變,國家之手從來沒有缺位。
對于跨國企業來說,曾經的黃金時代發端于1980年代美國和英國在經濟政策上的新自由主義。冷戰的結束拆除了意識形態的藩籬,讓這種“自由”得以覆蓋全球。不難看出,正是因為有西方的國家之手,西方的跨國企業在布局海外上才那么得心應手。如果把歷史再往前推,1944年西方國家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在匯率、資本流動、貿易等領域制定規則,為西方跨國企業的經營立了規矩。毫無疑問,這也是國家之手。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但隨后美國事實上成功地將其轉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框架。此后,就有了跨國企業田園牧歌的時代。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那是個西方企業講述世界主要經濟故事的時代。美國著名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有個觀點,即跨國企業能作為跨國行為體而存在,是因為它們反映了世界經濟主導國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就是說,跨國企業推動了美國經濟權力的全球化,而不是在侵蝕美國的權力。
“長達30年的套利窗口正在關閉”,《經濟學人》的結論比較悲觀,甚至認為“跨國公司很可能成為商業歷史上的一段插曲”。
跨國企業盈利能力的下降,意味著它們更難為國家權力提供增量。當國內經濟、社會問題凸顯時,那么把工作崗位帶到其他國家的跨國企業,就會背上原罪,甚至成為眾矢之的。特朗普就是這么干的。在他的“討厭清單”中,帕米薩諾口中的“全球整合型企業”絕對排位靠前。特朗普政府降低公司稅,意在逼迫跨國資本回流;攪亂全球產業鏈、重談貿易協定,意在通過“制造”邊界,改變此前有利于跨國公司布局全球的規則。世界再次變得崎嶇不平,還是因為國家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從享受過經濟全球化紅利的西方國家角度來看,如今國際營商環境變得不那么有利,也是因為國家之手。近年來,西方學界關于“國家資本主義”“政治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等話題的討論越來越多。這些討論幾乎都是基于這樣的假定,即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經濟體,通過強化國家角色的發展模式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這種模式與西方經典的自由主義不同,并且造成了不公平競爭。
這樣的邏輯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但目前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中,國家的角色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這既不是新興經濟體獨有的現象,也不是中國的特色。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米蘭·阿比奇,在2017年的一篇學術文章中,對國有跨國企業情況做過一個梳理。他發現,全球范圍內的國有跨國企業總共有5994家,排名前四位的分別是中國(19.5%)、法國(14.5%)、俄羅斯(9.5%)和德國(7.7%)。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中,有七個是歐洲國家。
在阿比奇看來,這樣的現狀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歸”或者“自由市場的終結”,因為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以及這些國有跨國企業對全球政治經濟的影響,都還是有待研究的問題。這一方面意味著國際經濟態勢的演變進入了未知水域,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家間圍繞經濟話題的分歧和矛盾,不能簡單地定性為發展模式之爭。
政治風險
對于跨國公司來說,國際營商環境變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將是地緣政治風險的增加。全球咨詢公司韋萊韜悅與牛津分析公司,在2019年年底發布了一份針對福布斯全球500強企業的調查報告。根據這項調查,89%的受訪者認為,過去5年里地緣政治風險在增加,其中有46%的受訪者把美國視為地緣政治風險增加的區域,主要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經貿政策的不確定性。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弗里蒙特,特斯拉裝配廠
總部位于瑞士的保險公司“蘇黎世北美”,2019年發布了一份關于美國商業環境不確定性的報告。這份報告通過對30個國家的497位公司首席財務官的調查發現,68%的受訪者預計未來1~3年美國的保護主義會增加,6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將加大跨境并購、收購的審查。調查還發現,越是大型的跨國企業,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擔憂越比例越高。
保護是因為競爭優勢遭遇挑戰。上述《經濟學人》的報道提到了這樣一個現象,即西方的跨國企業,從曾經的世界經濟領域的“獵食者”,開始變成“獵物”(被東道國競爭對手收購)。主要的原因是競爭不過新興經濟體的本土企業。大衛·蒂斯認為,大多數跨國企業都很難在海外復制在母國的成功,因為在全球化背景下,“距離”依然重要。他所說的距離,主要是指國家文化、身份認同的差異。這些差異,在民粹主義時代,很容易轉化為地緣政治風險。
目前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中,國家的角色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這既不是新興經濟體獨有的現象,也不是中國的特色。
特朗普政府在知識產權問題上施壓,頻頻打壓中國的科技企業,關鍵的原因在于,這是目前美國跨國企業為數不多的優勢領域。根據相關數據,位于經合組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2017年之前的5年里,海外利潤下降了17%,而美國得益于快速發展的科技企業,其跨國公司利潤只下降了12%。美國跨國公司排名前50位的企業中,海外利潤中65%依賴于知識產權,而十年前這個比例僅為35%。
當然,現階段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不僅已經與知識產權保護無關,而且是在背道而馳。這就涉及地緣政治風險的核心問題—戰略競爭。不難想象,在未來的國際營商環境中,非戰略性行業領域的跨國企業,還有可能繼續捕捉全球化的機遇。但與高科技相關的戰略性行業,跨國企業的運作很可能與國家戰略要求相配合。
責任編輯譚保羅 tdb@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