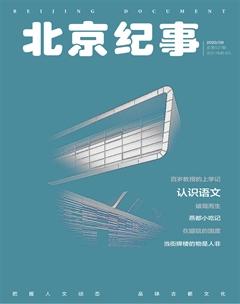認識語文: 語文課堂,和人文是啥關系?
曹文軒
我參與中小學語文教材編寫的過程中,提出來一個意見:我們現在編寫的是語文教材,不是人文讀本,“語文”二字不可有片刻忘卻。
以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一文為例,這篇曾經影響了美國歷史走向乃至影響人類歷史走向的政治演說詞是不是具有足夠的人文性?毫無疑問,但它同時還是一篇絕佳的好文章。從“語文”的立場來分析解讀這篇演說詞,修辭上它大量使用了排比句,而排比恰是演說詞特有的、最重要的修辭方式。演說詞的目的就是鼓動你,排比句可以形成一種強大的語流,使聽眾處在激情狀態。因此,《我有一個夢想》這篇演說詞從語文的角度可以有很多說道之處,而它的深刻性同時也是毋庸置疑的。
我曾經編過一套《民間語文讀本》,編選的要求就是:選取的文本必須在寫作上有可說道之處,能夠從寫作的角度去講它的妙處。比如我選了一篇悼詞,悼詞文體的寫作格式可能立刻會浮現:某某某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活著的時候做了多少好事,現在離開我們,讓我們化悲痛為力量,最后加上一句勸親人們節哀順便。而我選擇的悼詞是一個日本作家寫的,被哀悼的是位日本評論家,他一上來就罵死去的人:“你這個家伙太自私了,這塊墓地是風水寶地,老子先看上了,你怎么可以搶先我一步把它占上了?多少年以后,我沒辦法,我也是要來和你做鄰居的,但是我現在告訴你,我根本不想和你做鄰居,跟你這樣的人做鄰居太無趣了。我們有什么好說的?我們根本沒什么好說的!”一通下來就是罵,我當時一邊看一邊笑,一邊笑一邊眼睛發酸,可以想到那個逝者和正在做悼詞的人原來關系有多好,一個朋友不好到那個份兒上怎么可能做這樣的悼詞呢?閱讀這個悼詞,文章之道、文章之法便高下立判。
文學作品的藝術解讀,尚存巨大空間
有一篇是賈平凹的散文,寫刮風的。可是風這個字從頭到尾在他的文章里面都沒出現,他就寫刮風時的樣子以及風刮出去之后在大地上留下來的各種各樣的形狀,可是風這個字始終沒出現。學生閱讀之時,就應該思考這樣的文學處理有何可取之處,體會文學與現實之間有何關系。
因此講文學課、聽文學課,都不能只停留在對作品的人文性解讀上,還要回到藝術層面對作品進行解讀。
經典作品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學性和藝術性。
所謂的藝術性包括人物刻畫、情節安排、細節描寫、風景描寫、意境、意象、起承轉合、開頭和結尾各種敘事手段、氛圍營造、畫面感,以及各種修辭方式等,話題之多無法說盡,正是無法說盡,恰恰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解讀文學作品巨大的藝術空間。
有一次,我去杭州一所學校講寫作課。講座中提到了《凡卡》,這篇文章在很多版本的語文教材中都出現過,文章是寫一個叫凡卡的小孩在皮匠店里學徒給爺爺寫的一封信,把這封信放到郵箱里面,希望爺爺能收到。但是他只寫了“鄉下爺爺 收”,所以是寄不出去收不到的一封信。
于是,我臨場提了一個問題:誰能講一講《凡卡》?
切入課文,更輕盈視角可能更有效
有一個小男孩把手舉得特別高,我說孩子站起來回答我的問題。那個小孩站起來,才學絕佳,滔滔不絕,慷慨陳詞,滿臉漲得通紅,說凡卡寫了俄羅斯底層人民的困難生活,控訴了沙皇俄國的殘酷統治。講完以后,掌聲雷動。
那么這個小孩講得對不對?對,當然沒問題。當時俄國的那批作家包括契訶夫都有強烈的批判社會現象的動機,毫無疑問,《凡卡》正如那個孩子所言具有明確的批判社會的傾向,但它畢竟是一篇小說,是文學作品,對它的解讀不能光是這些。于是我接著問他,孩子,你能不能從其他角度講一講《凡卡》?他一下子呆住了。因為他沒有其他的話題,老師告訴他就是這個意象的話題,他不可能給我講其他的。
藝術層面上,學生該如何解讀呢?如果我講《凡卡》,會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凡卡在皮匠店學徒的苦難經歷,不是由凡卡傾訴出來,而改為作家本人直接寫出來,請問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一篇叫《凡卡》的經典短篇?這個問題直接切換到了文學的“敘述”角度。
第二個問題,《凡卡》小說中并沒有提到這封信永不會到達這個細節,這樣處理好嗎?其實這個細節絕對重要。我們之所以說《凡卡》是一個藝術性很強的短篇、構思非常巧妙的短篇,就是因為這個細節。這個細節是這個短篇的魂,是這個短篇小說的眼。我們對《凡卡》一文感同身受的原因,或許恰是因為人人心中都有一封永不能到達的信。
因此我們要懂得“鑒賞”,體會美好的心情和心境。回望先人們的閱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品評一件藝術品時的優雅風采。那些出神入化的點評讓藝術品真正被“閱讀”,也正是這種“閱讀”,讓文學成為文學。
金圣嘆的評點旁邊總有一個批叫作“絕妙好詞”。如果語文老師們在上課時也發出這種感嘆,就“點石成金”為真正的語文課了。
對于文學文本的解讀是否就已經是最合理最有效的?我表示懷疑。以往的解讀在大一統的語境里面,在有限的知識下已經程式化了,我們需要反思以往的解讀方式和解讀途徑,這就需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需要親近和接納新的知識,需要尋找輕盈的更為有效的切入文本的視角。
我們試圖從另一個方式解讀《窗邊的小豆豆》,看看是否還有更好的途徑。首先我們重新思考《窗邊的小豆豆》的主人公是誰?有人覺得這不言而喻,就是書名里面的“小豆豆”唄。可是我覺得《窗邊的小豆豆》主人公不是小豆豆,也不是小林校長。那是誰?它的名字兩個字,教育。
《窗邊的小豆豆》的開頭和結尾就可以印證。
開頭是這樣的,那個叫小豆豆的女孩又被日本一所學校勸退了。她的媽媽帶著這個古怪精靈的孩子去找學校,哪個學校接受她們的女兒?小豆豆的媽媽猶如走在懸崖峭壁之上,她實在不能知道在日本這個國土上還能有哪所學校能夠接受她們家的閨女。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巴學園這個學校,接待她們的是小林校長,下面的故事是小林校長耐心地、安靜地聽小豆豆一口氣講了3個小時的話,然后對她的母親講,這個孩子我收下了,收下她的其實是現代的教育理念。
故事的結尾,巴學園被大火燒掉了,小林先生穿著一套過了時的三件套西裝,望著正在大火中熊熊燃燒的巴學園問了旁邊站著的兒子一句話,“我們還要辦一所什么樣的學校呢?”這就是《窗邊的小豆豆》的最后。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從開頭到結尾都有強烈的理念在支撐著所有文字表達,教育!我說《窗邊的小豆豆》的主人公不是小豆豆,也不是小林校長,而是講教育。
進入文學作品的角度是多種多樣的,我也并不認為剛才的解讀就是最好的,更不認為這一解讀是唯一的。我只是想訴說一個道理,我們可以選用不同的角度進入一篇文學作品,而從每一個不同角度的進入都會讓我們看到這篇作品內部的不同風景。我們之所以提倡這樣并認定可以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們擁有一個鐵定的事實,一篇優秀的文學作品是有多種解釋的可能性,是有多重解釋的可能性。
有的時候,我們評析一部作品,會用“主題鮮明”來夸它。我最初也是這樣認為,可是后來發現這可能是一種誤區。誰能告訴我《紅樓夢》的主題是什么?
曹雪芹解決了中國大量的就業問題,多少人在吃《紅樓夢》這碗飯?多少紅學家、多少學生在研究《紅樓夢》?多少人在做《紅樓夢》的碩士、博士生論文?可是誰能告訴我,《紅樓夢》的主題是什么?說了這么多年,我們也不能一定說《紅樓夢》的主題是什么,因為一篇好的文學作品就像我們面對一種存在一樣,這個存在不是唯一能說清楚的,一個存在是經得起各種解釋的。
一篇好的作品是經得起各種角度的解讀,好的文學作品一定是呈現在人類和世界存在的基本狀態,而人類和世界并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
世界已存在千年,闡釋世界之道卻越發無窮無盡。如何解讀文學課?這或許沒有準確唯一的答案,但是一種探索的姿態,會讓文學作品具有更豐富的價值,學生的認知能力和思維能力也在不斷躍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