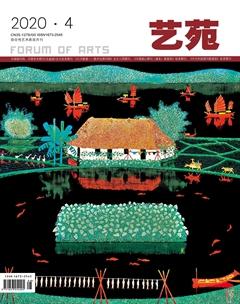論威爾遜《巴爾的摩旅館》劇中的文化象征與隱喻
【摘要】 蘭福德·威爾遜是美國當代著名戲劇家,他善用邊緣人的形象來反映受創的時代文化。他的三幕劇《巴爾的摩旅館》就以邊緣人的生活狀態來表達了當時扭曲的物質價值觀及其對未來城市發展前途的迷茫。該劇在人物塑造、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上與《櫻桃園》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表現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小人物所具有的精神特征以及作者對美國傳統歷史逝去的哀悼。
【關鍵詞】 蘭福德·威爾遜;《巴爾的摩旅館》;《櫻桃園》
[中圖分類號]J80? ? [文獻標識碼]A
蘭福德·威爾遜(Lanford Wilson,1937-2011)出生在美國中西部地區密蘇里州萊芭農,其戲劇作品共有17部,他的第一部戲劇是《集市告別》(1963),第一部多幕劇是《吉里德的香膏》(1965);中期主要作品有《檸檬色的天空》(1970)、《巴爾的摩旅館》(1973)和“塔利三部曲”(1977)(1);后期作品則主要有《燒掉這個》(1987)、《紅杉木窗簾》(1991)和《祈雨舞》(2000)等。他作品中的人物多游走于社會的灰色地帶,缺少內在主動性,人物所處的也都是經歷過創傷的時期。
威爾遜早期的作品只能在外外百老匯上演。20世紀60年代初期,威爾遜以他異于常人的敏感捕捉到人們在生活中所忽略的題材,又以極具個人特色的劇本創作扣響了現實中早已失修的警鐘。這使他的劇作不僅在外外百老匯得以生存下來,還深受大眾青睞。1973年上演的三幕劇《巴爾的摩旅館》(The Hot l Baltimore)更是讓他一躍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劇作家之一,鞏固了他的劇壇地位。同年《巴爾的摩旅館》又多次在格林威治的方形圓圈劇場(2)上演,該劇1975年還被拍成電視劇并在美國廣播公司(ABC)上演。
一、《巴爾的摩旅館》劇情介紹
《巴爾的摩旅館》原名為The Hot l Baltimore,其中的“hot l”是有意去掉e的“hotel”,根據舞臺說明e這個字母是被火燒掉了。這一細節處理體現了劇中“美國夢”從繁華走向幻滅的主題思想。劇情發生在巴爾的摩市一個靠近鐵路的破舊旅館里,旅館曾經的豪華見證過這座城市昔日的繁榮。劇中出場的人物包括旅館里的工作人員,和因為各種原因來到這間旅館的客人,共有12位。整部劇分為三幕,講述了1972年5月25日陣亡將士紀念日(美國聯邦法定節日,目的是悼念在各戰爭中陣亡的美軍官兵)當天在這個旅館里面發生的事情。地點在旅館大堂,時間為一天之內,情節圍繞旅館即將被拆除這個消息展開。
比爾是旅館的接待員,他會在早上提供叫醒服務。雖然他沒有咄咄逼人的性格,但有時也會跟房客發生爭執。旅館即將被拆除的消息是住在這里的一位妓女發現的,這位妓女在劇中沒有正式的姓名,僅被稱作“女孩”。“女孩”年輕有活力還是個鐵路迷。她熱情浪漫,對一切都充滿好奇。她樂此不疲地幫助一位名叫保羅的青年尋找關于他爺爺的線索,雖然保羅對于她、對于這座旅館來說只是一個過客。
住在旅館的其他人物還有很多,比如賓館卡茨經理一天到晚看上去都很疲倦,被各種瑣事纏身。前旅館工作人員的母親貝洛蒂太太為兒子工作的事情要找他。房客莫爾斯先生是個70歲、行動緩慢但精神矍鑠的人,但看起來只會抱怨。他的房間熱水不夠,沖著卡茨經理抱怨也不是一回兩回了。杰基、杰米姐弟倆來到酒店就聽見了莫爾斯的喋喋不休,于是杰基主動去幫助莫爾斯修理,可私底下她卻偷了莫爾斯的珠寶,事情暴露之后經理給他們姐弟倆下了逐客令。杰基的弟弟杰米是個有些智障、反應遲緩的人,易輕信別人,對姐姐的指揮言聽計從。杰基買下了一塊地想要致富,可被“女孩”告知是塊鹽堿地,毫無用處。杰基夢想破裂,加上被經理驅趕,她以去給汽車加油的理由將弟弟杰米拋棄在了這座旅館。
旅館里還有三位妓女:30多歲的愛普利和蘇西,還有一位68歲已經退休的米莉。愛普利溫柔大方,對自己和嫖客的經歷侃侃而談,同時也是個實用主義者。蘇西活潑且浪漫。第一幕結尾,在嫖客約翰走了之后,她只圍著一條毛巾就追了出來,接著就引起了大廳里騷動,惹得臺下觀眾哈哈大笑。可她有時也會堅硬得像顆釘子,對自己認定的事情會毫不猶豫地去執行。米莉姿態翩翩風度優雅,會給那個“女孩”講述自己少女時代的經歷,那是在巴吞魯日市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房子里,其中有關鬼的部分成功吸引了“女孩”。最后,為了讓杰米從被姐姐拋棄的沮喪中好起來,愛普利為他跳了一段舞,全劇結束。
該劇創作靈感來源于威爾遜1957所年看到的芝加哥。芝加哥在1871年也發生過一場大火,后經歷社會暴亂、環境污染加劇和黑幫勢力橫行,直到19世紀50年代才逐漸好轉。威爾遜選擇巴爾的摩這座城市為背景,如他所說,是因為:“對我來說,這是個城市的象征,從前生機勃勃,現在就要下地獄了。”作為美國馬里蘭州的最大城市和美國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海港城市,巴爾的摩還有著獨特的歷史底蘊。它是美國國歌的誕生地,也是美國第一條鐵路——巴爾的摩至俄亥俄鐵路的始發地,可20世紀初的一場大火(3)摧毀了這座城市,因此燒掉的字母e既提示觀眾不要忘記那場真正發生過的火災,也暗示劇中的主題思想。威爾遜說自己是一個“鐵路狂人”。19世紀的工業化浪潮中,鐵路業曾拉動美國經濟迅速發展,但是在20世紀60—70年代,隨著汽車工業和公路交通系統的發展完善,鐵路的重要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威爾遜在創作這部劇的時候說他有個實驗性的想法,打算寫一首長長的哀歌,為逐漸失去強勁競爭力的鐵路業而哀悼,所以在《巴爾的摩旅館》中,不管是那個沒有名字、對鐵路感興趣的“女孩”,還是旅館大廳墻上掛著的鐵路壁畫都顯露了威爾遜的創作初衷與動機。劇中的旅館是“邊緣人”的天堂,就像威爾遜自己所寫的那樣,建造這座旅館的初衷是讓它成為一個優雅而舒適的避風港,可一切都發展得似乎不那么順利,逐漸走向了一個相反的極端。
二、《巴爾的摩旅館》劇中的文化象征和隱喻
被火燒掉的“e”這一細節與歷史事實相對應。1904年巴爾的摩曾經歷過一場大火,起初并不嚴重,可突如其來的大風再加上木質結構的建筑,火勢便一發不可收拾。許多貧民作為圍觀者幸災樂禍。最后火勢越來越大,圍觀的群眾也成為了受害者。劇中的旅館就是巴爾的摩當時的縮影,一切都散發著頹敗的味道,亟待重建。
本劇的時間是陣亡將士紀念日當天,這個節日在美國具有重要意義。1971年尼克松總統宣布將陣亡將士紀念日列為國家節日,人們應當莊嚴肅穆非常有儀式感地度過這一天。可《巴爾的摩旅館》卻完全沒有提及關于這個紀念日的任何消息,旅館之中的人們在這樣的日子里仍然平庸無聊,為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對國家的過去和榮耀毫不在乎,威爾遜通過這種對比揭示了劇中人物對自身歷史的無知與冷漠。
70歲的莫爾斯先生是最年長的,他來自于上一個世代。他行動的緩慢暗示著經歷過戰爭身披榮耀的一代人已經老去,深感無奈,只能喋喋不休。上一代經歷過磨難阻礙、不斷開拓勇進的精神本應該是被發揚光大,可如今社會物質錢財的豐富使人們安于現狀、不思進取,甚至熱衷于投機鉆營。這一切讓莫爾斯看不順眼。
35歲的旅館經理卡茨先生疲憊不堪,周轉在旅館人事及雜事當中,他代表的是當時美國多數的中產階級。在經濟大蕭條之后,中產階級的經濟收入受到沖擊,巴爾的摩旅館建立初始的豪華和現如今的破敗正應對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艱難處境。杰基不切實際,總想一夜暴富,這與她裝卸工人的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裝卸工人原本是個腳踏實地的職業,而杰基卻異想天開,像底層的許多工人一樣以為隨便買一塊地就可以暴富,以致上當受騙。
劇中19歲的“女孩”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在本劇的一開始就通過她的話揭示了主題,她說到:“那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地方!他們為什么把一切都拆了呢?”她顯然是威爾遜的代言人,替作者表達了對當下社會現狀的憂慮。劇中她是懷念過去的象征。曾經的輝煌在現在人們的眼中變得一文不值,人們失去的也不僅僅是幾座建筑,更是以往最為寶貴的精神信仰。威爾遜在寫這部劇期間去了美國很多地方,劇中的“女孩”也是一位走遍美國各州的人物,她能夠清楚地知道每一班火車的名字、時刻表和路基。女孩體現了作者對美國過去美好歷史的眷戀和懷念。“女孩”告知杰基她買的地是鹽堿地,什么都種不出來,表面看是破壞了別人的夢想,細察辨析會發現作者通過女孩展現了美國“荒野精神”的隕落。經歷過西部大開發的美國人都把這段歷史視為一個神話、一個象征、一個與自然搏斗的歷史奇跡,而當下社會的都市發展模式已然讓人們遺忘了這種精神。劇中三次晚點的火車汽笛聲,代表著當時較為反常的生活背景與環境,它的偏離正常軌道如同旅館中的各色人物一樣。另一方面女孩還是未來的象征。在她口中不止一次地暴露美國當下社會的根本性問題:人際關系冷漠。例如,比爾在執行叫醒服務時有一位房客始終沒有接電話,女孩在看到比爾漠不關心之后說:“我真的很討厭沒有人關心任何人。”她主動幫助保羅找爺爺,知道保羅徹底放棄之后非常生氣;她還在貝洛蒂太太遭到拒絕之后說:“我只是不喜歡看到人們只需要東西。”她是劇中唯一對歷史感興趣、主動去探知,并且關注外部世界變化的人物,是這部劇中過去和未來的連接點。在女孩的映襯下,我們可以感受到旅館中的房客之間普遍缺乏關心,他們先是拒絕了人與人的基本溝通,后又割裂了歷史與當下的關系。以往在困境中誕生的集體奮斗精神是創造性的主動精神,是以人與人的團結、互助為中心的進取精神,而旅館中的房客體現出的卻是以自我個人主義為中心的“孤島”思想,他們漠視交際關系,淡薄家庭觀念,無視歷史的重要性,產生了與初始集體奮斗主義相反的精神特征。女孩的存在提醒著旅館中人,同時也想要喚醒當下的觀眾,在這個物質至上的時代中,我們更需要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和幫助。而從她游歷過美國各地卻最終留在旅館的選擇上,我們可以能看出,威爾遜對于城市未來的發展前景是迷茫的,他隱約感受到了當下時代自私、冷漠的個人主義盛行的問題。所以,女孩是他在劇中塑造的理想化角色,他希望通過女孩這個角色將過去和未來做一個聯結,凸顯出現代人在發展中所丟失的那些珍貴精神,以達到警醒的效果。《巴爾的摩旅館》是對當時人們生活狀態的真實呈現,全劇中沒有明顯的矛盾沖突,這是因為威爾遜將其隱晦地藏入了每個人物背后,用一種隱喻的方法來展現深伏的時代危機,看似是平淡的日常生活卻暴露著社會發展的嚴肅問題。
這座旅館是保護也是牢籠,它是將人們與外界隔絕的盾牌。旅館里的陳設就是人們內心的真實反饋。就像壞掉的電視機現在被用來當作桌子,旅館大門上裂了一英寸的破窗戶,幾十本書籍隨意堆放在曾經輝煌象征的壁畫面前,旅館的破敗象征著房客內在精神世界的衰頹。這里的人們包括不同的年齡段,來自不同的族群和階層,他們聚集在一起試圖通過逃避來抵抗旅館之外的世界,但相互之間又缺乏團結緊密的凝聚力如同散沙,沉溺于自我世界,危機面前冷眼旁觀,在即將到來的時代轉折面前艱難的行走,失敗是他們可以預見的結局。美國人以往勇于開拓進取的精神正在一步步消蝕,而那副掛在大廳的鐵路壁畫寄寓了作者對美國曾經擁有過的榮耀歷史和開拓進取精神的哀悼。
三、《巴爾的摩旅館》與《櫻桃園》
威爾遜曾說《巴爾的摩旅館》是受了契訶夫《櫻桃園》的影響,《櫻桃園》是契訶夫晚期創作的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話劇。契訶夫年幼時的艱苦經歷和醫生職業使得他洞察各個階層的境遇,無情地揭露沙皇統治下的不合理制度和社會丑惡現象。契訶夫戲劇形式的革新主要體現在注重日常生活細節的描述和“無中心”情節的使用上。威爾遜在《巴爾的摩旅館》中也借鑒了這種風格,即聚焦于呈現日常瑣碎生活,情節矛盾也從人與人的沖突轉變為人與時代、環境的沖突。
《巴爾的摩旅館》的劇情架構跟《櫻桃園》很相似。《櫻桃園》中女主角柳苞芙在經濟狀況不允許的條件下仍過著貴族糜爛奢華的生活,不久便負債累累,無奈之下莊園被拍賣給了出身農奴的羅巴辛。而曾經生活在這座莊園里的人們傷感地等待著新主人的到來,無力地懷念著過去。《櫻桃園》的故事背景是19世紀中葉之后的俄國,這時的歐洲大陸經歷法國大革命的洗禮,封建君主專制已被推翻,啟蒙主義廣泛傳播,但俄國還依舊保持著沙皇專制制度。《櫻桃園》表面上是在講一個櫻桃園的易主與消亡的故事,實則反映了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終究會取代地主貴族的歷史事實。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契訶夫和威爾遜都選擇了從日常生活細節入手來展現時代的發展變化。情節沖突淡化,劇中人物的設置也不再是英雄、權貴,而是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舞臺上的布景也不追求精致和炫目,而是簡約和真實。《櫻桃園》中塑造了四個仆人的形象,他們之間相互映襯,在老費爾司的“正常”狀態對比之下,葉比霍多夫的精神頹敗、董聶莎的自戀、雅沙的自以為是和自傲將底層小人物的面貌展現地淋漓盡致,從小人物的視角來預告即將到來的時代變革。威爾遜在《巴爾的摩旅館》之中則塑造了三位游離于社會之外不知何去何從的妓女形象。妓女往往是沒有尊嚴受人歧視的群體,而旅館里的她們卻對此甘之如飴。愛普利的以此為樂、蘇西的幼稚舉動、米莉一心只專注于自己的利益等,作者將這些邊緣人對于時事的冷漠悉數列舉。威爾遜通過她們在危機到來前仍舊沉溺于眼前之事來體現邊緣人的麻木無知。《櫻桃園》和《巴爾的摩旅館》的共同點是都以人物群像塑造為主,以群體人物的精神特征來表現時代的變化與發展。不同的是《櫻桃園》所書寫的時代透露著新興資產階級和新時代即將到來的嶄新氣息,而《巴爾的摩旅館》描述的卻是美國人對未來社會發展前景的迷茫和麻木。
在藝術風格上,《巴爾的摩旅館》和《櫻桃園》都使用了悲喜劇風格,以此來表達他們對逝去時代的哀悼。劇中人物的言詞荒唐和行動不協調所引發的笑聲,都是帶有嘲諷意味的冷笑,與傳統意義上的喜劇又有很大出入。二者之所以沒有被定義為悲劇,是因為劇中的人物都沒有悲劇的壯烈。悲劇人物總是在與命運或者是困境相搏斗,且終究逃不過失敗的結局。不管是櫻桃園里的貴族代表還是威爾遜筆下住在旅館的眾人,都在失去之際毫無作為。柳苞芙的哥哥加耶夫也曾為了保住櫻桃園而四處借錢,每次出門前的信誓旦旦和無一例外空手而歸的結果反而表明了他們的無力。旅館中的女孩也樂此不疲的幫助著保羅尋找爺爺,但保羅最終放棄的結局,無疑是威爾遜在控訴著當代美國人對于自身歷史的遺忘和漠不關心。劇中唯一應該讓所有人都感到焦慮的消息——旅館將被拆除卻似乎沒能引起這群人的重視。旅館拆除的消息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指向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并凸顯了以住在這里的人們為代表的落后群體在時代更迭點上對往日生活的留戀、對未來生活的彷徨和對現實的逃避,代表著麻木無知、不思進取的社會邊緣群體即將被歷史淘汰。劇中人的悲劇在一開始就是注定的,他們不是職業上的邊緣人就是精神上的邊緣人,時代浪潮更迭前卻沉溺于緬懷過去,自我的原地踏步與社會不可逆轉的進步相沖撞,表現出一種人與時代、環境之間的沖突。可這種社會的時代的悲劇又是怎么被歸為喜劇的呢?俄國在沙皇殘暴統治下隱忍的太久了,亟需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等級制度,這不僅是契訶夫的個人愿望更是俄國人民的向往。而對于威爾遜來說,1973年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大量涌現。19世紀晚期建立的巴爾的摩旅館就成了舊生活的代表,承受著要被覆蓋被更新的命運。曾經真實發生在巴爾的摩的大火燒毀了這座城市之前打下的堅實基礎,而芝加哥災后重建的失敗先例又讓威爾遜對于巴爾的摩這座城市的未來充滿質疑。人們的生活因為社會轉型、城市擴張出現許多問題,貧富差距與日俱增,衛生安全問題逐漸顯露,資源浪費與污染治理層出不窮,犯罪率上升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威脅。《巴爾的摩旅館》從近距離上看描述的是美國人對未來城市發展的迷茫和恐懼,但脫離開來將其放入歷史大背景中就會發現,時代總會繼續向前發展,一成不變的陳規舊矩被淘汰正是社會進步的典型標志。兩部戲劇都是以一種喜劇反諷的方式來表達大的時代環境變遷下普通人的局限性及無奈。
在人物對話上,威爾遜運用了多聲部的表現手法。《巴爾的摩旅館》劇情的矛盾表現手法與《櫻桃園》一樣,都是通過人物的對話閑聊來體現。契訶夫曾說:“在生活中人們并不是每時每刻都在開槍自殺、懸梁自殺……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吃吃喝喝,吊膀子,說些不三不四的蠢話,必須吧這些表現在舞臺上才對。”契訶夫的戲劇語言特色在于人物說話時的停頓,契訶夫利用停頓將本該外向爆發的情緒轉向人物內心,根據不同的環境和語境表達著全然不同的情感,時而緊張進而悲傷時而表現著內心的某種期待時而表現著即將來臨的情緒爆發。停頓是現實生活本身的節奏,越能接近生活的,便越能理解,《櫻桃園》中共有33處停頓,每一處停頓都恰到好處充分將他的戲劇生活化。威爾遜的特色則在于多聲部的對話方式,與契訶夫相反的是這種方式將人物沒有挑明的內心波動紛紛外化呈現。旅館的人們總在同一時間進行不同的對話,如果說契訶夫的停頓的關注重點在于個人,威爾遜的多聲部對話則更多的關注整體。多聲部的對話可以是兩個人也可以是多個人,雖然人們嘴上沒有說出對旅館即將拆除的慌張,但動不動就爭吵的對話方式已經暴露了他們內心的焦慮。第一幕的出場人物是最多的,所有的重要人物在第一幕全部出場完畢,所以第一幕的多聲部對話也是最密集的,一共有9處。第一幕結尾處所有在場的角色都在進行著或大或小的爭吵,對話全部被重疊在了一起,大量的對話重疊給了觀眾私人空間,每一部分的對話都不能完整的聽清楚,威爾遜用混亂的場面給觀眾反向營造出一個思考空間,把觀眾從劇情發展中拉出來架起了“第四堵墻”,認識到這里的人所構建起的整體就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處境一團糟。這兩部戲劇都是時代變遷的見證,《櫻桃園》以貴族的沒落來迎接新興階級,《巴爾的摩旅館》則是以當下城市中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墮落與挫敗來惋惜美國人民曾經擁有的堅韌和無畏勇氣。
結 語
《巴爾的摩旅館》受到《櫻桃園》的影響,在人物塑造、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上都有所借鑒,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劇中的群像塑造聚焦于時代大環境下人們普遍具有的性格特點,不管是何種職業何種階級,在這種動蕩之下都沒有歸屬可言,而威爾遜選擇以邊緣人作為敘述對象更是將人與時代的矛盾無形中擴大,即使是在“無中心”情節的敘述手法下,主要矛盾依然能夠清晰可見。《巴爾的摩旅館》是威爾遜創作生涯中一部具有轉折性的作品,它在延續前期作品懷念主題的同時,又呈現出后期劇作針砭時弊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更加側重于展現受創的傳統文化并揭露現代人扭曲的物質觀,最終向我們展示了一群小人物在時代的新舊更替中麻木無奈的畫卷。
注釋:
(1)塔利三部曲包括《七月五日》《塔利家的蠢事》《塔利父子》。
(2)CIRCLE IN THE SQUARE:是后來百老匯圓圈劇場的前身,1951年建于紐約州邊境附近的格林尼治。方形圓圈劇場的特色在于其延伸出來的舞臺,會讓觀眾深陷劇情當中。
(3)1904年2月7日上午11時,因為美國巴的摩市的約翰·赫斯特公司一家占地面積很大的綢緞呢批發倉庫起火,最終蔓延整個城市。
參考文獻:
[1]Gene A.Barnett.Lanford Wilson[M].Boston,1987.
[2]Lanford Wilson.The Hot l Baltimore playwrights[M].New York,1973。
[3]無名山.世紀大火難三——美國巴爾的摩大火[J].消防月刊,2002(12).
[4]劉珍.解讀《荒野獵人》折射出的“美國精神”[J].戲劇之家,2017(9).
[5]陳文鐵,郝利群.美國當代戲劇家蘭福德·威爾遜評析[J].上海戲劇,2007(3).
[6]雪菲.淺析契訶夫靜態戲劇《櫻桃園》中的悲劇性[J].漢字文化,2017(6).
[7]周千愉.契訶夫殘酷精神下的獨創性喜劇模式——以《海鷗》和《櫻桃園》為例[J].人文天下,2018年(8).
[8]張京.試談戲劇中的停頓——以契訶夫的《櫻桃園》為例[J].現代交際,2010(9).
作者簡介:孔澤陽,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國現當代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