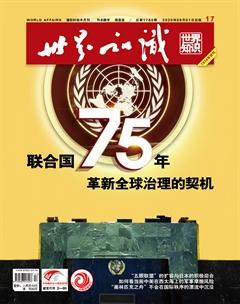如何看當前中美在西太海上的軍事摩擦風險
胡波

位于中國西沙群島西南端的中建島。
最近一段時間,隨著中美關系持續下行,加之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國內外不斷傳出類似“美國要轟炸甚至占領中國南海島礁”的所謂內部消息,中美雙方的前沿兵力也都在強化存在和威懾,在此背景下,社會各界紛紛擔心,繼貿易戰和科技戰后,“中美會不會爆發軍事沖突”?
任何軍事沖突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但至少,其中一方需要具備與對手進行沖突的意愿和條件。基于理性的判斷和推測,筆者嘗試回答,美國大選前后,中美軍事沖突的風險有多大?風險究竟在哪里?
美軍在抓緊做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的各種準備
美國軍方認為中國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灰色地帶競爭和藍水海軍等三個方面都對其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這種認知發端于2009年前后,經歷了一個不斷演變、發酵的過程。2009年至 2012 年,在奧巴馬政府的主持和推動下,“空海一體戰”和《聯合介入作戰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的醞釀與發布,標志著美軍已開始從戰術上嚴肅看待所謂的“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
2012年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這是繼9.11事件之后,美國安全和國防戰略的又一次重大轉變。美國宣布結束伊拉克戰爭,并成功擊斃本·拉登,以反恐戰爭為首要任務的國防戰略正式宣告結束。新的國防指針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防務重心開始真正瞄準中國。
2015年前后,美國戰略界實際上已有定論,認為美國面臨的海上戰略環境正在發生巨變,“失敗國家”和恐怖主義雖然仍能對美構成廣泛的重大挑戰,但大國地緣競爭已經上升為美國面臨的頭號海上威脅,其中與中國的海上競爭又被視為重中之重。2015年奧巴馬政府發布的《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國家安全戰略》和《亞太海上安全戰略》等文件指出,“印度洋—亞洲—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日漸增長,正在構建和部署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對我們全球海上進入能力構成挑戰”。這實際上已經將中國鎖定為美國最主要的海上戰略競爭對手。
這之后,美軍非常嚴肅地考慮在南海與中國的競爭甚至是武裝沖突問題,針對中國提出了一系列作戰概念,比如海軍的“分布式殺傷”(現已改稱“分布式行動”),陸軍的“多域戰”,以及海軍陸戰隊的瀕海作戰概念等。這些概念多數以南海為作戰的假定環境,圍繞南海局勢進行戰略建設和兵力推演。近年來,我們可明顯看到美軍圍繞與中國在南海的潛在沖突加緊做各類準備。美國的攻擊型潛艇、戰略轟炸機、水面艦艇等越來越多地加強了針對南海的聯合演練。
2017年5月美國海軍發布的《未來海軍》白皮書明確了美國海軍在遠洋、近海和瀕海地區不同的海洋控制任務,要求在不同類型的海域里,美國海軍都必須具備攻擊、欺騙和防御敵方導彈、潛艇、網絡和電子攻擊的足夠能力。2018年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指出,“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近期訴求是要構建在印太地區的區域霸權,長遠來看是要取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這份報告聚焦“打贏一場戰爭”,即與中俄等國可能的高烈度戰爭。
在政策層面,近年來美國越來越流露出對力量對比變化的強烈不滿或焦慮,認為,隨著中國的崛起,時間在中國一邊,臺海和南海等區域的局勢走向對中方有利,對美國不利。2018年4月26日,現任美軍印太總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在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名審議聽證會上表示,“除了戰爭之外,美國已經沒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國控制南海”。
因此,無論從戰略、政策還是操作層面,美國都有強烈的沖動,通過外交、軍事和輿論等手段去刺激、挑動西太局勢,以盡可能地掣肘中國,戰爭解決的意愿也水漲船高。
美國挑起對華軍事沖突的條件仍不完備
然而,在美國眼里,中國畢竟不是一般的對手。中國是核大國,綜合國力僅次于美國。雖然軍力在全球層面上遠不能與美國相匹敵,但是在臨近的西太平洋地區,與美軍的總量和能力差距在快速縮小。按照蘭德公司等美國智庫做的仿真推演,美國與中國在臺海、南海一旦發生戰爭,哪怕是局部的,破壞性也是巨大的,美軍即便能贏,也只會取得慘勝。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勝算和機會將越來越大。
2014年以來,美軍發起以“改變未來戰局”的顛覆性技術群為重點的第三次“抵消戰略”,大規模增加作戰平臺數量,積極創新作戰概念,不斷推動防務重心和資源向印太地區轉移,試圖在技術上對中國形成新的代差,在規模上彌補數量劣勢,在作戰概念和想定方面針對中國量體裁衣。但上述任務都過于困難和復雜,轉型需要時日,短期內美國并不太可能做好在海上與中國大動干戈的準備。美軍如果采取諸如轟炸或奪取中國在南海駐守島礁的行動,則勢必招致中方的全面報復,這顯然是當前美國各界除了那些極端狂熱分子外希望避免的。
2015年開始,美國不斷有高官揚言,要在南海給中國來場“流鼻血式的”(Bloody Nose Attack)沖突。種種跡象表明,美國可能確已做好在南海搞一場中低烈度沖突的準備。美軍近期在南海開展的每次行動,包括“航行自由行動”、抵近偵察和航母及轟炸機的戰略巡航,很可能都備有一旦與中國軍隊發生正面摩擦之后該如何進一步行動的升級預案。這意味著,如果有摩擦和沖突發生,哪怕是意外的對峙升級,美軍可能很快從和平施壓、威懾和挑釁模式轉入戰爭模式。
在目前的南海、臺海復雜形勢下,無法排除這樣的可能:為打破目前的僵局,給中國國內外造成很大的影響,掣肘中國的海上崛起,并服務于美國國內大選的政治需求,特朗普政府希望在它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中國發生一場可控的沖突。這場沖突可能持續時間很短,(指戰艦、軍機等)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有激烈的電子對抗或短暫的交火,涉及的主要作戰平臺數目不多,可能是個位數的。但美軍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它并不知道中國政府和人民解放軍會如何反應,對挑釁行動造成的后果是否真正可控、不致引發大規模武裝沖突缺乏把握。

美國海軍“里根”號航母打擊群2020年夏季在中國近海巡航軌跡。

美國海軍EP-3E電子偵察機2020年8月15日在南海、臺海地區的航跡圖。圖片來源/“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網站,http://www.scspi.org
因此,從主觀角度看,美軍有挑起沖突的意愿,但決心不足。軍事沖突畢竟不同于貿易戰和科技戰,一旦開啟,可能誰都無法充分預料后果。當然,這只是理性推測。由于中美關系惡化和美國自身的內部矛盾,美國政客“甩鍋中國”和對中國強硬已成“時尚”,如果因為大選導致美國國內矛盾激化,其政軍體制出現混亂狀態,美軍指揮鏈條出了問題,極端勢力就可能在南海等方向采取冒險行動。
目前來看,美軍指揮體系依然相對穩定,五角大樓高層也非常擔心中美在海上發生沖突,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本人較為穩健,在強調競爭的同時,依然強調危機管控的重要性。7月21日,埃斯珀視頻連線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并發表演講,盡管花了很大篇幅渲染“中國海上威脅”,但也明確表示,“無意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希望年內實現任上首次訪華,與中國“建立必要的危機溝通體系”。未來情況如何,尚有待觀察。
意外和緩和哪個先到?
與猜測中美雙方的意圖相比,發生意外事件的可能性更值得關注。中美兩軍每天都會在海上發生數起海空相遇事件。雖然絕大多數互動是專業、安全的,但發生摩擦的風險仍在急劇升高。根本的問題是,現實中的中美海空相遇的很多是有意而為的,對抗性本來就比較強,比較突出的有三大類:一是,美方艦艇頻繁闖入中國南沙駐守島礁的12海里或西沙領海及內水,中方不得不進行驅離和攔截。2018年9月30日,美國海軍“迪凱特”號驅逐艦與中國海軍“蘭州”號驅逐艦在南薰礁12海里內險些發生碰撞,最近僅41米左右。二是,美軍機在空中實施越來越多的抵近偵察,中方必然會采取警戒等相應措施。三是,中美雙方每年都會在南海進行各類軍事演習,通常都會針對對方進行偵察和監視。這種行為從軍事上可以理解,但如果太過接近,就容易引發摩擦。2013年12月,美軍“考本斯”號巡洋艦異常接近正在南海進行訓練的中國海軍“遼寧”號航母編隊。近些年,美方更是越來越不注意保持安全距離。
現在,一旦中美爆發任何海空意外,基于目前中美總體關系不斷惡化的氛圍,進行有效管控并阻止直接升級的難度是很大的。中美兩軍現有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不足以應對海上復雜局面,兩軍之間雖有《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等安排,但都是為意外相遇而設立的。中美在2015簽署了《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和《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兩個備忘錄,其認真落實離不開合適的政治氛圍和一定的戰略與政策互信,而這些在當前的中美關系當中是稀缺的。1999年至今,中美每年都會舉行海上軍事安全磋商,不過近兩年的成效和氣氛都變得不盡人意。
唯一相對較為穩定的是兩國國防部長直通電話和不定期會晤,但以相互表明立場為主。8月5日兩國防長通了電話,共同強調避免誤判和加強危機管控,發出了穩定的信號。下一步,雙方有必要共同采取一些降低局勢緊張的具體措施。
中國維護主權與海洋權益,追求合情合理的國際空間,與美國維系亞太海上主導地位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哪怕中國什么都不做,只要力量在發展,就會被美國視為挑戰。更何況,中美兩國的制度和國防文化都截然不同,加大了彼此矛盾。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軍事競爭在所難免,恐非“大交易”或“大妥協”能夠解決,而是需要經過長期的斗爭和博弈,才能找到新的平衡。
無論如何,一場失控的軍事競爭,對雙方而言都是災難。當務之急,是要回歸理性,認識到自身力量的限度和利益的邊界,并進行適當的戰略調適,相向而行謀求緩和目標的緊張氣氛。雙方尤其需要重新激活溝通和對話,將自己的訴求和意圖明白無誤地告訴對方,而不要過度宣泄情緒,更不要將軍事問題政治化。
(作者為“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