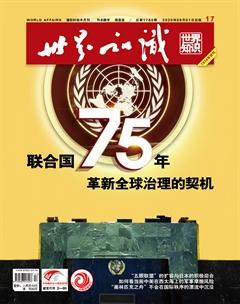阿聯酋核電站引發對中東核未來的擔憂
張文
近期阿聯酋消息不斷。在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這個驚天新聞背后,該國國內經濟和科技的一系列進展也足以引人矚目。7月20日,該國首個火星探測器“希望”號在日本種子島航天中心發射升空,這也是阿拉伯國家的首個火星探測器。8月1日,在經歷十余年等待、三年延期、預算超支逾40億美元情況下,該國巴拉卡核電站啟用,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投入商業運營的核電站。近日阿聯酋水電公司又宣布已完成阿布扎比一座光伏發電項目的招標工作,該項目完成后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單體太陽能發電站,與巴拉卡核電站一樣,也是該國為“告別最后一滴油”、實現能源多元化所做的準備。有報道稱,該國還將建設第一座垃圾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相結合的電站。
8月1日啟用的是巴拉卡核電站四個反應堆中的一號機組。如果全部反應堆一起運營,核電站裝機量將達到5600兆瓦,可以滿足阿聯酋1/4的用電需求,每年減少碳排放2100萬噸。巴拉卡核電站的投產標志著阿聯酋正式加入全球核能俱樂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稱其為“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阿布扎比王儲扎耶德也自豪地宣稱“在和平發展核能的道路上翻開新篇章”。但資深核能專家指出,新核電站的落成將為這片土地埋下“多重風險”——從項目安全隱患、核擴散可能,到地區競爭對手之間的核軍備競賽及其對地區穩定的破壞。
石油出口國謀求多元化發展動機
阿聯酋是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生產國之一,石油和天然氣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近1/3。2019年該國原油出口額達到500億美元。化石能源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也拉動了阿聯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的高速增長。但正如阿布扎比王儲提出的問題所示:“50年后,當我們只剩最后一桶油,并且它被運往國外時,我們是否會感到傷心?”
的確,自20世紀70年代起,人類的發展觀已經發生深刻轉變,逐漸認識到長期過度依賴化石能源而造成的過度排放、環境惡化等問題。2020年石油價格的暴跌也暴露了化石能源市場正發生著劇烈變化。一些國際機構和能源專家研究表明,經濟增長對石油的依賴程度已接近節點,對石油的需求在達到峰值后將進入平臺期,高油價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中東產油國越來越多地形成共識:單一依賴石油的經濟之路是不可持續的,系統依賴石油的發展模式恐將扼住國家命脈。因此,多元化發展是中東國家應對石油枯竭時代的未雨綢繆,更是其謀求國家經濟轉型、尋求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東地區不乏依靠石油發展起來的國家,但其持續繁榮卻不能僅靠石油,需要建立多元的經濟體系。但替代化石能源的并不僅僅是核電。從成本角度考慮,數據顯示到2012年巴拉卡項目動工時,太陽能和風能成本已急劇下降。據分析,自阿聯酋公布其核能開發計劃的2008年至2019年的十余年間,太陽能光伏成本下降了89%,風能下降43%,而核能成本卻上升了26%。海灣地區擁有非常豐富的日照資源,而開發核能的經濟效益并不十分突出,因此有專家質疑,阿聯酋開發核電是否別有企圖?事實上,核能除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不容小覷外,其戰略意義更加深遠。換言之,從戰略上說,一旦擁有核技術,一個秉持中立、平衡外交的國家,是否有可能迅速轉變為地區沖突的積極干預者?
核能項目安全成廣泛關切
針對如上質疑,阿聯酋核能公司(ENEC)發表聲明解釋說,太陽能和風能等間歇性可再生能源不能保障連續發電,無法滿足需求。但巴拉卡項目安全技術是否可靠,又是人們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有英國資深核咨詢專家認為,巴拉卡反應堆在安全方面的設計并不過關。該專家在其撰寫的一份報告中詳細介紹說,巴拉卡反應堆缺乏關鍵的安全設施——用于組織堆芯熔化的“堆芯捕捉器”,也沒有第三代深度防御加固裝置,以保護反應堆避免因遭受導彈或戰斗機攻擊而造成輻射泄漏,而上述兩者早已成為歐洲新核反應堆的“標配”。對此,阿聯酋當局表示,自2010年以來,已累計邀請并接待過來自國際原子能機構、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等機構的40多個國際考察團,能夠保障巴拉卡核電站技術安全。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中東的土壤是否適合發展核能源。中東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地緣政治極其復雜,各種危機多發,有統計表明該地區的基礎設施遭受的空襲比地球上任何其他地區都多。2019年9月沙特阿拉伯石油設施遭到18架無人機和七枚巡航導彈的襲擊,這一襲擊曾暫時削減了沙特逾一半的石油產量,進一步暴露了阿拉伯半島關鍵基礎設施的脆弱性。一旦在巴拉卡發生事故,放射性污染必然會從阿聯酋擴散到鄰國。有專家指出,甚至沒有任何區域議定書來確定責任。
中東核未來引發多重擔憂
阿聯酋政府聲稱,其防空系統能夠攔截任何針對其核設施的襲擊,且表示阿聯酋對和平發展核能有承諾,并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國際原子能大會的“核安全行動計劃”,言下之意是國際社會應安心對待該國的核計劃。
但巴拉卡核電站畢竟使阿聯酋成為中東地區的第三個“擁核”國家,此事非同尋常。中東前兩個“擁核”國家是被認為已經實際擁有核武庫的以色列和引起核危機的伊朗。鑒于該地區的特殊地緣政治局勢,巴拉卡核電站啟用引發了人們對中東核項目的多重擔憂。

工作中的巴拉卡核電站雇員。
一是擔憂在民用能源掩護下研發核武器。事實上,在阿聯酋巴拉卡核電站投入使用的當下,土耳其、約旦、埃及也有建設核電站的計劃,沙特阿拉伯則正在首都利雅得的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科技城建設第一座核研究反應堆。雖然沙特和阿聯酋一樣強調其開發核能的目的不會超出建立民用能源項目的范圍,但沙特卻尚未正式宣布放棄發展核武器。目前引發世界關注的伊朗核問題,起點也源自20世紀50年代伊朗對民用核能設施的建設。
二是擔憂中東各國的秘密核計劃引發地區局勢的“核裂變”。伊拉克的秘密核設施在美國1991年發動海灣戰爭期間被發現并拆除;伊朗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指責其違反核不擴散條約后,直到2002年才公開承認核設施存在;而其他諸如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和敘利亞等國家也有秘密發展核項目的歷史。因此,世界普遍擔憂阿拉伯半島在默默變成核區域后,突然爆發嚴重后果。
三是擔憂核能開發引發核軍備競賽。沙特王儲表示,一旦伊朗獲得了核武器,沙特也打算獲得核武器。沙特的核追求野心可以追溯到2006年,當時該國與海合會其他成員國希望在一項聯合計劃的框架內尋求發展核能的選項。沙特已將其核計劃納入國家2030愿景之中,理由也是為使國家經濟發展擺脫單一的石油資源路徑。人們擔心,以色列已在美國默許之下樹立了一個缺乏核透明度的負面先例,中東地區是否會出現基于所謂“震懾”的核軍備競賽,成為引發核戰爭的導火索和“馬前卒”,甚至導致世界性危機?
在當前伊朗核問題陷入僵局、中東地區核擴散趨勢上升的背景下,上述擔憂不無道理。
(作者為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