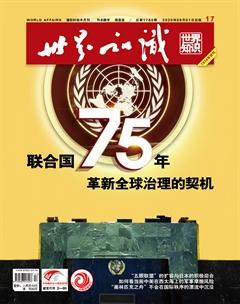一戰后的歐洲何以混亂血腥
馮玉軍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并未因“十四點計劃”和“凡爾賽體系”而實現永久和平、撫平戰爭創傷。對于戰敗國來說,一戰的結束反而是另一場巨大暴力災難的開始。一戰正式結束到1923年7月《洛桑條約》簽署之間的“戰后”歐洲,是地球上最為混亂的地區。內戰交織著革命和反革命的廝殺以及新興國家間的邊界沖突,遍布從芬蘭到高加索的暴力沖突導致近1000萬人死亡、2000多萬人受傷。正是在這樣的戰爭廢墟上,納粹主義等極端主義意識形態興起,并由此導致了二戰的爆發。
一戰雖已過去百年,但其直接后果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至今仍困擾著世界。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一戰后歐洲的失序、戰亂和血腥暴力的發生?都柏林大學羅伯特·格瓦特教授在其《戰敗者:兩次世界大戰間歐洲的革命與暴力(1917-1923)》中,用豐富的史料和細密的論述揭開了那段不堪回首而又發人深省的歷史。
一戰后的歐洲沖突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國家之間爆發的戰爭,如蘇波戰爭、希土戰爭等;二是在俄國、芬蘭、匈牙利、愛爾蘭和德國部分地區爆發的內戰;三是政治暴力所引起的社會和民族革命。
一戰導致哈布斯堡、羅曼諾夫、霍亨索倫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國解體,帝國崩潰和民族國家興起導致了更多的沖突。在“民族自決權”理論的刺激下,一大批新興國家涌現出來,為了爭奪土地、資源、人口而相互廝殺。可以說,帝國的解體在歐洲制造了新的“暴力邊界”,“領土修正主義”讓歐洲在之后的幾十年中紛爭不斷。盡管想建立單一民族國家,但波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仍是些小型的多民族帝國,它們和哈布斯堡帝國時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僅僅是疆域縮小和民族層次結構翻轉了而已。
列寧曾說,“戰爭引起革命”。的確,如果一戰沒有爆發,僅僅是國內的政治動蕩或民眾反抗,不太可能導致沙皇政權徹底崩潰。戰爭引發的多重危機特別是食物危機加劇了社會緊張,俄國首都由于面包短缺而引發的抗議成為推翻沙皇統治的直接導火索。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是自1789年以來通過革命運動第一次接管了一個國家,革命和隨后席卷全國的內戰,把相互作用的革命與反革命運動迅速傳播開來。猶太人是內戰受害者中特別突出的群體,但事實上,沖突影響的是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和社會團體,由此推動了一場為生存而戰的原始斗爭和不斷循環永無休止的暴力復仇。
一戰后的歐洲,對暴力的推崇、喪失人性的復仇意識以及塹壕戰的經驗把人們對暴力的認同推向極致,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社會中都形成了一種野蠻性。它猶如被從潘多拉盒子中釋放出來的怪獸,引發了一系列相互關聯、但邏輯和目的較之一戰都更加危險的沖突。與一戰那樣以迫使敵人接受和談條件為目的的戰爭相比,戰后歐洲的沖突更加肆無忌憚。它們是你死我活,以全部消滅敵人為目的戰爭。在此過程中,各種政治派系的民兵為自己的利益承擔起了國家軍隊的角色,他們所實施的殺戮使朋友和敵人、軍人和平民的界限變成了可怕的模糊不清。這突破了宗教戰爭以來歐洲對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進行區分、把敵人當作“正當的對手”以此對武裝沖突進行約束的傳統。在這一時期的沖突中,死亡的平民人數往往超過士兵。
戰敗引發了戰敗國深刻的社會政治危機,而對戰敗國的掠奪導致了新一輪的復仇主義。《凡爾賽和約》未能平息一戰所引起的憤怒,一戰的慘烈以及戰后戰勝國對于戰敗國敲骨吸髓般的掠奪導致沒有任何一個戰敗國可以回到戰前的國內穩定與國際和平的狀態,而在“挽回”失地和人口的渴望驅使下,暴力修改條約也成為極端主義勢力蠱惑民眾、奪取政權的最好旗號。
一戰后的歐洲,清理“內部敵人”的邏輯大行其道。與停戰相伴隨的是四處蔓延的革命和政權的暴力更迭。只要權力出現真空,那些民兵就會按照對暴力復仇的想象去實行。而一個國家對其內部敵人的戰后“清掃”,往往被視為其重生的一種必要前提、一種暴力復興的形式,它可以證明戰爭中犧牲的意義,不管是戰敗還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