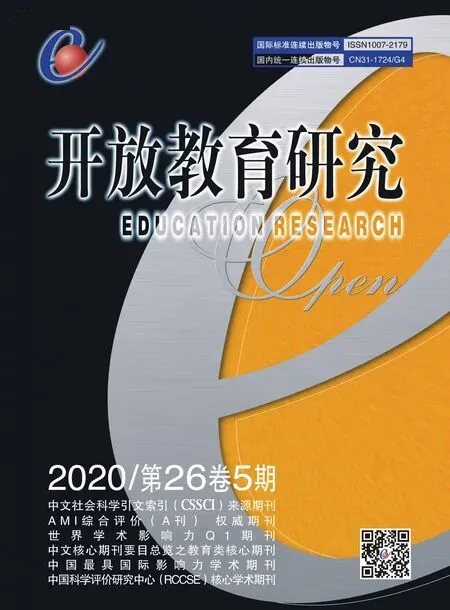學生反饋素養論綱:內涵、模型與發展
董 艷
(1.北京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北京100875; 2.北京師范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問題提出
反饋是教學環節中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因素之一。約翰·哈蒂等(Hattie et al., 2007)認為,反饋是由主體 (如教師、同伴、書本、父母、經驗等)提供的關于個人表現或理解的信息。一直以來,關于反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師和同伴反饋方面。陳晴晴(2019)探索了教師對學生提問的反饋狀況;侯中太(2019)分析了基于活動理論的同伴學習活動反饋效應。近些年,隨著大數據及智能技術的發展,大量研究開始探討如何利用技術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反饋。陳明選等(2018)認為,測評大數據為學習者狀態分析和教學優化提供了客觀的數據支持;黃昌勤等(2019)探討通過動態可視化呈現學習者云空間的行為關聯數據,為他們提供及時反饋、監督與指導。張慧等(2018)探討了智慧微格教室如何結合學生需求提供精準反饋,教育人工智能機器人如何提供個性化反饋與自適應學習逐漸成為這一領域聚焦的熱點之一(徐歡云等, 2019)。國內外相關研究均聚焦于如何為學習者提供反饋以及學生應如何吸收反饋。多數研究將學習者置于“被關懷”的角色,或者是被動接收者的角色加以探討,忽視了學生自我反饋的能動性,也忽略了學生只有投身到積極和有效的反饋中才能夠帶來“教學相長”。
隨著學習科學的發展,反饋研究逐步聚焦于學生個體并以不同形式出現在學術領域:1)關于學生對反饋的感知研究。中國參與PISA2015國際測試的四省 (市) 學生的感知反饋指數低于新加坡和美國;學生得到關于“我在這門課上的表現如何”的反饋相對較少;感知反饋對科學素養水平不同的學生存在的影響具有異質性(段鵬陽,2019);2)關于加強學習者利用反饋促進能力發展的研究。何克抗(2017a)談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研究手冊(第四版)》時指出,我們應改變原有的機械反饋模式(也稱技術模型),以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支撐的反饋模型為參考,從學習者角度去尋求反饋、讓反饋發揮更大的作用與影響,積極倡導教師有效提供和使用反饋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孟凡茂(2016)通過研究計算機支持的形成性評價,認為反饋可以通過成功預期和任務-價值的信念進行預測;3)關于學生反饋文本的分析研究。馮翔等(2019)探索了大規模在線教育環境中學生反饋文本體現出的學業情緒問題。綜上,從學生角度展開的研究,雖然強調學習者的能動性,但仍未將學生反饋作為高于能力的“素養”進行探討。
海外學者從2012年起已將“反饋素養”(feedback literacy, FL)作為學術概念進行解構,并在課程教學中探討如何設計反饋的融入機制以便促進學生主動學習。長期研究逐漸形成的共識是:反饋是可喚醒個體持續改進和有效監督自我學習過程的內在動機,從而影響學生學業表現 (Carless & Boud, 2018)。為此,反饋不僅要關注學習者的接受程度及其能力,還要關注學習者的反饋產出。相比海外的反饋研究體系,我國在學生反饋素養的應用價值及實踐案例研究方面略顯不足。如何重新思考和構建適合我國本土環境的“學生反饋素養”研究和實踐體系,通過研究我國學生反饋素養的內涵特質,并在課堂甚至遠程教學環境中融入支持學生反饋發生的機制模塊,加強學生反饋素養的培育,是促進學校教育教學中師生有效互動、生生相互促進、“以學為中心”等這些早被呼吁但并未有效實現的教育理想成為現實的可探究途徑。在大規模疫情期間,很多學生在家進行遠程在線學習,如果能夠培養他們良好的反饋素養,與遠端教師積極互動,促進學生自我調控和學習投入,這樣的在線學習就更有可能提升質量。
二、研究團隊與主要觀點
反饋素養作為一個正式的學術概念,最早出現在英國學者薩頓的論文中(Sutton, 2012)。通過分析反思型人才的反饋過程,薩頓認為反饋素養是學業素養的一部分,跨越認知、社會和情感領域,且由三個關聯要素組成。反饋素養能促使學生吸收反饋信息,充分利用反饋開展學習。但學生反饋是個復雜而富有挑戰性的過程,反饋素養也會受到教師身份認知的影響。薩頓的研究提醒教育者應充分重視學習者的核心地位,重視“以學為中心”的教育思想。這一概念的提出豐富了學生反饋研究的內涵,從關注學生作為“信息接受者”及其對反饋的內在感知,到學生作為“信息發送者”利用反饋與他人交流,并激發自身思考學習者反饋的價值,對相關領域的發展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薩頓提出反饋這一概念時并未引起重視,學者們關注學習者作為反饋主體的研究隨著“以學為中心”思想的流行而逐漸活躍起來。從2018年起,重構學生反饋素養模型的研究迅速展開。通過文獻分析發現,當前聚焦學生反饋研究團隊和主要觀點如下。
(一)澳大利亞團隊:博德教授與莫蕾教授合作為代表的“要素派”
澳大利亞團隊主要以大衛·博德(David Boud)和伊麗莎白·莫蕾(Elizabeth Molloy)兩位教授為代表。早在薩頓之前,他們就認識到學生反饋是高等教育領域有爭議且令人困惑的重要問題,并于2013年提出以可持續發展評估為基礎的反饋模型。這一模型視學習者為驅動學習的關鍵角色,通過活動激發學習者主動反饋。他們認為,教師要認識到課程設計環節學生參與反饋的重要性,要為學生發展反饋意識設計活動和產出的機會,并提供標準促成有效評判,再通過任務的嵌套、增加任務的挑戰性,使學習者不僅成為反饋的發現者,還能成為反饋的提供者。該模型從關鍵教學環節中提出可操作性程序,但缺乏體系化構建的細致。盡管這一團隊的研究成果在薩頓后發表,但并未引用和涉獵學生反饋素養概念。直到2018年,博德與大衛·卡勒斯(David Carless)合作發表文章,才真正采用學生反饋素養概念并加以拓展。
博德團隊后來還探討了如何建立反饋對話機制,并利用交互分析機制促進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Ajjawi et al., 2017)。莫蕾(Molloy et al., 2020)參與合作探討了如何圍繞學習者構建學生反饋素養的操作性類目框架,并強調學習者“作為積極參與者,而非單一的信息接收者”的主體觀,從而避免以往對學生反饋素養僅從概念或設計角度開展研究,卻缺乏實踐研究的局限。類目的數據來自于澳洲兩所高校共5000多份學生數據的調研,包括七個維度(31類別),從不同教學設計層面支撐教師將學生反饋素養嵌入到教學活動中。博德教授后又多次與其它團隊合作開展富有成效的研究。
(二)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團隊:卡勒斯教授及其跟隨者的“模型派”
卡勒斯的研究始于2005年,最初關注學習導向的高教評估、同伴評價與反饋,后來提出如何發展可持續的反饋框架,以及在教學對話中使用范例說明高質量反饋工作的本質。卡勒斯后來還帶領研究生構建反饋概念模型開展教學干預研究,在模型建設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卡勒斯等2011年就提出發展可持續反饋,學生需主動發展自主學習能力,教育者要鼓勵學習者參與反饋實踐,利用范例教學提升學生反饋能力。2013年他與楊(Yang & Carless, 2013)合作提出三角對話反饋結構模型,從學生、教師、機構三個視角探討反饋機制。他對學生反饋素養的真正關注是2018年與博德教授合作發表《發展學生反饋素養以促進反饋的吸收》文章,提出加強反饋理解、判斷和情緒管理的綜合過程,促進學生反饋行動的產生。但由于模型過于簡單,他在第二年又獨自提出反饋環(feedback loop)模型,全面分析了學生反饋螺旋的長效運作機制(Carless, 2019)。反饋環模型(見圖3)認為,外在(導師、同伴、自我)和內在(動機因素、自我調控策略、設計者提供的反饋機會)的多種因素共同促進反饋螺旋框中的單循環和雙循環的內在機制有序運行,同時對未解決的難題進行轉化。
卡勒斯教授又聯合英國薩瑞大學研究團隊探索了師生反饋素養的交互作用機制,首次提出教師反饋素養(Teacher Feedback Literacy,TFL)概念和師生反饋素養的聯動發展機制(Carless & Winstone, 2020)。他的團隊還探討了如何在課程中嵌入反饋素養的關鍵機制,通過激發、處理和實施等措施開展有效的教學反饋(Malecka et al., 2020)。他的學生莊善宏博士(Chong, 2020)發表了生態視角下的學生反饋素養重建模型。我國內地學生反饋素養研究團隊興起也多受其啟發。
(三)英國薩瑞大學團隊:溫斯頓研究員為代表的“實操派”
溫斯頓(Winstone)是第三組探索學生反饋素養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團隊核心。上文已提到她和卡勒斯教授之間的合作,但那篇文章并非雙方首次合作。在此之前,溫斯頓研究員已牽頭與他人合作完成一本專著(Winstone & Carless, 2019),集大成地概括了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成果。全書包括導論和反饋挑戰、發展學生反饋素養、促進學生反饋參與、技術增強反饋過程、通過評估設計賦能反饋、賦能反饋對話過程、編織內在和外在反饋、實施同伴反饋、反饋關聯維度、反饋研究的未來等十章。專著還探討了高等教育背景下設計有效反饋過程解決面臨的挑戰及如何設計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強調對話式教學、學生如何更好地吸收反饋為核心的思維新范式。正如書中描述,反饋是一種多視角的探索話題,沒有一種所謂正確的方法能解決所有問題。重要的是,如何從以信息傳遞為中心,轉向以支持學生學習為中心,呼喚學習者積極參與和吸收反饋。
本文將溫斯頓定義為實操派,緣于她在教學領域開展了許多示范性和操作價值的研究。她與另一位合作者那什(Nash)教授,在2017年利用195篇(1985-2014年期間)文獻分析結果, 從受眾過程視角探索如何利用多要素開展反饋,提高學生參與的能動性。他們認為以前的許多研究均具有潛在的假設:只要提供反饋,學生就會吸收。但如何尋求和獲得反饋才是學生們面對的最大障礙。為此,他們以“會很有用,但我不會用”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應。雙方還合作開發了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工具包(Winstone et al., 2019)。該工具包為如何培養學生反饋素養提供了實操支持,為提升學生反饋素養提供應用指向。
(四)我國大陸地區的研究團隊:分散興起的“新秀派”
我國大陸學者開展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源于海外學習經歷。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應用語言學中心的許悅婷師從卡勒斯教授,和導師合作探討了如何基于教師反饋提升學生反饋實踐的意識和能力(Xu & Carless, 2017)。隨后,她聯合位于深圳的哈爾濱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韓曄發表了關于學生反饋素養與反饋如何促進學習的文章,研究均以中國本土大學生為樣本開展調研,以第二語言學習為研究背景,通過兩個案例探討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機制(Han & Xu,2019)。還有學者(Zhou et al., 2020)聚焦于促進學生反饋素養提升的師生關系研究,特別是反饋過程的尊重問題。總的來看,我國大陸團隊在學生反饋素養方面的研究,還相對分散、力量單一,亟待加強相應領域的研究投入。
三、概念模型
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源自教育評價及評價素養的研究。隨著學生反饋素養研究的深入,相應的概念模型也不斷被提出、重構和檢驗。下文針對其中具有實踐價值的六種主要概念模型進行介紹。
(一)理解觀
薩頓(Sutton, 2012)認為,學生反饋素養是一套通用的做法、技能和屬性,是一系列情境化學習實踐,包含認識論維度、本體論維度及實踐性維度。三個維度均依賴學生對反饋及其要素的理解。認識論維度強調學生必須發展兩種不同反饋類型的理解能力:關于知曉的反饋(feedback on knowing)和為了知曉的反饋(feedback for knowing)。前者指學生就課程中所學知識的質量和數量接收到的知識性反饋,具有修正性和評估性,用來解決“我該怎么做”的問題,是一種教學形式;后者強調學習者主動利用反饋探索下一步怎么做。本體論維度認為學生反饋素養是自我認同和自我效能感高的表現。對學業能力有信心的學生往往更專注于識別和解釋有助于提升自身學習的反饋信息,即使在沒有反饋的條件下也能夠清楚地表達觀點來索取反饋。實踐性維度強調反饋素養理論的應用價值,認為學生基于反饋采取必要的行動是開展下一個任務的必要條件。上述維度也被具化為:知曉(knowing)、身份建構(being)和行動(acting)。用薩頓的話說,接受反饋可能是學生自我發展的過程,學生吸收教師描述的知識信息證據,從自我角度確立和認同信息對自我發展的價值,然后思考和采取行動。目前我國學生學習儀表盤的研究就應用了這一模型(麗姿·貝內特&肖俊洪,2019)。
卡勒斯與博德(Carless & Boud, 2018)支持薩頓的研究并擴展了學生反饋素養的內涵,認為學生反饋素養概念內涵豐富,學生要充分把握和理解外來信息和兼具反饋意識,并使用獲取的反饋信息采用有效的工作和學習策略。情緒管理在這一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四個關聯要素包括感知反饋、作出判斷、管理情緒和采取行動。前三者在流程上是雙向的,彼此之間可以雙向激發,而同時激發更容易促進反饋行為發生。但在具體操作時,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獨立發生(見圖1)。具有良好反饋素養的學生能準確感知自己在反饋過程中的積極角色,在反饋過程中對學習作出合理的判斷,并以積極方式管理情緒。

圖1 學生反饋素養的行動要素模型
學生反饋會因特定的學科、課程與情境的差異而不同,與先前個體經歷和自身特征有關。在第一階段,學生要能感知到反饋,并認可反饋的價值,主動感知甚至達到“欣賞反饋”的程度。現實中,學生往往更重視明確的糾正性反饋以及技術增強的反饋方式與內容,而不太重視書面評價之外的其他反饋。在第二階段,學生除非有持續的機會與他人觀點進行比較,否則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Boud et al., 2013)。學生更喜歡那種說明性的質量標準,當判斷標準過于抽象和密集時,他們反而難以作出判斷。在第三階段,學生往往在應對反饋時存在負面體驗,但與教師之間的信任關系會有助于情緒管理。反饋素養水平高的學生能夠專注于形成性信息,并對信息保持積極的看法。相反,反饋素養水平低的學生往往認為受到批評,不愿或不積極投入反饋并與老師互動,甚至防御或者偽裝。在卡勒斯看來,這一模型還不足以說清楚反饋的內在機制。
(二)結構觀
2013年,楊與卡勒斯(Yang & Carless, 2013)聯合發表的三角結構對話模型從三類教育存在(學生、教師、機構)出發,分析如何嵌入結構性對話反饋機制促進學生學科學習 (見圖2)。學生的認知、教師的社交-情感支持、學校的組織結構都會帶來不利于反饋的障礙。為明晰出發的方向,三角維度又衍生出六種關鍵特征(學生投入度、自我調控、信任關系、情感敏感性、彈性約束、調動資源)。其中,主要障礙在于學生認知。有效使用反饋需要把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決學科問題,提高自我調節能力,指導學生運用知識和技能確立假設和測試解決方案,并幫助他們評估當前的學習行為和期望之間的差距。教師的社交-情感支持,主要通過建立師生信任關系和避免情緒過度敏感解決相關的障礙。情緒敏感性是產生共情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可以支持建立信任關系,并提高反饋吸收效果,構建積極的學習傾向。

圖2 對話反饋的三角結構模型
學校方面的障礙來源于組織結構和資源分配是否靈活,如大學的評估政策、實踐和組織方式。理想的情況是,大學應該配備足夠的人力和物力,減少不必要的限制,在資源無法滿足的情況下通過提供反饋和靈活調動工具和資源,特別是技術工具障礙。結構維度包括反饋時間、順序和模式,與產生和提供反饋的資源相關。模塊化課程、大班規模、學習生活的多種需求、工作量增加以及產生研究成果等的約束,加劇了設計有效反饋的挑戰。
(三)循環觀
這一觀點以卡勒斯(Carless, 2019)為代表,認為反饋實踐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通過有限循環促進學生吸收反饋。反饋循環模型(見圖3)希望充分調動多元因素促進學習者持續投入反饋學習過程。反饋螺旋包括單向環和雙向環。單向環處理已經識別的問題或任務,雙向環針對所識別的問題和任務,考慮如何解決,如果不能成功解決,乃需對其重新評估。懸而未決的學習難題也會出現在螺旋框內,必要時進入到單向環或雙向環反饋過程。反饋螺旋圈的運轉還依賴于外在和內在的多方面因素,即一方面來自于教師、同伴或自己的輸入,以及學習者理解反饋的過程, 但不同來源的信息輸入影響學生的理解反饋;另一方面還受到學習者個體動機、自我調控以及設計者提供的反饋機會等多元因素的影響。利用反饋環模型所開發的討論平臺可以分析如何支持和鼓勵學生開展反饋,強化學生的主體角色,促進師生及時對話和提高學生能動性的可見效果(Mayhew, 2019)。

圖3 利用反饋促進學生長期學習投入的循環模型
莊善宏博士(Chong, 2020)并未完全沿襲其導師作法,而是重構了生態學視角下的學生反饋模型。該模型包含三個層級:投入維度、情境維度和個體維度,充分考慮個體及社會情境要素的影響。個體維度主要考慮學習目標、反饋有用性、參與反饋體驗以及科目能力等。可見,這一模型考慮了人和物的要素,但不足之處在于它未對要素之間的協同關系展開討論。
(四)評價觀
加利諾(Garino,2019)認為,眾多學生反饋模型并未真正解決學習者難以吸收反饋信息的問題,因此應該考慮如何讓反饋成功發生。為此,他構建了準備-意愿-能動(Ready-Willing-Able)評價模型(見圖4-a)。學生綜合判斷個體的準備狀態、意愿狀態和能動狀態,并對反饋信息進行價值判斷,做好接收反饋的準備(如接收信息,理解信息),然后進入價值判斷循環(如重視反饋者,強化比較判斷,明晰反饋內容,重視反饋信息),待綜合判斷完成后,進入動機激發和應用適應性學習策略開展行動環節。因此,學習者愿意接收反饋,利用反饋學習,需要隨時作好準備,并愿意參與評價過程。學習者的動機和心態決定反饋能否成功。學習者需要利用策略性的學習行為,將反饋融入實踐變革中。

圖4-a 準備-意愿-能動模型
為解決學生在反饋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障礙,影響反饋過程的完成,該模型還分析了各階段可能遇到的問題,構建了姊妹模型(見圖4-b)。例如,在啟動階段,情緒干擾會影響學生的信息接收過程,概念術語也可能導致學生對反饋目的的誤解;在價值判斷階段,學生會受到動機、特征、關系等消極判斷的影響,對信息的認識膚淺,難以校準甚至抱錯誤期待,不能進行創造性表述;在投入動機階段,學生面臨如何解決掌握型目標和表現型目標(mastery vs. performance goals)、固定心態和增長心態的矛盾(fixed vs. growth mindset);在自主調控學習階段,低效策略也會干擾反饋效果。該研究還納入了一些重要教育理論(如自主學習和成就目標理論)。因此,這兩個姊妹模型的有機搭配為開展有效的教學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學生成功應用和發起反饋提供了可能。

圖4-b 準備-意愿-能動的姊妹模型注:灰色區域是障礙因素
(五)類目觀
莫蕾等(Molloy et al., 2019)質疑已有文獻中關于“在課程中嵌入反饋過程設計,學生就可以有效利用反饋信息提高學習質量”的假設,認為教師融入課程反饋的設計很重要,但反饋必須能調動學習者參與的能動性。學生有效參與和利用反饋投入學習的能力應受到更多關注。為找到與反饋相關或者促進反饋應用的所有學習要素,他們開展了細致的主題分析和類目建構研究,持續了18個月。團隊人員經過分析調研數據、討論代碼、專家咨詢、焦點小組訪談、扎根理論等方法的推進與迭代,持續討論直到理論飽和,最終形成“七要素,31類別”的類目框架表(見表一)。盡管它只是一個框架要素,而非流程式的模型,但這一類目研究為教學干預提供了參考。

表一 學生反饋素養類目
(六)社會文化觀
格拉維特(Gravett, 2020)的研究從社會文化角度,提供了一個偏離主流討論的新觀點,從社會學的角度思考如何推進學生反饋。她認為學生反饋素養是個二元概念,反映了人文主義視角下反饋者和接受者間的關系及所包括的認知和情感兩個維度。在借鑒社會學、唯物主義和后人類主義等文獻的基礎上,她探索了反饋素養和評價與被評價概念之間的互動關系。
該研究還認為,學生參與反饋是一種社會實踐,其能動性是個復雜的因素,超越了人與人的互動,為分析社會領域的人際互動提供了借鑒。例如,研究人員在論文發表前總要接受編輯或同行評價,這就是一種接受社會反饋的過程。同行評審反饋的意見會由編輯反饋給研究者,研究者需要進行認真細致地修改,并將修改過程反饋給期刊,而對反饋的理解或反饋素養水平將決定修改和反饋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像修改過程一樣重要。在醫學領域,醫患之間也存在反饋與參與反饋的問題。醫生的權威性往往會影響患者的真實反饋,有時甚至可能耽誤治療。在社會工作場所,人與人之間更需要一種反饋互動,反饋素養會對組織效率或人際互動效果產生關鍵影響。
四、反饋素養發展機制
反饋研究的初衷是為了促進學生的知識建構和自我調控(Boud et al., 2013; Evans, 2013)。學習者對反饋的實際參與和投入卻不令人滿意,甚至表現出不一致和不均衡現象,個體之間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約翰遜(Jonsson,2013)看來,學生無法投入反饋的五大原因包括:1)反饋沒用;2)反饋不夠詳細或個別化;3)反饋語言過于權威化;4)沒有掌握合適的反饋策略;5)不理解反饋使用的術語。為改變學生無法有效投入反饋的狀況,許多學者開始研究如何建構其發展機制。
(一)教師反饋素養與學生反饋素養的聯動發展
教師反饋一直被認為是促進學生獲得學科內在價值的重要條件之一(Burns et al., 2019)。學生在反饋中的受益部分取決于教師如何創造有利的環境。隨著學生反饋素養研究的深入,教師反饋素養也開始作為積極要素受到關注。它是指教師運用自己的技能和能力,為學生理解和使用反饋提供條件。徐和卡勒斯(Xu & Carless, 2017)的研究將教師反饋素養具化為三種內在聯系的角色:1)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反饋;2)發揮同伴反饋的潛在優勢,激活學生作為反饋生成者的角色;3)參與維護關系和溝通社會情感。教師的角色是利用同伴、人際關系和社會情感的作用激發學習者的內在反饋。
教師通過認知腳手架策略和社會-情感策略為學生提供支持(見圖5),促進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筆者看來,教師反饋素養和學生反饋素養也像圖中的認知腳手架和社會-情感支持的齒輪一樣,形成聯動發展機制。兩者之間的多元對話和有效反饋促進彼此的發展。教師反饋促進學生習得必備的知識和技能,緩解學業壓力和解決現實困難,實現學生自主學習。同時,教師教學要利用社會-情感要素促使學生管理好反饋情緒,保障有效反饋的發生。師生反饋素養的聯動發展模型,建立了認知維度和社會情感維度之間互動關系。

圖5 雙要素聯動發展機制
為降低反饋管理難度,避免教師和學生積累的挫折感抑制反饋,卡勒斯等(Carless & Winstone, 2020)提出了教師反饋素養的新框架,包含設計、關系、實踐三個維度(見表二)。其中,設計維度側重于設計反饋過程,使學生能夠接受并作出評價判斷;關系維度通過構建師生之間的信任關系促使反饋的達成;實踐維度探討教師如何處理學科和組織反饋實踐中可能存在的沖突問題。

表二 教師反饋素養的新框架
(二)同伴反饋更容易發展學生反饋素養
相較于師生之間可能存在的壓力,同伴反饋更容易促使學生反饋。在師生反饋素養聯動發展的過程中,同伴反饋可以參與其中,并起到積極的中介作用(Han & XU, 2019)。同伴反饋無疑對學習行為有支持作用(Carless & Boud, 2018)。筆者認為,同伴反饋不僅有助于提升學生的反饋素養,還有助于促進學生4C核心素養的達成。4C素養(合作、溝通、審辨、創新)作為學生面向未來的核心素養,是未來人才發展素質的共同模塊。合作與溝通是衡量個體能否參與團隊的基礎。審辨與創新是衡量個體是否具有高階技能的主要標志。前者強調學生思維或反饋過程的認知沖突。缺乏認知沖突,將難以激發學生高階思維能力的發展。創新素養體現個體認知的新異性,讓學生在反饋過程中不再人云亦云。現有研究非常關注通過同伴反饋增強團隊合作行為和自我評估能力,這兩項技能是學生未來就業的重要條件(Sridharan et al., 2019)。研究通過分析98名商科學生的協作數據發現,同伴反饋信息中的表揚和批評對團隊合作成就和自我評估技能具有中介作用。
同伴反饋可以被應用于項目式學習中,促進同伴之間的有效合作。學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甚至在不同角色之間切換,提供所需要的反饋。缺乏必要知識和評估能力的學生難以向同伴提供高質量的反饋,或者利用同伴反饋進行學習(Pitt et al., 2019)。同伴反饋需要學生有較好的認知水平,比如了解課程內容、具體任務及相應標準,能用自己的語言解釋或尋找合適的理由進行辯論。同伴反饋的質量還取決于提供者的社會情感成熟度和個人的性格。有些學生因過度依賴教師的反饋,而懷疑和拒絕同伴反饋。周等(Zhou et al.,2020)研究發現,我國學生面對同伴評價會表現出較多的負面情緒,埋怨多,感激少。個體差異也會影響同伴反饋效果。兩個高成就、高動機的參與者要比兩個低成就、低動機的學習同伴,更具有反饋素養。
(三)發展學生反饋素養的關鍵在于激發學生的個體能動性
反饋素養水平高的學習者能積極理解和吸收外來反饋,并在必要時對外發出反饋信息。教學中能動性反饋循環能逐漸減少學生對外部反饋的依賴。學習者如何建立積極應對反饋的心態與方法,是當前研究的關注點。但給學習者提出更多的反饋要求,不意味著減輕教育者的責任。英國學者從多個維度構建了促進積極反饋的多要素分析模型(見圖6),將相關要素分為三大類:信息接收過程組、人際溝通變量組和反饋干預組(Winstone et al., 2017)。其中,反饋干預組影響其他兩組要素,而人際溝通變量組和信息接受過程組之間又會產生相互影響。這些過程有助于學習者養成主動接收反饋的素養。反饋干預組主要聚焦于內化和應用標準、可持續監測、集中提供培訓、反饋提供方式等。信息接收過程主要包括:自我評價、評估素養、目標設定和自我調控、投入和動機等。反饋信息主動接收者應該能夠:1)理解評價和學習的關系,以及回應被評價者的期待;2)評價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是否違背顯性或隱性的評分標準;3)理解反饋的術語和概念;4)掌握合適的評估和反饋所需的技術,以及何時加以使用。另一主要元素是人際溝通變量組,主要包含信息接收者的特征和行為、發送者特征和行為、消息特征、環境特征等。

圖6 學習者主動接受反饋的影響要素模型
學生個體的不利狀況(比如學業成績差)往往阻礙反饋發生,導致反饋內容難以讓人理解。圍繞學習困難的學生反饋,皮特等(Pitt et al., 2019)開展了通過反饋教學法增加學生能動性的研究,即通過反復練習和促進發現同伴之間的互動反饋,成功促進學生反饋素養的形成,更直觀地理解學科內容,也能引起他們的反饋參與。教師可以利用教學中范例的分析過程幫助學生提升反饋素養(Zhang et al., 2020)。
(四)開展有效教學對話應成為發展學生反饋素養的常態模式
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反饋是通過對話發展學生自主監控、評價和調控的能力。隨著研究的推進,以學與教的對話式反饋逐步占據中心地位。專家和學生一起討論有助于促進學生的積極反思和反饋,進而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這一過程也會對學生學習體驗產生積極影響,并支持反饋投入和反饋素養的發展,提升與反饋相關的學業成績。學生參與任務的動機和完成任務的信心也會因反饋而得到加強,反饋滿意度得到提升。
最早探索教學對話促進反饋發展的模型是由博蒙特等(Beaumont et al.,2011)提出的“對話前饋評估環(Dialogic feed-forward assessment cycle)”。這一模型后來得到修訂和發展(見圖7)(Ajjawi & Boud, 2017)。該模型由外環和內環組成,外環由三個內環推動而成。三個內環分別為:1)準備指導環(preparatory guidance),包含校準解釋、任務討論;2)任務指導環(in-task guidance),包含模型解答、通用反饋、同伴評價;3)績效反饋環(performance feedback),包含草稿圖和討論、語音反饋、案例、形成性和及時性反饋等。三者之間依次又形成大的閉環。在這一過程中,師生之間啟動準備指導環節后,通過任務指導環節提交任務,并在績效反饋環進行評價反饋,然后繼續開展前饋(feedforword)。交互分析對于理解人與人、人與物的活動和互動非常重要,其前提是人工制品和技術構成了社會場域。這種分析對話反饋的系統方法有助于維持反饋對話的交互特征研究。信任是成就對話反饋的重要因素(Winstone & Carless, 2019)。教師通過推動師生對話、同伴對話、內省對話和技術支持的對話,減少反饋障礙,推動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

圖7 對話反饋評估循環
(五)技術增強機制應成為智能時代提升學生反饋素養的主要途徑
相關研究曾探討過技術促進學生參與反饋并利用反饋學習的優勢,比如,能綜合多種反饋,有助于學生便捷地獲取反饋。在線測驗、點擊器、虛擬學習環境、電子作品集、音頻反饋、視頻反饋和屏幕廣播反饋等數字化反饋是當前的主要反饋方式,從形式上優于文本方式的常規反饋,從某種程度上比單一反饋方式更受學生認可(Ryan et al., 2019)。數字化反饋也可以加入人為信息,例如教師可以使用積極的表情符號為書面在線評估反饋注入樂趣、溫暖和情感等信息,促進學生對反饋信息的接收。學生更愿意投入在線交流與反饋中(Caruso et al., 2019)。基于設計的適應性對比判斷項目對學生作出積極反饋,有助于改進過程性反饋和提升學生成績(Bartholomew et al., 2018)。大數據學習分析可以為低適應性學習者提供操作性在線學習反饋(Tempelaar, 2019)。
技術增強環境有助于幫助學習者克服特定文化背景下面對面反饋可能產生的尷尬。已有研究表明,在線反饋有助于內向型學習者突破師生面對面反饋可能遭遇的尷尬。學習者在網絡學習中通過教師在線反饋的積極信息,更好地理解教師的教學語言和教學行為,從而提高在線反饋的主動性,盡管學生看不到網絡那一端的教師到底是誰(Ding et al.,2019)。目前,利用技術增強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不多,應成為未來的主要取向。相關研究還應提升技術反饋對學生發展重要性的認識,并將學生作為技術反饋過程設計和實施的重要利益相關者。
五、研究展望
高水平的反饋能幫助學生理解自己的表現,應對未來,縮小差距,保持學習動力等。關于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國內學者還在職業學習場所、第二語言教學等領域展開了相關研究。但東西方文化差異會導致學生面對反饋產生不同表現。評價鑒定、傳遞信息的舊反饋模式正被鼓勵師生間積極互動和對話的新范式所取代。這種取代過程具有挑戰性,也值得研究。
(一)創建聚焦反饋素養發展的學習者雙角色反饋機制研究與實踐文化
中國學生反饋素養的研究多聚焦在外語寫作方面,比如研究生如何與導師進行論文寫作的對話反饋。中國文化背景下師生關系的緊張也會導致反饋處理和應對的低效,甚至把簡單問題復雜化,影響問題的解決。
未來研究應聚焦以學生為反饋信息接收者和發送者的雙重角色。前者要考慮教師、家長、同伴以及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教育機器如何提供更符合學習者特征或需求的反饋信息,如信息內容、信息方式、信息標準等;后者強調接收者的情緒變化,以及是否能夠理解這些反饋信息并決定下一步行動等。為了促進學習者的反饋,教師要聚焦如何給學習者提供認知腳手架,通過問題導入、方法導入、案例導入等促進其作為信息發送者的內在反饋生成和對外表達,從而產生有效的反饋循環。學生自主發展不僅要主動獲取信息,開展學習,更應該在互動中感知信息、理解信息、組織信息和反饋信息。關注學生反饋、探索如何從課程設計與實施中開展促進學生反饋素養發展的辦法,應該成為關注學生自主學習和持續發展研究的新文化。當前,強調研學旅行、跨學科學習等實踐模式有助于促進學生習得反饋素養。已有相關研究將成為本土化探究與構建新模型之路的分析起點。
(二)構建我國學生反饋素養的特征模型
學生的反饋素養影響學生對反饋的感知、利用反饋參與學習以及對反饋進行再反饋。了解學生的反饋素養特征,全面把握學生反饋素養的表現水平,為教學提供了模塊干預設計的依據。全方位調研可以構建不同區域、不同學段的學生反饋素養特征模型,開發有效的測評工具,診斷學習者反饋素養,為教師開展教學提供參考。
學生反饋素養不僅受個體的影響,學校、家庭以及社會情境也會對之產生影響。選擇上述成熟的模型開展不同視角的深度研究,可從成功促成和障礙要素著手(Garino, 2019),也可從時間要素分析(Nash et al., 2018)。面向未來的反饋通常比面向過去的反饋更有價值,評估性反饋比指導性反饋更容易讓人記住,反饋語言自身也會對反饋產生影響。反饋所用的日常單詞或短語的差異,意味著學生個體學習經歷和體驗的差異,從而帶來不同的概念理解。若不能正確解釋接收到的反饋語言,就很難進行有用的反饋(Jones et al., 2020)。努力程度和反饋質量也可以預測學生反饋的應用效果(Vattoy et al., 2020)。反饋素養有助于學生產生反饋求助行為,求助方法和結果也會對反饋素養發展產生潛在影響(Joughin et al., 2020)。
(三)開展融入反饋素養發展的教學干預研究
盡管學生和同伴愿意在大學第一年期間就提供和接受反饋,但同伴反饋的質量和程度往往是膚淺和表面的(Mutch et al., 2018)。支持學生反饋能力的發展難以在短期內實現,必須嵌入到課程教學中進行干預,并不斷加強。開展以有效對話為機制的教學能夠促進反饋素養的發展,教師對學生學習過程進行教學引導是有效開展教學對話的前提。
當前,全國教師積極響應“停課不停學”號召而開展超大規模的線上教學(黃榮懷等,2020)。大多數教師能積極應對,但教師主導或提供單向反饋的教學方式仍占相當數量。缺乏對話的在線教學存在互動低效、反饋單一等不足。如果融入促進學生反饋素養發展的交互式教學設計,在線教學將不再是教師的“個人獨唱”,而變成師生共同彈奏的“在線交響”。教學對話引導學生和教師從不同角度考慮如何更有效地調動與激發學生參與反饋的能動性(Winstone et al., 2017; 何克抗, 2017a)。只有師生在教學中真正融入積極的互動反饋過程,教學對話才能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深層次意義建構。
教師為學生提供必要的反饋信息有助于構建有效的教學對話。當反饋是消極的、不可理解的、矛盾的或缺乏相關性時,反饋障礙就會發生。師生關系缺乏信任或存在分歧時,學生反饋的能動性也會受到影響。教師有意識地激發和處理反饋信息才能促進學生反饋行動的實施(Malecka et al., 2020)。教師還應改進反饋行為,提升學生的反饋滿意度(Carless, 2020)。反饋信息特征也會影響學生的反饋滿意度(Smith, 2020)。教師可以采取學生喜歡的視覺反饋取代純文本或圖片反饋,因為有事先訓練和雙循環反饋過程的長期干預比沒有面對面訓練和單循環反饋過程的短期經驗更受用(Mercader et al., 2020)。
設計學生反饋素養的教學干預要兼顧學科特點,嵌入具體學科的實踐才是真實反饋(Dawson et al.,2020)。英國某大學28年間對五大學科課程群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數字化反饋質量的感知與期望因學科群而異(Elshaer et al., 2020)。嵌入提升學生反饋素養的教學環節,能促進學生在課程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投入和發出反饋,參與的過程會將他們的思維逐步引導到面向設計的產生式學習發展過程中(董艷等, 2019),學生可以進入積極的自主發展學習過程。因此,反饋改進不應只關注如何調整教師的行為,還應促進學生成為反饋的發起方,成為未來工作場所中的對話主導者(Noble et al., 2020)。
(四)開展基于人工智能的人機互惠雙反饋模型探究
計算機發揮教學人員功能,充當代理角色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的智能教學系統(Instructional Tutorial System,ITS)。這種教學系統能利用大數據對學生學習進行精準評測,分析學生學情,反饋總體教學效果(邢西深,2020)。智能系統提供反饋優化了教學環境,構建了深度學習的虛擬空間,減輕了教師負擔,促使學生與周圍互動從而實現自主學習。在最初的研究中,人與人的反饋方式為人類對計算機媒體類的反饋研究提供了參考(何克抗, 2017b)。
隨著教育人工智能的發展,技術支持下的教學反饋已經從機械化反饋發展到個性化、適應性反饋。人工智能逐漸開始扮演教師的多樣化角色,如個性化智能教學的指導顧問、學生個性化問題解決的智能導師等(余勝泉, 2018)。重視人工智能下包含反饋的學習發生機制的研究,促進人工智能從外置性技術輔助走向內融性技術滲透(郭炯等, 2020),已成為信息技術領域的發展訴求。教育機器人能否以診斷學生信息為基礎,提供個性化反饋,通過設計融認知、行為、情緒等綜合診斷的能動性反饋干預模型,浸潤式地激發學生反饋素養的發展,促進師生反饋素養聯動發展,形成人機互惠的雙向反饋模型,可以拭目以待。
當學生們敢于喊出“這不是我們需要的反饋”(Pitt et al., 2016)成為改變已有反饋研究與實踐文化的開始,“請您聽我說”也成為學生們積極參與主動反饋交互過程的開端,這些也必將成為學生利用周圍多來源信息進行自我意義建構和表達反饋成效的開始。臺灣知名教育學者蔡今中教授曾在訪談中提到“每位研究者要認識到自己的個人特質,敢于探索未知,但也要挑戰已知”(翟雪松等,2017)。學習者可以先從挑戰已知開始,克服對學問或學術的最初恐懼,在與導師或前輩的互動交流中,在與文獻進行心靈溝通的過程中,了解自己的特質,并提升反饋的信心和力量,積累發展自己探索未知的勇氣和魄力。為促進學習者盡早掌握反饋這一有效工具,我國應盡快從聚焦學生個體反饋素養雙角色發展的研究與實踐文化、教學干預機制、學生現狀調研與特征模型構建以及人機協同反饋互惠模型的探索等層面入手,創建面向學生自主發展、師生協同進階的、認知-情感-行為多維均衡促進、融入技術支持的多層次反饋育人體系,明晰我國學生反饋素養本土化的內涵和影響要素,促進學生內生動力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