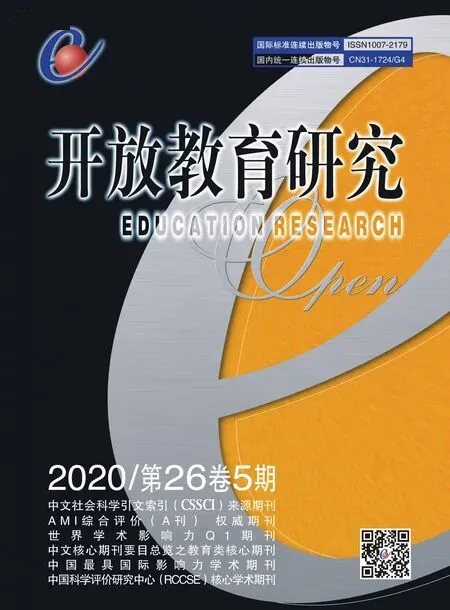技術賦能的韌性教育系統(tǒng):后疫情教育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新路向
祝智庭 彭紅超
(華東師范大學 開放教育學院,上海 200062)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世界各國和地區(qū)被迫暫時關閉學校。根據(jù)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統(tǒng)計,截至4月初,全國性關閉學校的國家有194個,受影響學生近16億(UNESCO, 2020)。
期間,在線教學擔起了課程學習的重任,但仍有大量學生無法接受教育。聯(lián)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報告顯示,全球無法進行在線學習的學生數(shù)量至少有5億,其中絕大多數(shù)由無法訪問網(wǎng)絡所致:全球?qū)⒔?7%的學生無法上網(wǎng)(GEM Report, 2020)。根據(jù)2020年4月發(fā)布的《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僅為64.5%(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信息中心, 2020),這里面還包括信號不穩(wěn)定、網(wǎng)速低下的網(wǎng)民。
學校關閉導致學生接受教育的基本公平受到損害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教育系統(tǒng)的脆弱性。對此,本研究團隊在探析教育系統(tǒng)的韌性內(nèi)涵及其能力圖譜的基礎上,解析教育系統(tǒng)數(shù)字化,不同韌性程度的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性能變化,及增強其韌性的系統(tǒng)性策略,并探究后疫情時期,教育信息化建設的新路向以及教育系統(tǒng)發(fā)展成為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短期、中期、長期建設規(guī)劃。相信文章觀點能對教育技術理論和實踐人員有所啟發(fā)。
一、 教育系統(tǒng)韌性的內(nèi)涵
(一) 韌性的內(nèi)涵與能力
漢語詞典中,“韌”與“脆”相對,指柔軟又結(jié)實。“韌性”指物體受外力作用時,雖然變形但不易折斷破裂的性質(zhì),也指人頑強持久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漢典, 2020)。作為物理學概念,“韌性”一般指材料在斷裂前吸收能量或塑性變形的能力,吸收的能量來自于外在沖擊,可以界定為消納能力。塑性變形不同于脆性斷裂,是為了維持原有功能特性而改變自我的能力,這種能力可以界定為適調(diào)能力。
可以發(fā)現(xiàn),物理學概念的消納能力即是漢語詞典中“結(jié)實”的表現(xiàn),適調(diào)能力即是“柔軟”的表現(xiàn)。此外,教育領域還有一種更為高階的韌性——變革能力,這種改變自我的能力不僅僅維持原有教育系統(tǒng)的功能特性,更多的是生成新的抗壓特性。
消納、適調(diào)、變革三種韌性能力與經(jīng)合組織(OECD,2017)和美國國際開發(fā)署(USAID,2019)界定的三種韌性能力基本吻合,它們分別是吸收與應對能力(absorptive coping capacity)、適應性能力(adaptive capacity)、變革性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y)。消納能力是教育系統(tǒng)的堅守能力,體現(xiàn)的是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主要通過啟動預防措施或者制定應急預案,緩解甚至規(guī)避外在沖擊或應激源的負面影響。疫情期間,各國學校暫時關閉,改用在線教學,即是消納韌性能力的體現(xiàn)。適調(diào)能力是教育系統(tǒng)的增量式調(diào)整能力,體現(xiàn)的是系統(tǒng)的靈活性,主要根據(jù)社會、經(jīng)濟、環(huán)境的變化調(diào)整、修改或變換其特性或行為,確保系統(tǒng)的功能和結(jié)構不會質(zhì)變,能夠持續(xù)正常運行。變革能力是教育系統(tǒng)的革命性回應能力,體現(xiàn)的是系統(tǒng)的變更性,主要通過革新、轉(zhuǎn)型等措施創(chuàng)造更加完善的系統(tǒng),使其不再受沖擊或應激源的干擾(見圖1)。可以看出,這三種能力指明了增強教育系統(tǒng)韌性的三個方向,它們的變化強度和轉(zhuǎn)型成本也是逐級上升的。

圖1 教育系統(tǒng)的韌性能力圖譜[修改自 (Béné et al., 2012)]
基于上述認識,本研究團隊將教育系統(tǒng)的韌性界定為教育系統(tǒng)通過消納、適調(diào)、變革消減、規(guī)避外在沖擊或應激源,或在受壓下依然正常運轉(zhuǎn)甚至更加完善的能力。
(二) 增強韌性的生態(tài)觀
教育系統(tǒng)應是個開放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外接社會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內(nèi)含教育機構生態(tài)、教師教學生態(tài)和學生學習生態(tài)。事實證明,增強教育生態(tài)各層面的韌性是明智之舉。新冠肺炎疫情伊始,我國教育部迅速組織智庫團和社會力量,分別從學生、教師、家庭、學校、教育局等層面制定應急預案,成功地緩解了疫情帶來的影響。
這種增強韌性的生態(tài)觀也是世界各國與地區(qū)以及國際組織機構增強韌性的思路。美國政府強調(diào)要加強教育跨部門合作,并考慮交通、基礎設施、社會規(guī)范等的影響(U.S. Government, 2018),強調(diào)關注學習者、學校、社區(qū)、機構四個層面,并將增強消納等三種韌性能力分擔到各個層面(USAID, 2019)。歐盟委員會在整個生態(tài)—社會、經(jīng)濟、政治體系內(nèi)分析韌性,并從個人、社區(qū)、機構、區(qū)域及資本所有者等行為主體間的作用和交互角度,增強韌性(Rita et al., 2017)。同樣,經(jīng)合組織也關注多層系統(tǒng)——學生/個人、學校/工廠、教育與培訓系統(tǒng)、社會文化系統(tǒng),構建了多層面韌性框架引導制定增強韌性的政策(OECD, 2019),設計了相應的分析概念框架指導韌性水平的分析(OECD, 2017)。
增強韌性,需要各個層級具備不同的特性或反應(Mitchell, 2013)。這不僅包括教育系統(tǒng)的人員、家校和體制層面,也涉及社會文化層面,如企事業(yè)單位提供臨時崗位,緩解疫情造成的無法順利就業(yè)的難題,且需要促使消納、適調(diào)、變革三種韌性能力相互協(xié)同和補充(Béné et al., 2012)。消納響應速度快,無需教育系統(tǒng)作出過多的改變,在面臨沖擊或應激源時,常常是應急預案的首選,但這并非說增強三種韌性能力必須按照預定的時間順序。從生態(tài)系統(tǒng)角度看,我們要盡早確定和規(guī)劃增強這三種能力的方案,它們是相互增益的。當然,這也要視干擾(如沖擊)強度而定。干擾強度低時,教育系統(tǒng)往往能夠消納不良影響;超出消納能力,教育系統(tǒng)便需要逐步增量式調(diào)整自身(適調(diào)),甚至出現(xiàn)變革局面(變革)(見圖2)。教育系統(tǒng)變革雖然難度較大、短期內(nèi)無明顯效益(USAID, 2019),但它為更好地應對未來類似沖擊提供了機會(Rutter, 2012)。

圖2 增強教育系統(tǒng)韌性的生態(tài)框架
二、 增強教育系統(tǒng)韌性的路徑: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
全球新冠疫情警示我們,要用技術提供教育服務(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a),這種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是增強教育系統(tǒng)韌性行之有效的思路與取向。經(jīng)過此次疫情,這已成為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
(一) 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韌性曲線
從技術增強學習的角度看,教育系統(tǒng)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經(jīng)歷了桌面軟件增強的線下系統(tǒng)、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基礎的虛擬系統(tǒng)、以云架構為基礎的數(shù)字生態(tài)系統(tǒng)、智能技術賦能的智慧生態(tài)系統(tǒng)。范圍從獨立的線下課堂擴展到線上空間,再擴展到整個教育系統(tǒng)甚至外部的社會文化系統(tǒng)。本質(zhì)上,它們都是綜合計算、網(wǎng)絡和物理環(huán)境的網(wǎng)信-物理系統(tǒng)(cyber-physical system,CPS),其韌性可用圖3表征(Klingensmith & Madni, 2018)。
具體講,有韌性的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受沖擊前后,性能變化曲線形似盆狀。未受沖擊期間,能保持對環(huán)境感知,提前做好受沖擊的準備。諸如氣候變化等慢性沖擊往往具有周期性,容易預見和提前準備,但類似此次疫情等急性沖擊,不可預見且破壞性影響大(Juan-García et al., 2017)。遭受急性沖擊的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應能夠抵抗并承受這種破壞,受損時,也能夠維持運行(Goerger et al., 2014)。同時,靈活的系統(tǒng)能夠動態(tài)調(diào)整其架構、組成成分或行為(很多時候需要人為助力),促使系統(tǒng)達到最小性能閾值前恢復功能。一般情況下,系統(tǒng)的功能能恢復至初始水平,即復原(bounce back)。如果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本身具有良好的學習能力,在外在環(huán)境改善后,性能會變得更好(bounce better)(見圖3)。

圖3 韌性系統(tǒng)的盆狀曲線
除了恢復如初或變得更好,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需要前向反彈式發(fā)展(bounce forword),以應對未來的沖擊或壓力。教育系統(tǒng)的重塑與變革僅靠自我成長遠遠不夠,還需要人為的介入與改造,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在線系統(tǒng)直播、課堂管理功能的上線;后疫情時期,高等教育系統(tǒng)大興遠程學習、強化虛擬學習體驗的變革(Frankfurt, 2020)等。
(二) 增強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韌性的策略
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是開放的,增強其韌性需要兼顧系統(tǒng)內(nèi)外各種因素。這方面,莫里斯等 (Morisse & Prigge, 2017)構建的韌性屋模型提供了制定系統(tǒng)性策略的方向,即從理解外部環(huán)境、理解系統(tǒng)本身兩大基礎性因素和人員、流程、技術、信息四大支持性因素入手(見圖4)。

圖4 增強韌性的系統(tǒng)性策略
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受到的沖擊或干擾,主要來自外部環(huán)境。因此,增強韌性首先需要理解外部環(huán)境,包括處境感知和沖擊預警。前者感知當前處境和未來處境的變化,辨別系統(tǒng)是否會受到?jīng)_擊或干擾;后者及時向教育工作者、學生、家長發(fā)送通知,幫助他們了解面臨的威脅或問題。這兩方面對于教育工作者及時作出決策至關重要。要實現(xiàn)變革,還需理解系統(tǒng)本身,包括文化價值觀、教育環(huán)境、體系架構和模塊的相互依賴關系。文化價值觀審視教育文化與價值觀是否與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吻合。教育環(huán)境判定線下、線上或混合環(huán)境能否提供連貫、沉浸的學習空間。體系架構確定系統(tǒng)是否靈活、可變。模塊的相互依賴性主要明確各模塊間的獨立性,決定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哪些模塊可以單獨革新。
增強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韌性涉及學生、教師、家長和其他管理者,主要是他們的教育培訓與引導支持。教育培訓旨在增強相關人員的風控意識、領導與管理能力,發(fā)展專業(yè)才能。引導支持旨在引導相關人員規(guī)避和應對傷害,在沖擊下如何持續(xù)提供教育服務,必要時應該給予專家、經(jīng)濟等的支持。增強韌性往往伴隨教學系統(tǒng)、教務系統(tǒng)以及服務系統(tǒng)等的流程變化。教學系統(tǒng)的流程向支持泛在化的無縫學習轉(zhuǎn)變,教務系統(tǒng)的流程向支持彈性教學與柔性學習轉(zhuǎn)變,服務系統(tǒng)的流程向關注學生情感、品性轉(zhuǎn)變。技術是增強系統(tǒng)韌性強有力的支持因素,這主要關注過程監(jiān)控、網(wǎng)絡安全、基礎設施的加強與改善。過程監(jiān)控旨在及時發(fā)現(xiàn)教育教學的故障點,快速作出補救反應。網(wǎng)絡安全旨在通過加密協(xié)議、防火墻等保證用通信安全可靠。基礎設施旨在通過增加智能設備、通信設備提高教育教學途徑和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傳感器收集了大量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蘊含著巨大的價值。因此,增強韌性的信息因素,需要增加大數(shù)據(jù)與云計算的投資與建設,增強從數(shù)據(jù)中提煉價值的能力以及速度有加快。
三、 教育系統(tǒng)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新思路
教育信息化1.0時代,我國已實現(xiàn)了“三通兩平臺”建設與應用的快速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18)。新冠疫情初期,我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實施超大規(guī)模的在線教學與居家學習,這一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成果發(fā)揮了巨大的韌性作用。
經(jīng)歷這次全球新冠疫情,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增強教育系統(tǒng)的韌性成為后疫情及“十四五”時期,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的重要任務。新目標下,教育系統(tǒng)的數(shù)字化也將出現(xiàn)新路向:無邊界、多通道、“去中心”、分布式、自治性、自修養(yǎng)。
(一) 無邊界
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無邊界發(fā)展通過提高聯(lián)通性來增強韌性,即不僅聯(lián)通各類學習場所,也聯(lián)通系統(tǒng)外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這一方面能夠弱化異位散布式教學質(zhì)量的衰減,另一方面能夠收集更多新信息來分析系統(tǒng)內(nèi)部的變化與發(fā)展(Morisse & Prigge, 2017)。
當前的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主要關注單所學校的教育和課堂教學,具有邊界,一旦學校因自然災害等沖擊無法開學,學生便會面臨在家待學的困境。屆時即使緊急上馬在線學習(邊界拓展至家庭),教學質(zhì)量也會大幅衰減,因為這不是簡單的遷移問題,涉及系列變革,因為由共位集中式教學結(jié)構轉(zhuǎn)為異位散布式結(jié)構,需要長期的探索與實踐,這也將是后疫情時期,教育系統(tǒng)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主要取向。
同樣重要的是,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需要實現(xiàn)學校間的關聯(lián),特別是校內(nèi)課堂間的關聯(lián)。將學校課堂邊界打通后,學校間便能進行同步教學與同步研修,破解薄弱學校和教學點缺少師資、開不好規(guī)定課程的問題以及教師教學能力不強、專業(yè)發(fā)展水平不高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0a)。本質(zhì)上,這是通過縮小“教學鴻溝”,提升整個教育系統(tǒng)的整體韌性水平。
網(wǎng)絡通信能夠為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無邊界發(fā)展提供技術方案,其中最有潛力的是5G技術。在真實的5G網(wǎng)絡環(huán)境中,用戶能夠獲得Gb級的速率體驗(高速率),端到端的時延能夠低至毫秒級(低延時),單位平方公里的在線設備數(shù)可達百萬、總流量可達數(shù)十Tb(高密度),通信雙發(fā)的相對速度可達500km/h(高移動性)(IMT-2020 5G Promotion Group, 2020)。這樣的優(yōu)勢,可確保聯(lián)通各類學習場所間的大量數(shù)據(jù)實時通信,流暢不擁堵。加持4K/8K超清視頻技術后,這些場所可無縫連接,成一個有機整體。
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邊界越廣,越能獲得全面數(shù)據(jù),描繪系統(tǒng)的特性狀況越準確。大數(shù)據(jù)能夠提供技術支持,通過教育數(shù)據(jù)挖掘技術提取出核心指標的特征(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并以特征為依據(jù),通過學習分析技術診斷系統(tǒng)的狀況,在必要時給出恰當?shù)奶幏剑珙A警、啟動應急措施等。
(二) 多通道
多通道能保證信息通暢,即使某部分被阻斷,其他通道也能確保系統(tǒng)正常,因此,增加通道能增強韌性。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發(fā)展,遠程教育和在線教學已日趨成熟,并呈現(xiàn)出線上線下相融合的取向。在這樣的架構下,學生能隨時隨地快捷地切換學習方式且能夠維持學習的連貫性。
然而,我國家庭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目前僅64.5%,遠遠無法提供同等于學校的教育機會,這一點,疫情期間已得到證實。同樣被證實的是網(wǎng)絡擁堵會降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和體驗。鑒于此,在線下通道和互聯(lián)網(wǎng)通道的基礎上融入廣播電視網(wǎng)和電信網(wǎng)通道是增強韌性的快捷途徑。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統(tǒng)計公報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 2020),截至2019年底,全國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為99.13%、電視覆蓋率為99.39%,基于電信專網(wǎng)的交互式網(wǎng)絡電視(IPTV)也有2.74億用戶。如果合理優(yōu)化配置,教育數(shù)字化系統(tǒng)的覆蓋率將大幅提升且極大緩解互聯(lián)網(wǎng)的壓力,且能夠保證貧困地區(qū)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權利。
除了增加信息傳輸通道,增加感控通道也可增強韌性。特別是5G應用后,上述四大優(yōu)勢為物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萬物相連更加穩(wěn)定、快速(吳位強, 2019),遠程控制更加精準。5G支持的物聯(lián)網(wǎng)(Internet of Things,IoT)技術,連通異地教學設備、學具、實驗儀器等資源,能帶給學生流暢的學習體驗。這種物聯(lián)感控通道打破了物理資源使用的地域局限,允許無法到校的學生依然能夠使用學校設備。若在物聯(lián)感控通道上加持XR技術,包括虛擬現(xiàn)實VR、混合現(xiàn)實MR、增強現(xiàn)實AR及觸感技術(Brown et al., 2020),學生還能夠獲得臨場感與沉浸感。
(三) “去中心”
信息通道、感控通道通過多樣性增強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韌性,并將教育系統(tǒng)的人員、設備、資料、環(huán)境等通過網(wǎng)絡互聯(lián)互通。這帶給學生更多學習機會的同時,也加大了教育系統(tǒng)遭受沖擊的隱患。“去中心化”可以模糊教育系統(tǒng)的中樞,通過降低中樞成為“靶心”的可能來增強系統(tǒng)的韌性。
本研究團隊一貫主張“技術促變教育而非引領教育”(祝智庭, 彭紅超等, 2018),教育系統(tǒng)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需要相關部門的決策與引導,不能完全“市場化”,因此教育系統(tǒng)的去中心化變革是一種隱喻,并非取締中心機構,這里用引號注明這一點。
借助網(wǎng)絡思想,加強移動性和冗余性成為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去中心”的主要途徑。移動性旨在增強關鍵部門和機構的移動辦公能力,降低對固定物理場所的依賴。采用創(chuàng)傷小、易復原、增量式的微變革是較為明智的舉措。冗余性旨在借助數(shù)字優(yōu)勢,將教育系統(tǒng)的資源副本存儲在多地。這樣即使某些副本遭到破獲或篡改,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功能和結(jié)構也不會受到影響。數(shù)據(jù)多地存儲帶來的問題是有效數(shù)據(jù)的共識問題與隱私保護。這方面,新興技術區(qū)塊鏈能夠提供解決方案。區(qū)塊鏈通過共識機制集體維護各數(shù)據(jù)副本一致性(Muhammad et al., 2019)、通過哈希鏈連接各數(shù)據(jù)副本的去中心化技術方案,具有數(shù)據(jù)不可偽造、記錄可溯源的高可信度優(yōu)勢(Underwood, 2016)。區(qū)塊鏈安全性的突出表現(xiàn),讓學者相信它能夠?qū)崿F(xiàn)信息互聯(lián)向價值互聯(lián)的變遷(Tapscott et al., 2016)。
(四) 分布式

進一步來說,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可由單機系統(tǒng)架構轉(zhuǎn)型為分布式生態(tài)系統(tǒng)架構,通過緩解系統(tǒng)中樞的工作量和提高系統(tǒng)壓力測試極限來增強系統(tǒng)的韌性。分布式生態(tài)系統(tǒng)架構的每個子系統(tǒng)都會得到一定權限處理一些事務,只將處理結(jié)果反饋給中樞,這樣既可以充分利用整個系統(tǒng)的基礎設施資源,又能極大降低主干網(wǎng)的通信量。
實現(xiàn)系統(tǒng)架構的轉(zhuǎn)型,需要攻克兩個難題:1)如何搭建高度靈活與兼容的分布式架構;2)如何關聯(lián)已有的“信息孤島”,包括聯(lián)通方式與動機機制。對于后者,本研究團隊早期提出的數(shù)據(jù)松耦合的聯(lián)通思路和“企業(yè)數(shù)據(jù)換市場、教育部門市場換數(shù)據(jù)”的思路(祝智庭等, 2017a)能夠提供工作導向。
(五) 自治性
受壓力沖擊,各分布式教育子系統(tǒng)間的通信可能會被阻斷,被阻斷的子系統(tǒng)需要具備自治能力來維持教育服務功能。這種反映魯棒性(robustness)的韌性主要分兩個方面:第一,局域范圍內(nèi)的教育系統(tǒng)依然能夠提供服務;第二,局域教育系統(tǒng)內(nèi)的通信遭到阻斷,學生的個人學習終端依然能夠提供服務。
對于第一方面,霧計算(fog computing)和邊計算(edge computing)能夠提供技術方案。這兩種技術均是將計算由數(shù)據(jù)中心(如網(wǎng)絡云中心)向數(shù)據(jù)源頭(或用戶)貼近的技術,其中霧計算專注于讓數(shù)據(jù)中心至數(shù)據(jù)源頭之間的網(wǎng)絡能夠提供計算、存儲等服務,這樣網(wǎng)絡便可以成為數(shù)據(jù)處理的“流水線”,而不僅是“數(shù)據(jù)管道”(趙梓銘等, 2018)。邊計算直接專注于更貼近設備(或傳感器)的網(wǎng)絡邊緣(Satyanarayanan, 2017),把相互獨立、分散在用戶周圍的資源統(tǒng)一起來提供計算、存儲等服務。
對于第二方面,人工智能能夠提供技術方案。當前,人工智能與教師的協(xié)同是教育信息化發(fā)展的主流趨勢(祝智庭等, 2018; 余勝泉等, 2019),這種協(xié)同能夠發(fā)揮人機的各自優(yōu)勢(彭紅超等, 2018),助力實現(xiàn)規(guī)模化的個性化學習。但在網(wǎng)絡完全被阻斷的情況下,人機協(xié)同不再起作用,教育系統(tǒng)的自治水平將取決于學習終端自身的智能水平。從這個角度看,教育領域的強人工智能發(fā)展與弱人工智能發(fā)展同樣重要。目前,手機、平板、筆記本等終端均已具有一定算力,能夠支持智能應用程序的運行,諸如自然交互與適性推薦等智能服務也已成為常態(tài)。不過,智能終端助教或?qū)W伴終究無法具備足夠的教學智慧,因此,此類自治一般只能作為教育系統(tǒng)恢復功能爭取時間的權宜之計,即使安裝應用程序后,終端具有了自我學習的本領,甚至具備了認知智能。
(六) 自修養(yǎng)
人員的韌性特別是數(shù)字韌性是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終極韌性。這種韌性表現(xiàn)為學生、教師和管理者的自修養(yǎng):無論經(jīng)受了什么外部沖擊,即使在社會或技術系統(tǒng)遭遇破壞的情況下,個體也能夠保持耐受性、抗壓性,維持積極的心理狀態(tài),并能借助不同條件的支持利用適當?shù)臄?shù)字化工具,不斷地學習與提升,逐步適應已變化的外部環(huán)境,甚至催生外部環(huán)境持續(xù)發(fā)生改變(祝智庭,沈書生, 2020)。作為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的核心,人員應比任何技術或生態(tài)系統(tǒng)有更強的數(shù)字韌性。
研究表明,韌性可以通過學校教育提升(Seligman et al., 2009),并且這種讓學生在腦中形成韌性的方式,比技術武裝更有價值(Telenor Group, 2013)。具體講,我們可以研發(fā)韌性教育課程并將韌性教育納入教育或培訓體系中(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b)。目前,國際上已出現(xiàn)了一些范例可供參考。例如,漢森(Sven Hansen)創(chuàng)辦的韌性研究院關注韌性的測量、學習與跟蹤,開發(fā)了50多個在線學習微視頻,從快速復原、全人成長、人機聯(lián)絡、心流體驗四方面培養(yǎng)韌性能力(The Resilience Institute, 2020)。
韌性教育超越了簡單的記憶與計算,注重互動與參與,并且,相比用紀律和懲罰管控問題行為,側(cè)重發(fā)揮學生長處的同時提升幸福感的教育更加有效(Cahill et al., 2020)。根據(jù)瑞維奇(Reivich,2010)的研究,從以下七個方面入手更容易實現(xiàn)韌性教育培育目標:情緒感知與控制(emotion awareness and control)、沖動控制(impulse control)、合乎現(xiàn)實的樂觀(realistic optimism)、靈活變通的思維(flexible thinking)、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同理共情(empathy)、勇于接觸社會(reaching out)。
四、 技術賦能韌性教育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方案
按照教育信息化發(fā)展規(guī)律,技術支持的韌性教育生態(tài)系統(tǒng)依次會經(jīng)歷三個階段:從無到有的萌生與起步階段、從有到優(yōu)的示范推進階段、規(guī)范化與制度化的全面普及階段。第一階段側(cè)重頂層設計;第二階段側(cè)重技術與教育深度融合與創(chuàng)新;第三階段側(cè)重規(guī)模化應用。此次新冠疫情強行打破這一規(guī)律。國家為保證學校“停課不停學”,超大規(guī)模地實施了在線教學與居家學習。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應在確保前期勝利果實的前提下,開展創(chuàng)新行動。在此原則下,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短期、中期、長期建設規(guī)劃可分別側(cè)重OMO教育生態(tài)、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智慧教育生態(tài)。
(一) OMO教育生態(tài)
OMO是Online Merge Offline的簡稱,即線上線下融合。疫情期間的在線教學與后疫情時期的課堂教學之間的銜接是OMO教育生態(tài)建設的當務之急,特別是在特殊省市的學生依然無法返校的情況下。對此,使用在線會議平臺和直播平臺可快速搭建簡易的OMO系統(tǒng)。具體講,在線會議平臺作為師生與異地學生聚集的主要場所,教師在教室中既可以與眼前學生交流,也可以與線上學生互動。直播平臺直播課堂場景,可向本單位或社會學生開放,可用于領導或管理者監(jiān)督指導,也可用于家長交流討論,后兩者是實現(xiàn)管理融通、家校聯(lián)通的簡易措施。如果教室具有智能錄播系統(tǒng),學生將能看到教室的多個場景,增加臨場感。
新冠疫情前,線上空間與線下空間屬于淺融合,線下空間處主體地位,線上空間主要職責為分流,流通方向是線上帶動線下的單向流通。疫情期間,線上空間具備了教學功能,線上線下的融合轉(zhuǎn)為有機整合的一體化“雙店”形態(tài),二者互聯(lián)、互通、互增值(雙向流通)。完成上面緊急銜接任務后,OMO教育生態(tài)可逐步弱化線上空間與線下空間的邊界——設備界面。這需要感知智能技術、AR/MR/VR技術及可穿戴設備的賦能。感知技術賦能人機自然對話,識別師生的肢體語言,如舉手發(fā)言等。另外,市面上的感壓板還能感知學生的筆記,分析學生的認知模式。AR/MR/VR技術支持的可穿戴設備能賦能不同程度的線上線下空間的融通:借助AR技術用數(shù)字對線下空間做“注解”;借助MR技術將線上空間與線下空間融合,其逼真程度能夠達到學生無法分清身處哪個空間的效果;借助VR技術擴展新的虛擬世界,誘發(fā)學生的心理體驗(Czikszentmihalyi, 1990)。
除環(huán)境生態(tài)建設,它還需要構建教學生態(tài)。按照華東師范大學閆寒冰教授的觀點,OMO教育本質(zhì)上是同步與異步兩種教學方式的融合。以此兩類教學方式外加學習環(huán)境(線上、線下)為橫縱軸構成坐標系,按照各象限的特點構建教學生態(tài)是可行的。
(二) 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
沒有任何媒體是萬能的,且特殊群體(如有試聽障礙的學生)對媒體亦有特殊需求。對此,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期建設可以側(cè)重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以便容納廣泛的適齡公民接受教育。
1. 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理念與現(xiàn)狀
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的宗旨是將信息用盡量多的媒體表征、媒介形態(tài)承載、通道傳播、終端同步或異步接收,以確保任何人在任何時間與地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獲到想要的信息,即滿足不同學生的細分需求(陳東毅等, 2014)。當然,使用原則是在教育需求和成本的權衡下,做到投入最小——傳播最優(yōu)——效果最大的目標(祝智庭, 彭紅超, 2020)。
經(jīng)過此次疫情,國家和地區(qū)的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已初見端倪。在國家層面,教育部部署了中小學網(wǎng)絡云平臺、北京等省市網(wǎng)絡平臺以及中國教育電視臺四頻道,多通道地傳播教育信息,確保師生能夠通過電腦、平板、手機、電視等終端開展教與學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等, 2020)。在地區(qū)層面,上海、江西較為典型。它們使用有線電視和IPTV直播教學內(nèi)容,并事后在網(wǎng)絡平臺上補充教學資源,供學生學習或下載。上海市甚至為中小學每個年級開通一個頻道,教材也有紙質(zhì)和電子兩個版本供選擇。
當前,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遠遠不夠完備:媒體表征沒有注重動態(tài)轉(zhuǎn)換,各媒體形態(tài)的資源不成體系,廣播電視網(wǎng)與電信網(wǎng)沒有得到充足利用,多終端設備間難以無縫切換。這些將是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期建設的工作方向。
2. 全媒體教育生態(tài)建設策略
信息常用圖、文、聲、像等表征。 目前這些媒體的融合,主要以促進認知為導向,而基本的可訪問性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這對于14.42萬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20b)異常重要。由此,媒體表征的動態(tài)轉(zhuǎn)換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特別是語音識別技術實現(xiàn)語音轉(zhuǎn)文字(包括盲文)、文字轉(zhuǎn)語音、視頻生成字幕(包括盲文)等的自動化轉(zhuǎn)換,以加強各類群體的可訪問性。慶幸的是,這些技術已經(jīng)基本成熟,并且能夠?qū)⒍嗝襟w轉(zhuǎn)換成盲文的平板,如BLITAB(Tsvetanova et al., 2020)也已問世。
常見媒介形式有教材、報紙、網(wǎng)頁、影音等。其中,教材最成體系,其他媒介形式,雖不乏優(yōu)秀范例,但建設并不完備,這直接導致除課堂教學外,學生難有機會接受系統(tǒng)的教育。對此,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中期建設,應注重其他媒介形式的學習資源的系統(tǒng)性研發(fā),特別是短小精悍的數(shù)字化視音頻資源,因為這種資源幾乎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傳播,還可以開展生成性資源和高沉浸感資源的建設。前者將學生學習中產(chǎn)生的評論、批注筆記等整理再利用(彭紅超等, 2016),這可以延長資源的壽命,彌補資源進化中的價值折損(許哲等, 2014)。后者利用XR技術開發(fā)新型的強交互式情境資源。
目前,廣播電視網(wǎng)與電信網(wǎng)幾乎能實現(xiàn)全民覆蓋,卻沒有充分應用于教育,原因在于學校的教育變革壓力以及普遍存在的喜新厭舊心理。對此,政府可以通過調(diào)整相應的考核評估機制以及適當?shù)囊龑訂T加以改進。
多設備的無縫切換,從系統(tǒng)架構來看,可從兩個方面入手:前端和后臺。前端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屏幕的尺寸不一導致無法兼容顯示。這一般可以采用三種方式處理:網(wǎng)頁重構(即建立與原有網(wǎng)頁內(nèi)容同等的、適合對應終端顯示的新網(wǎng)頁)、轉(zhuǎn)碼(采用轉(zhuǎn)碼技術,將原有代碼轉(zhuǎn)成目標代碼,百度即采用此技術)、網(wǎng)頁分割(將網(wǎng)頁分割成語義完整的內(nèi)容塊,然后重組成具有一定邏輯通路的子頁群)(彭紅超, 2014);第二,某些功能缺失的,可以通過開發(fā)相應的插件、軟件甚至是系統(tǒng)嘗試解決。后臺一般采用數(shù)據(jù)松耦合的方式聯(lián)通,實現(xiàn)這種耦合的關鍵是開發(fā)數(shù)據(jù)轉(zhuǎn)換工具,將不同的數(shù)據(jù)來源均轉(zhuǎn)換成目標格式。此外,實現(xiàn)多設備無縫切換最為重要的是教學設計,具體包括無縫學習情境、無縫學習過程、無縫學習體驗三方面。本研究團隊早期的研究成果《“互聯(lián)網(wǎng)+”視域下的無縫學習體驗設計》(余明華等, 2017)具有參考價值。
(三) 智慧教育生態(tài)
智慧教育追求優(yōu)化教學過程、提供個性化服務、促進美好發(fā)展,這需要長期的規(guī)劃與探索。本研究團隊主張它“永遠在路上”。智慧教育生態(tài)作為韌性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高級形態(tài),其建設可以重點關注智慧環(huán)境和智慧教學法兩個方面。
智慧環(huán)境方面,可運用數(shù)字化融合技術,構建以學為中心的、以數(shù)據(jù)流為紐帶的學習生態(tài)環(huán)境,具體可以以無縫連通學習空間、敏銳感知學習情境、自然交互學習體驗、精準適配學習服務、全程記錄學習過程、開放整合學習資源為工作導向。此外,還需注重社會文化模塊的創(chuàng)設,將智慧環(huán)境打造成教法—技術—文化系統(tǒng)(文化定導向、數(shù)據(jù)定決策、教法定行為)(祝智庭,彭紅超, 2017b)。這方面,可以從制品符號、行為方式、理念價值三個維度入手,即利用大數(shù)據(jù)技術,解析文化中的制品符號、行為方式,識別出核心的理念價值,然后教育情境化,生成教育領域的行為方式(如教與學的活動等)和制品符號(如教案、學案等)。這樣,智慧教育生態(tài)便能夠?qū)崟r根據(jù)社會文化的變化而調(diào)整(即適調(diào)韌性能力),減輕或緩解部分沖擊的負面影響。
智慧教學法方面,可本著精準決策、個性服務、優(yōu)化過程、人機協(xié)同、發(fā)展思維、注重創(chuàng)造的原則,分別構建智慧教法生態(tài)與學法生態(tài)。在這方面,本研究團隊早期提出的教法生態(tài)與學法生態(tài)可供參考(祝智庭, 彭紅超, 2017a):教法生態(tài)連續(xù)統(tǒng)的兩端分別是授導型教學和研創(chuàng)型學習模式,它根據(jù)教學條件與需要,調(diào)整模擬、問究、辯論、協(xié)作等策略的組合與比重來定位所采取模式與研創(chuàng)型模式的距離;學法生態(tài)針對基礎知識與能力、綜合應用能力、個人特長技能、群體智慧四層目標,分別側(cè)重班級差異化教學、小組合作研創(chuàng)型學習、個人自主適性學習、群體互動生成性學習四種模式,并由精準教學、創(chuàng)客教育、思維教學等思想的加持與護航。這種教學生態(tài),能夠適應大多數(shù)境域,即使教育系統(tǒng)內(nèi)部功能或外部環(huán)境遭到突變。
五、 結(jié) 語
發(fā)展韌性教育系統(tǒng),需要遵循“喜新不厭舊”的原則。當教育系統(tǒng)遭到損害時,能堅守住韌性底線、避免系統(tǒng)全面崩潰的往往是傳統(tǒng)的技術。但我們同時也要意識到,韌性教育生態(tài)的生命力在于持續(xù)創(chuàng)新。在這方面,十大技術創(chuàng)新應用將是電視教學、區(qū)塊鏈、在線測評、自步學習、人工智能、學習分析、虛擬現(xiàn)實、物聯(lián)網(wǎng)、聊天寶、實時網(wǎng)播。
著手增強教育系統(tǒng)的韌性,要事前厘清四個問題(USAID, 2020):第一,針對什么,即要明白影響教育系統(tǒng)的沖擊或壓力是什么;第二,為了誰,即利益相關者是學習者、學校、機構還是整個教育系統(tǒng);第三,通過什么,即通過增強哪些能力(如消納、適調(diào)、變革)提高韌性;第四,增韌表現(xiàn),即增強韌性后,系統(tǒng)應具有的表現(xiàn)是什么,應該達到什么標準。
借鑒數(shù)字化城市韌性建設的智慧(Colding et al., 2020),增強教育數(shù)字系統(tǒng)韌性需特別關注以下方面:第一,維持多樣性和冗余性,在提高受損程度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正常運行的可能;第二,保持連通性,特別是核心功能模塊之間的連通;第三,管控慢性變量與反饋,避免易忽視的損害因“累積效應”造成重大傷害;第四,培養(yǎng)復雜的適應性系統(tǒng)思維,便于系統(tǒng)內(nèi)人員作出明智的決策;第五,鼓勵系統(tǒng)持續(xù)“進化”,以完善未來行為并改善對挑戰(zhàn)的響應;第六,擴大參與度,讓利益相關者均參與進來;第七,促進多中心治理,通過職責分攤實現(xiàn)“去中心化”。
技術賦能的韌性教育系統(tǒng)為“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創(chuàng)造了可能,但要實現(xiàn)這一點,首要的挑戰(zhàn)是無縫學習:無論時間、地點、設備等如何變更,學生均能夠連續(xù)貫通地學習,因為有效學習必然是連貫的,特別是認知連貫。這一點可確保學生續(xù)接學習斷點,繼續(xù)進行信息加工(即“斷點續(xù)學”)。
新冠疫情給我們帶來沉痛打擊的同時,也來帶了發(fā)展機遇。抓住機遇,發(fā)展韌性教育系統(tǒng),正當時。當然,技術伴隨著風險,采用“微創(chuàng)新”的理念,積小勝為大勝才是明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