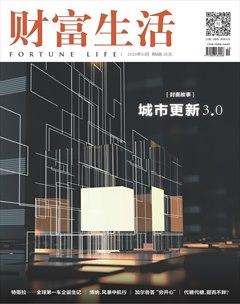新天地 VS 田子坊哪個更成功?
2-50-75-80,意大利建筑師、工程師卡洛·拉蒂教授以這樣一組數字闡釋城市更新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類——在地球上,城市只占據了地表面積的2%,卻聚集了50%的人口,進行著75%的能源消耗并排出了80%的二氧化碳。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在城市的可持續化的更新進程中做出一些小小的改變,就能夠在全球尺度上獲得顯著的效果。
包括卡洛·拉蒂在內的專家學者都認為,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中國建設的城市比人類歷史上加起來都要多。那么,城市更新的成功是否有所謂的標準存在呢?
參與過國內多個街區的藝術更新改造的英國格拉斯哥大學藝術史碩士Sasa表示,城市更新的成功“沒有絕對,只有相對”。
在她看來,城市是有生命周期的,城市更新也是動態的、螺旋上升的。對于中國而言,大多城市目前已經走出了“清除貧民窟”的1.0階段,正向 “以城市物質結構為重心”的2.0階段邁進,經濟水平發展較好的城市可能已經向“以社會、經濟、環境政策配合城市物質規劃的綜合更新”的3.0階段發展。但無論如何,都是在做城市的“再升級”。
“像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型城市,它們的城市更新改造開始得比較早,因為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所以在早期肯定會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需要在后來的城市更新中不斷去完善、補漏。像杭州、南京這樣的歷史古城,它們的現代化更新啟動相對較晚,又有了城市更新的參考對象,那么在改造過程中,它們歷史文化保留和現代發展需求間的矛盾就不如北京和上海那么鮮明。”因而,把不同時期、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之間的城規做優劣比較,似乎就顯得有些關公戰秦瓊了。
她告訴筆者,與其比較優劣,不如置身城市所屬的當下環境,從兩個角度度量:一是判斷它是否是當下最適合的改造辦法,二是判斷它在十年或者二十年后,當城市進入另一個生命周期時,這套體系是否依然能維持,也就是前瞻性。

圖/視覺中國
“就拿新天地和田子坊來說,都是大家津津樂道的項目,因為都在上海,而且都是針對石庫門建筑的改造,所以總有人拿它們做比較。有人說,新天地把住戶全部遷走了,但田子坊保留了住戶和社區的狀態,所以田子坊更好。但我覺得,不是說保留就一定好,不保留就一定不好,前者你可以說是商業成功,后者你可以說是社區復興,評判的角度不同罷了。況且任何一個項目想要做成,都是多方角力妥協后的結果。可能動遷資金太高,所以選擇不拆遷了;可能老建筑的保護等級提升了,能開發的空間變小了……這當中變數太多了,我們沒法穿越到未來,所以只能站在當下,用前瞻的眼光盡力在各種牽絆下做最優抉擇。”她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