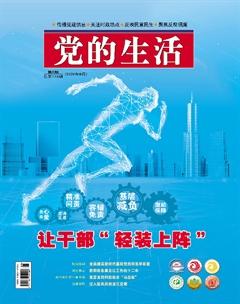嚴懲誣告陷害,為擔(dān)當(dāng)作為者澄清正名
王宇萌
“關(guān)于對雞西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科技信息科科長井緒江利用職權(quán)在為他人辦理住房公積金繳納、提取等工作時收取回扣問題的不實舉報……現(xiàn)予以澄清正名。”2020年5月21日,井緒江收到朋友轉(zhuǎn)發(fā)來的微信消息,內(nèi)容是黑龍江省紀(jì)委監(jiān)委為受到不實舉報黨員干部澄清正名的通報,其中就包括他。
“看到自己被證明清白的消息,感到非常高興,腰桿挺得更直了。我會調(diào)整自己,繼續(xù)努力工作,回饋組織對我的信任和厚愛。”井緒江被澄清正名,不僅讓他在單位重新抬起了頭,也讓他對家人有了一個交代。
2018年以來,公開為干部澄清正名,在一些地方逐漸成為一種常態(tài)。據(jù)《法制日報》報道,目前已有10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一級的紀(jì)檢監(jiān)察部門出臺為被錯告誣告黨員干部澄清正名、處置誣告陷害行為的相關(guān)規(guī)范。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正在用實際行動吹響讓干部挺直腰桿、輕裝上陣的號角。
澄清正名,給干部“卸包袱”
受到不實舉報,那是一種什么樣的體驗?
“當(dāng)時,不僅自己壓力巨大,家人得知后也跟著一起上火,岳父的視網(wǎng)膜手術(shù)恢復(fù)效果就因為此事受到影響,妻子也因此失眠,患上中度抑郁癥,14歲的孩子也表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情緒波動……”井緒江黯然回憶道。
反腐敗固然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但正如硬幣的兩面,信訪舉報在切實發(fā)揮群眾監(jiān)督作用的同時,也難免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在現(xiàn)實中,不實舉報甚至惡意舉報,讓許多勇于創(chuàng)新、干事?lián)?dāng)?shù)狞h員干部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成為壓在他們心頭的一道枷鎖。
對于不實舉報和惡意舉報,許多地方的紀(jì)委監(jiān)委部門果斷出手。2018年9月17日,中央紀(jì)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公布了山東省青島市一次性通報的七起澄清不實舉報典型案例,為受到不實舉報的黨員干部澄清正名。
“經(jīng)查,某項目控制性詳細規(guī)劃還在編制過程中,尚未供地實際使用。因此,不存在舉報中所提到的未經(jīng)招投標(biāo)直接定向指定的情況。”當(dāng)著浙江省寧波市某區(qū)委書記及其他區(qū)委常委的面,市紀(jì)委監(jiān)委紀(jì)檢監(jiān)察室同志公布了調(diào)查結(jié)果,對舉報信反映該區(qū)某位區(qū)委常委的不實問題進行了澄清。
雖然這場澄清會的規(guī)模很小,但對這位區(qū)委常委而言,分量卻重若千斤——“這是組織對我的信任,我必將秉持公心、恪盡職守、認真履職!”
2019年8月,浙江省寧波市集中對101名黨員干部進行了澄清正名,其中涉及“一把手”29人,營造了激濁揚清、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良好氛圍。
據(jù)媒體公開報道統(tǒng)計,從2018年至今,中央紀(jì)委國家監(jiān)委網(wǎng)站總計集中公布了23起澄清不實舉報或為被錯告誣告黨員干部澄清正名的典型案例,各地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集中通報的澄清不實舉報典型案例則不勝枚舉。
在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王敬波看來,各地通報不實舉報案例為黨員干部澄清正名,是一個好的發(fā)展方向,有利于落實來自社會的監(jiān)督力量,打通內(nèi)外監(jiān)督、上下監(jiān)督的“籬笆墻”。
黑龍江省雞西市紀(jì)委監(jiān)委有關(guān)負責(zé)人明確表示:“及時為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顧慮,就是要保護那些敢于負責(zé)、敢于擔(dān)當(dāng)作為的干部,給他們吃下定心丸,切實保護黨員、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
嚴格審核,還被誣者清白
為擔(dān)當(dāng)者擔(dān)當(dāng),對負責(zé)者負責(zé),是各級黨委政府發(fā)出的大力倡導(dǎo)和做出的鄭重宣示。那么,各級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該如何為受到不實舉報的干部澄清正名呢?
十九屆中央紀(jì)委三次全會明確要求,要制定紀(jì)律檢查機關(guān)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guī)則,保障黨員權(quán)利,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

2019年3月,中央辦公廳印發(fā)的《關(guān)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也指出,要制定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guī)則,保障黨員權(quán)利,及時為干部澄清正名,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
北京科技大學(xué)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認為:“制定紀(jì)律檢查機關(guān)處理檢舉控告工作規(guī)則,就是要進一步規(guī)范紀(jì)律檢查機關(guān)處理檢舉控告的工作職責(zé)、工作程序,健全相關(guān)體制機制,在發(fā)揮黨員和群眾監(jiān)督作用的同時,又保障黨員權(quán)利。”
例如,河南省紀(jì)委監(jiān)委建立常態(tài)化澄清機制,通過召開澄清會、向黨組織進行通報等方式,給廣大群眾一個明白,還被誣告者一個清白,幫助受到誣告錯告的黨員干部卸下思想包袱。
“做好澄清工作,首先要牢牢把握澄清的目的——期望能以點帶面推動形成干事創(chuàng)業(yè)的良好氛圍,所以在澄清對象的選擇上就要精準(zhǔn)。”浙江省寧波市紀(jì)委監(jiān)委相關(guān)負責(zé)人表示。
在寧波市開展集中澄清正名工作期間,該市紀(jì)委監(jiān)委在確定初選名單后,交由信訪、黨風(fēng)政風(fēng)、案管、審查調(diào)查、監(jiān)督檢查和巡察等部門進行聯(lián)審把關(guān),堅持用證據(jù)說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過,一個細節(jié)一個細節(jié)審,確保沒有明顯的澄清隱患。在此期間,市、縣兩級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先后對十余名澄清對象進行了調(diào)整更換或補充查證。
浙江省杭州市紀(jì)委監(jiān)委第三監(jiān)督檢查室主任黃勝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我們澄清的原則是實事求是,依紀(jì)依法,有一個就澄清一個。我們澄清工作是‘就事論事,這四個字非常重要。如果有人舉報你,我們調(diào)查過了,這件事不存在,我們澄清的就是不存在的這一件事,不會延伸到其他事情上去。”
嚴懲不貸,向誣告者亮劍
在為受到不實舉報的干部進行澄清正名的同時,也必須對誣告陷害者進行嚴懲。因為在反腐工作中充分發(fā)揮群眾監(jiān)督作用的同時,也有一些“居心叵測”者為了一己私利,或通過“碰瓷”反腐來鏟除“異己”,或?qū)Ω墒聯(lián)?dāng)者惡意誣告陷害。
北京大學(xué)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一些人常常利用惡意舉報,達到自己的非法目的。如果這些人得不到懲處,那么被誣陷的人便會心灰意冷。”
令人欣慰的是,從黨規(guī)黨紀(jì)到法律法規(guī),均對誣告陷害的處理做出了明確規(guī)定。在實際工作中,也讓誣告陷害者付出了應(yīng)有的代價。
比如,黑龍江省蘭西縣星火鄉(xiāng)豐崗村黨員楊潤才曾實名舉報該村一名黨員干部有關(guān)違紀(jì)問題。蘭西縣紀(jì)委監(jiān)委調(diào)查組核實情況后認定,被舉報人存在違紀(jì)行為,并給予了被舉報人相應(yīng)的紀(jì)律處分。但楊潤才認為,蘭西縣紀(jì)委監(jiān)委做出的處分過輕,是在袒護被舉報人,因此對調(diào)查組及其主管領(lǐng)導(dǎo)心生不滿。為泄私憤,楊潤才又惡意捏造調(diào)查組成員及主管領(lǐng)導(dǎo)各收受被舉報人5萬元的虛假事實,向綏化市紀(jì)委監(jiān)委舉報,嚴重損害了他人聲譽,造成不良社會影響。2020年1月,楊潤才受到開除黨籍處分。
從媒體公開報道可見,對于惡意舉報行為,各地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紛紛重拳出擊——湖南省2018年查處典型誣告類信訪舉報58起,追究28名惡意舉報人責(zé)任;2019年,黑龍江省紀(jì)委監(jiān)委對33名惡意舉報者追究責(zé)任,同時公布了對誣告者的處理決定。此外,吉林、山東、浙江、內(nèi)蒙古、新疆等地紀(jì)委監(jiān)委也出臺了相關(guān)制度,對誣告陷害行為的認定、調(diào)查程序、責(zé)任追究等方面做出嚴格細致的規(guī)定。
“這些地方的舉措充分證明,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對不實舉報和誣告陷害的高度重視,表明了紀(jì)檢監(jiān)察機關(guān)對處理不實舉報和誣告陷害具有規(guī)范化的制度要求,并且制度規(guī)定日趨完善。”在北京科技大學(xué)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看來,這些制度對保護黨員干部合法權(quán)益有重要意義,為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營造出良好氛圍。
決不放過一個違法亂紀(jì)者,也不讓一個擔(dān)當(dāng)干事者蒙冤受屈。顯然,“澄清正名”機制持續(xù)釋放的明確信號,正在為干事創(chuàng)業(yè)者營造解除后顧之憂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