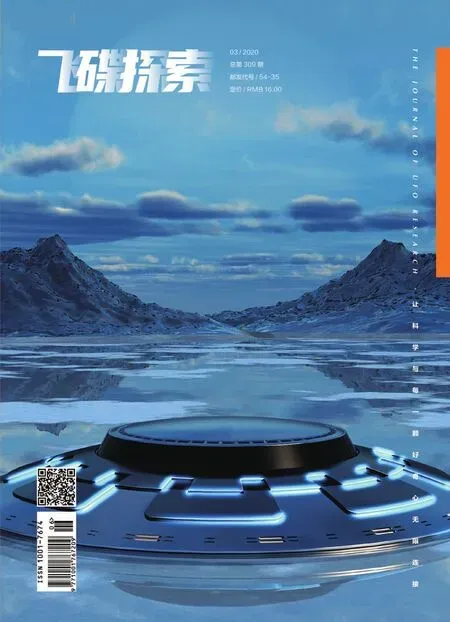『見鬼了』
文|明白知識

骷髏幻戲圖
南宋李嵩的絹本設色團扇畫,現藏于故宮博物院,是南宋風俗畫杰作

甲骨文中的“鬼”字,上部是個碩大的腦袋,下部是人,意即像人的怪物。
你相信這個世界有鬼嗎?
不相信的人,會對這種虛無縹緲的想象嗤之以鼻。但是,聲稱看見“鬼”的人還真不在少數。
相信自己遇到過“鬼”的人,經歷的遭遇事件一般都出現在某些特定場景里。比如,陰森森的黑暗里,一陣簌簌的穿堂風吹過,總有人覺得這是“鬼魂”出現了。比如親人離世時。有研究發現,在過度的悲傷中,有60%的人覺得自己“看見”或“聽見”了逝去的親人。
還有些真真假假的報告。比如,1966年,有人在英國國家海事博物館女王府的螺旋樓梯拍攝郁金香裝飾時,捕捉到了一個奇詭的黑影。又比如,1997年,有人聲稱自己的奶奶在養老院中拍照留念,照片中卻出現了已于1984年去世的爺爺的身影。
這些例子,無論是口述還是照片,其實都很難驗證。嚴謹地說,這些案例既無法被科學所驗證或證偽,又不能做實驗重現當時的結果。
那么,鬼魂到底存不存在?
“鬧鬼”的次聲波
在美國紐約市,有這樣一個奇特的人,他叫喬·尼克爾,他很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專職研究超自然現象的人。鬼魂到底存在不存在?他已經鉆研了50年,研究了數百個案例。
他研究這些超自然案例的出發點,不是為了駁斥那些常人看來神神道道的事情,而是試圖去解釋這些超自然現象發生的原因。因此,他使用了所有他能用的方法,這些方法大多來自多種學科或跨學科領域,包括語言分析、心理學分析等。
他的結論是:找不到鬼。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確定是鬼魂的案例。
當然,在科學的意義上找不到鬼,也不意味著你就不能認為自己見到“鬼”了。因為從邏輯上說,你的確可能遭遇了一些生活常態之外的異常因素。
比如,次聲波作祟。
次聲波是指頻率小于20赫茲,但是高于氣候造成的氣壓變動的聲波。次聲波的聲源包括自然現象,比如極端的地震或巨浪等,還有一些人工設施,像是風力發電機甚至風扇,都有形成低頻聲波的可能。
根據NASA的試驗,由于次聲波與人體器官的振動頻率接近甚至相同,就可能會引起人體的胸腔共振,并影響呼吸,使人產生作嘔、頭疼等反應。
而且,某些特定頻率(如19赫茲)的聲波還可能導致眼球視覺系統的共振,從而讓人們的視覺產生扭曲效果。加之這些聲波能夠移動微小的物體,讓燭光詭異地閃爍,我們便會以為自己竟然看見“鬼”了。
英國考文垂大學博士維克·坦迪在《機器中的幽靈》這篇論文中,就描述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作者曾擔任工程設計師,所在公司的業務是制造醫療設備,他們的工作間里總會有機器運轉,聽上去就像是誰在低聲喘息。而坐在旁邊的工作人員也會逐漸感到抑郁,冷得發顫,感覺自己像是被監視,模糊的視野里甚至會出現灰色的幽靈。
再想想看,當你感到似有陰風陣陣的時候,是不是常常處于幽閉而空曠的建筑長廊?這就對了,長廊是駐波非常理想的空間,當兩列傳播方向相反、振幅頻率都相同的波相疊加時,人體的共振會被加強。如果你越發感到恐懼,交感神經系統便會被激活,呼吸頻率加劇,甚至可能影響身體情況。這時我們就要注意,是次聲波這個家伙在搗鬼了。
人腦中的“鬼魂”
不過,為什么在受到外界影響后,我們會下意識地把矛頭指向“鬼”?這其中有個關鍵環節——人腦的意識作用。
美國學者邁克爾·尼斯是拉法耶特學院的心理學助理教授,他指出,人們對現象世界的體驗和感知,即自己見到和聽到的東西,來自大腦對從外界獲得的有限或不完整印象的建構。
簡單來說,大腦會對感知到的外界事物進行補充聯想。
比如昏暗房間里模糊的人形,可能是外來的客人,也可能只是一件掛在衣架上的外套。但是我們常常會主動進行建構和想象,認為那可能是鬼,并產生一種“幻想性錯覺”。

從功能上來說,前額葉皮層負責人腦的高級智力活動,是人類思想的重要物質基礎
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神經學博士奧拉夫·布蘭科有一個著名的科學實驗,他通過大腦、人體與空間的關系,在實驗中再造了一種鬼魂存在的錯覺,就解釋了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
這個實驗很簡單。蒙住被試者的雙眼雙耳,用一臺機器帶動他的雙手在身體前方做出隨意動作。在他身后,有一臺機器人,會用機械手臂輕微地觸碰他的背部,復制被試者的手部動作。
實驗剛開始,背后機器人的動作與被試者伸向身體前方的手部動作一致,并且同步運動,此時,被試者的大腦很快就適應了這種狀態。但接著,在機器人的動作與被試者的同步動作之間,引入很小一段時間延遲,神奇的事情就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在被試者身上出現了。
被試者的空間感知發生短暫的扭曲,他會感覺自己正在與某種生物互動。這種感受很容易被解讀為某種“鬼魂”,因此被試者會產生強烈的“鬼魂”存在感。有些被試者甚至感覺周圍存在著的“鬼魂”多達4個,由于恐懼,不得不要求立即停止實驗。
布蘭科解釋,這是首次在實驗室內誘發了一種外部感覺。實驗說明這種外部(奇異)感覺可以在正常環境下產生,簡單地通過相互沖突的感官運動信號即可實現。
也就是說,通過簡單的實驗手段,就可以欺騙大腦,讓大腦聯想,產生出鬼魂存在的感覺。想讓你“見鬼”就能讓你“見鬼”。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覺得見“鬼”了,可能只是我們的大腦受到了一些簡單的刺激,卻將之解讀為某種神秘的存在,結果讓我們以為見“鬼”了而恐懼不已。
我愿意“見鬼”
還有一種類型的“見鬼”,跟睡眠狀態有關。
想象一下,午夜時分,你剛進入睡眠,或者半夢半醒之際,處于有意識的狀態。但是,當你想要動彈一下身體,卻發現像是被不明物體按壓著一樣,不僅無法移動,甚至出現可怕的幻覺,比如仿佛聽到窸窸窣窣的說話聲和腳步聲,看到有怪物的暗影在房間里穿行,隨之心頭涌現出恐懼和驚慌的情緒,以為自己遇到“鬼”了。
在古代,人們將這種當時無法用常理解釋的奇異現象,稱為“鬼壓床”。而如今,我們知道,這在醫學上其實是一種被稱為“睡眠癱瘓癥”的生理現象。按照一些統計,可能有8%的人在某個特定時刻會遇到這種經歷。
這是因為,人們的意識雖然清醒過來,但支配肌肉的神經仍處于低張力狀態,由此導致了睡眠麻痹。一般來說,睡眠癱瘓癥常常會因為生活中壓力過大、作息時間不規律、失眠或焦慮等因素而產生。于是,生理現象涂抹上心理情緒,就變成了所謂的“鬼壓床”。

英國畫家亨利·富塞利創作于1791年的畫作《夢魘》
此外,還有一種心理作用,能讓我們看見“鬼魂”,那就是悲痛。當親愛的人逝去,我們可能會在過度的悲傷中,乃至往后某一天的夢里,再度“看到”逝者的音容笑貌,就好像真實發生過一樣。或者我們還可能有這樣的念頭:我相信愛人并沒有離開,他(她)的靈魂還在陪伴著我。他(她)會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好好地生活。盡管,這可能是一種幻覺下的謊言,但我們愿意接受并試著去相信。
神經學家奧利弗·薩克斯在其著作《幻覺》一書中指出,“失去、渴望、鄉愁都是強效致幻因素”,而這些都是與情感需求緊密相連的。薩克斯提到一個案例,心理分析學家馬里恩.C曾寫信說:有一天,她下班回到空曠的房子里,竟然“聽見”了亡夫保羅的聲音,那么“清晰、沉穩而且真摯,和他健康的時候一模一樣”。她也“看見”了他臉上的表情,正坐在棋桌旁迎接她歸家。
薩克斯分析到,這種看見已逝親人鬼魂的幻覺并不可怕,相反,它是哀悼過程的一部分,是一種積極的安慰力量。當一個人的身體被悲痛掏空時,這種幻覺卻可以幫助治愈內心的創傷,甚至享受在幻覺中與伴侶的對話。因此,“見鬼”,從來都不只是與恐懼相關。
死后的“鬼神世界”
可以看到,這些無論是通過外部、生理還是心理方面等因素來揭示鬼魂奧秘的科學實驗,其實都在試圖解釋產生鬼的幾種感覺源頭。科學家在這里預設了一個前提,那就是鬼魂并不存在。
只是,從文化心理層面來說,人們卻可能希冀著有那么一個“鬼神世界”的存在。
在古代中國,“鬼”往往與“神”連稱,形成了一套傳統的鬼神信仰體系。雖然其出自先民對未知領域和自然力量的敬畏之情,卻也不乏充滿想象力的浪漫色彩。
一方面,面對自然世界的變幻莫測,人類顯得渺小而無力,于是將其神秘化,認為日月山川皆有魂魄神靈。
另一方面,鬼神觀念與祖先崇拜緊密結合在一起。《禮記·祭義》有云: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在古人樸素的認知里,眾生皆有一死,死后必有歸宿,這就是“鬼”。

在《尋夢環游記》中,奇詭的“亡靈國度”被塑造成一座華麗的維多利亞式大都市
進一步說,“鬼”指新死的近祖,而“神”指本部族繁育后代的肇始遠祖,兩者合稱便泛指已逝祖先的靈魂。當先民在遭遇災害時,便會朝向天地架起祭壇,祈求先祖的魂魄能夠保佑子孫的平安。
比如偉大詩人屈原所處時代的楚文化,就充滿了“言鬼敬神”的文化習俗。每當娛“神”之時,先民飾以彩衣,饗以芳澤,樂以歌舞;而當祭奠陣亡戰士時,則長歌當哭,“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鬼神文化在古代中國人的傳統認識和民間習俗里,更多地寄托著人們對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和深情。
生命的終點
有意思的是,西方語境中也不乏對于死后世界的想象。
不過,現實世界與那個神秘的“鬼魂世界”,就是完全分隔的嗎?如果彼此間思念,情感又該怎樣訴說呢?人們想到的法子是,通過與“鬼魂”相關的特定節日,建立起兩個世界間溝通的橋梁,使生者與死者“相聚”。

墨西哥梅特佩克的亡靈節活動
比如墨西哥的“亡靈節”。每年自10月31日起,墨西哥人便會在由村莊通往墓地的路上撒上黃色的花瓣,家家門口點上南瓜燈籠,將糖骷髏、萬壽菊和螺旋狀的面包擺上祭壇,男女老幼戴上面具,穿上印有白骨的鬼怪衣服,穿過街市,歡迎亡靈循著芬芳和燈火的指引而歸來。
比起中國古人對于故人深沉的感懷,墨西哥人的傳統則充滿了狂歡色彩。經典動畫電影《尋夢環游記》的靈感便源于墨西哥的亡靈節。影片創造性地想象了一個絢爛而神秘的“亡靈異世界”。在那里,塵世肉體的離去,并不等于真正的死亡。正如影片的經典臺詞所說:“真正的死亡是世上沒有人再記得你。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終點,遺忘才是。”想來,這便是“看見鬼”于我們最真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