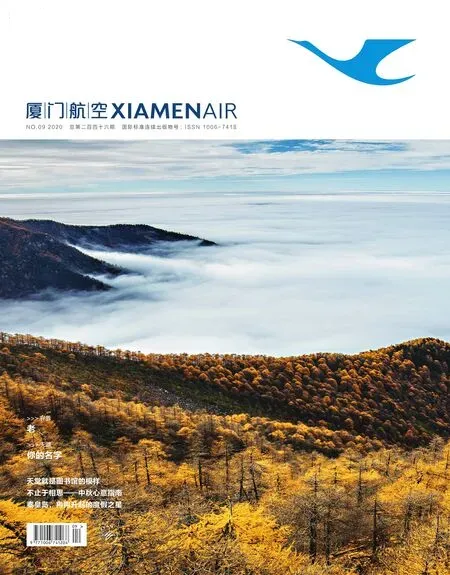去潛水,海藍時見鯨
_陳家蒂 _羅元廷

攝影_陳家蒂
我媽說,她在懷我的時候是吃了鵝蛋的,所以我天生膽子比較大,做事情比較“敢”。反正做什么事兒不帶“怕”的。
潛水、跳傘,許多人畏懼的很多新鮮事物,我都樂意嘗試,并喜歡挑戰。我的第一次潛水體驗是在什么時候呢?好像是2006年在三亞的蜈支洲島,但是具體過程卻早已印象模糊。2012年去了馬爾代夫柏悅哈達哈,只跟著小黑浮潛游了一圈海溝,只一瞬間便被水下新奇的世界驚艷。
第二次體驗潛是在2013年泰國的濤島,當時參加的PADI(國際專業潛水教練協會)項目,教練用英文教了我們半天,似懂非懂。潛水的時候有個人一直浮在水面下不去,我一開始也沒完全掌握,但后來多練習幾次之后,基本對上上下下、來來回回漸漸熟悉。
再到2019年,我們又去我國的臺灣綠島潛水,還在水下各種擺拍,寄海底明信片給各路好友。截止到這時,以上幾次潛水體驗,真的只是在體驗,或者確切地說是蜻蜓點水。直到我接觸到AE 潛水俱樂部,我才真的慢慢了解,什么叫“潛水”。
曾經在菲律賓宿務和朋友半夜暢聊,這位自己買游艇玩潛水的大哥跟我說:“潛水就是,一到水底,整個世界安靜了,壓力煩惱,全都沒有了。”
無獨有偶,上周在東山島考潛水證的前一晚,偶然遇到一位同樣酷愛潛水的大哥,在找到組織的那一刻大哥的話匣子一打開猶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地說了一大堆他喜歡潛水的理由。反正我只記住了:“一到水里,壓力煩惱全沒有了。”
所以,“潛水”可以“減壓”?到水里難道不應該是越潛壓強越大嗎?

攝影_劉大壯
而泰國PADI 體驗潛的經歷告訴我們,學潛水如果不是中文教練,可能我們真的會在那些技術性的詞匯上卡殼。
機緣巧合,我遇到了AE 潛水俱樂部,出于對自己生命負責的態度,我終于開始認認真真地學習潛水了。或許有人問為什么不是PADI而是SDI(國際水肺/技術潛水)?可能我的答案只有一個:因為PADI 沒有冬哥。不開玩笑地說,從走進OW 理論課堂的第一天起,我們首先就被冬哥教練身份的萬丈光芒所折服。同時我也需要嚴肅認真地告訴各位,世界各地的潛店是根據潛水組織(PADI/SDI/SSI/CMSA……)注冊的潛水員證件租配裝備給你,各組織之間課程體系其實都比較類似。
冬哥(陳小冬)作為國內僅有的12 個ERDI 國際應急反應潛水教練之一,也是廈門市曙光救援隊副隊長,課堂上的他講起課來是如此的生動有趣,不僅彌補了我原有的很多未知領域的新知識,還糾正了自己不少原來對潛水的錯誤認知。
比如潛水的氣瓶里裝的是空氣,不是純氧氣。冬哥說了,如果誰說氧氣瓶,那肯定是一看就沒來上過課的,或者是可以逐出師門的……
等到理論課上完,終于可以開始在泳池進行靜水練習了,這才是真正的技術實踐呢。記得那天下水前,第一個流程是準備整理。教練黃同學帶著我們領裝備,按順序裝好裝備。氣瓶很沉,BCD 很重,裝的過程細致又煩瑣。等把裝備搞定,已經1 個多小時過去了。好家伙,還沒下水呢,已經滿頭大汗。
等到冬哥上場,學跨步跳水,穿脫腳蹼、仰面踢腿這些基本動作就又把我們給累個半死……等到真正穿上BCD,握著二級頭真正跳下水,基本已經過去2 個多小時了。丟二級頭,尋回二級頭,換二級頭。按壓呼吸,噴氣呼吸,和Buddy 交換二級頭呼吸,這幾個動作似曾相識,因為在泰國PADI 體驗潛水時,教練是有講到相關內容的。但是真正潛水并沒有做練習和考試,畢竟,那只是體驗潛。真正做起來,動作倒沒有太難,就還好。真正感覺有點難度的是仰面踢腿和面鏡排水。踢腿這事,想象起來不難,但是踢起來總覺得腳蹼太沉,被冬哥數落膝蓋彎了,沒有大腿帶動小腿,如果到海里有流自己就踢不回船上。
本來下水最擔心的就是嗆水,偏偏這個環節冬哥會故意掰開你的面鏡讓它進水,逼著你排水。有的時候慌了,鼻子一吸氣,嗆水,可能會做不下去了。這一關還真是誰都幫不了你,只能自己克服心理的障礙,始終記住,嘴巴在呼吸,鼻子壓根兒就不要呼吸。始終記住排水的技巧,努力去做,最后,其實都可以完成。
潛水不僅是技術活,更是力氣活。到東山島的當晚看著身材瘦弱的師姐幫我們整理十來個裝備包的時候,我們簡直都驚到下巴掉下來了!最后師姐細心地給我們發了電腦表和手電電池,這下齊活兒。
第二天一早,大家吃好早餐陸續開始整理裝備,完全將裝備裝好,團隊流水線作業裝上車,記好BCD 或調節器的號碼(劃重點,要考!)。團隊到碼頭再卸下裝備到船上,依次排好,上船出發!

攝影_李哥

攝影_陳家蒂

攝影_李哥

攝影_李哥

攝影_李哥
從東山島冬古碼頭到兄弟嶼大約1 個多小時船程。到了以后冬哥就開始挨個兒趕鴨子下水了。這次開放水域有5 位AOW 開放水域進階考試的學員,剩下就是我們兩個OW。所以冬哥先盯AOW,黃同學和大師姐帶我們兩個OW。
跨步入水,再拉著繩子慢慢下潛。完全遵照冬哥教授的“水面安全,Buddy 在,電腦表有在,殘壓正常,水下正常,做耳壓”的流程進行。唯一發生的小波折就是,沒記住自己準備編號的兩人,把裝備穿反了。自己的裝備,自己最清楚。如果穿錯了下水,找不到自己熟悉的裝備配件,本身就會有一種“疙瘩”一樣的不順心。
水下微涼,但大腦反而清醒了。下潛過程中,開始感覺耳壓不適,立刻做耳壓,就適應了。入水適應后調節好中性浮力,跟著黃同學和大師姐開始到處溜達。黃同學見我們適應得不錯,就開始了一些小測試,比如換二級頭的呼吸。第一潛結束,我們稍事休息。第二潛冬哥先帶AOW 5 人下大深度喝可樂去。我們在船上休息等待。結果,氣瓶綁帶的穿法又折騰出我們一身汗。怎么穿氣瓶都綁不緊。怎么辦呢?一會兒冬哥他們回來了,我們就該下水了。急得沒招的時候放棄主觀臆斷完全按照綁帶1-2-3-4 穿繩,陰差陽錯居然對了,還好沒耽誤時間。
冬哥上來,喊我們下水,AOW 5 人上船。最后這一潛,冬哥、黃同學、大師姐三個教練帶著我們兩個OW 到處逛海底。3 臺GoPro 直拍,簡直不要太爽。我們不僅看到了大螃蟹、烏賊、石斑魚、小丑魚、鰻魚,還有各種海底螺貝、海星。真的沒想到,東山島的海底太多神奇。以至于最后我們不得不上升時,感覺自己完全沒玩夠。沒想到真的掌握技巧以后,在海底自由自在游弋的感覺,是如此的特別。可能,在此刻,我終于有點理解“潛水”的魅力了。
我想起了去年電視劇《小歡喜》中天文館劉靜的那段超治愈的話:當我們注視太空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尋找自己的起源。我們自己的故事,就是宇宙的故事。其實,沉入海底,我們何嘗不是在探究自己的起源。星辰大海,是起源,也是歸宿。千萬年來,人類對飛行的渴望,對潛游的追求,說到底是外觀世界、內尋自我的探索。
為什么“壓力煩惱沒了”?那是因為,下潛時,我們在深海中自己解答了自己的疑惑。林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我們就是那條正在下潛的“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