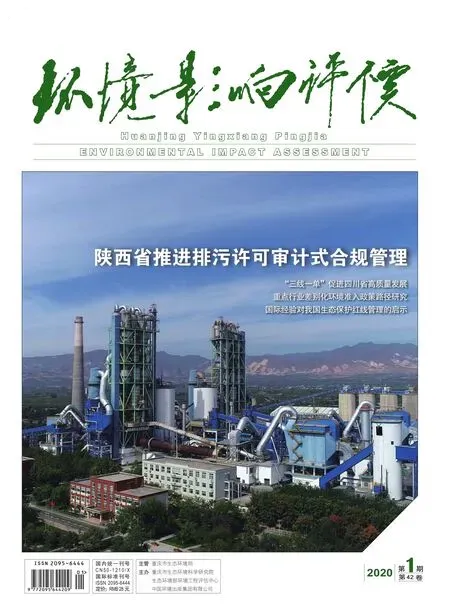環境風險評價的現狀問題及建議初探
賈黎,任勇,范辭冬,饒維
(1. 四川省環科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成都 610094; 2. 四川省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四川成都 610016)
目前突發環境事件已越來越被公眾所關注,化學品爆炸及泄漏、原油泄漏等事件引起人們極大的關注,且直接影響周邊區域的人身健康及財產安全。現代社會應將環境風險管理納入制度化管理體系中,以期預防和降低環境風險。其中,環境風險評價屬于環境風險管理體系的重要環節,為預防、控制、減緩環境風險提供技術支撐。
1 環境風險評價的發展歷程
環境風險評價,應以突發性事故導致的危險物質環境急性損害防控為目標,對建設項目的環境風險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環境風險預防、控制、減緩措施,明確環境風險監控及應急建議要求,為建設項目環境風險防控提供科學依據[1]。
我國環境風險管理和評價工作起步于1988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重大建設項目特別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項目在環境影響報告書中設置了環境風險評價專題。2004年,原國家環保總局頒布的《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HJ/T 169—2004)要求涉及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險物質生產、使用、儲存的建設項目(不包括核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應包含“環境風險評價”章節,標志著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工作的全面鋪開。2018年,《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修訂版(以下簡稱《技術導則》)發布實施。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推動我國于2007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作為該法中環境應急管理工作的責任部門,原環境保護部(現生態環境部)從2009年至今出臺了一系列環境應急管理的規章、文件、技術指南,涵蓋環境應急管理的全過程,包括環境風險評估、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編制和管理、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處置、應急監測、信息報告、污染損害評估等,初步構建了我國環境應急管理體系。2015年,原環境保護部頒布了《突發環境事件應急管理辦法》和《企業事業單位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備案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了部分企業事業單位須制定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并以突發環境事件風險評估和應急資源調查為制定的基礎。
2 環境風險評價存在的問題
2.1 與安全評價標準的協調
環境事件往往起源于安全生產疏漏,加強企業安全管理是預防和降低環境事件的關鍵。在我國,環境風險管理、安全管理分別由不同職能部門監管,環境風險管理的職能部門為生態環境主管部門,安全管理的職能部門為應急管理主管部門。因此,一個有環境風險的企業須在項目建設前分別開展環境風險評價和安全評價。
環境風險評價和安全評價既有區別也有聯系。區別在于,評價目的側重點不同。安全評價的目的側重于優化企業內部的安全設計及管理,是對事故原因的排查和防范;環境風險評價的目的側重于控制和減緩企業事故發生時對外界的環境危害,是對事故后果的控制和減緩。聯系在于,技術路線總體一致。在評價中開展事故發生和影響結果的模擬,均需要開展危險性辨識、源強估算、事故概率、事故后果預測[2]等工作。
《技術導則》刪除了安全防范措施內容,更側重于環境風險防范和有毒有害物質進入環境的應急處置[3]。技術路線總體一致的特點,又決定了環境風險評價和安全評價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環境風險管理和安全監管部門不同,則造成了我國環境風險評價和安全評價的技術標準差別較大:
(1)危險化學品危險性識別依據不同。環境風險評價采用歐盟《塞維索指令Ⅲ》等中推薦的臨界值,安全評價則采用《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辨識》,前者中大多數危化品臨界值較后者更嚴格。以硫化氫為例,環境風險評價中推薦臨界值為2.5 t,安全評價中相應值為5 t。
(2)泄漏場景的推薦假設不同。環境風險評價推薦的泄漏場景有泄漏孔徑10 mm、10分鐘內儲罐泄漏完畢、儲罐全破裂等,并提出了相應的泄漏頻率推薦值[1];安全評價推薦的泄漏場景有小孔泄漏、中孔泄漏、大孔泄漏、完全破裂四種[3]。
(3)大氣污染物毒性濃度標準不同。環境風險評價采用美國能源部規定的采取保護性行動標準(PAC)作為大氣污染物毒性終點濃度標準;安全評價則采用美國環保署、聯邦應急管理署規定采取的應急響應計劃指南值(ERPG)作為大氣污染物毒性終點濃度標準。以三氟化硼為例,安全評價采用的危及人生命和健康的濃度為100 mg/m3,對人體造成不可逆影響的濃度為30 mg/m3[3];而環境風險評價中對應濃度分別為88 mg/m3和29 mg/m3。
(4)評判風險可接受水平不一致。環境風險評價不要求開展風險可接受性水平評判,只要求增加評價結論及建議的內容[4];安全評價要求部分危險程度高的重大危險源應開展定量風險評價,并計算個人風險值和社會風險值,對于風險值超出可接受水平的,有必要通過減少危險品數量、種類、修改工藝和貯存條件、優化總圖布置、改進設備等措施進一步降低風險。
2.2 與環境風險評估的區別與聯系
目前,我國大多數有環境風險的企業要進行兩次環境風險評價(估)。第一次是在項目開工建設前的項目環評階段,稱為環境風險評價;第二次是在項目建成后的環境應急預案備案階段,稱為環境風險評估。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評估既有區別也有聯系。
兩者區別在于:
(1)發生時間和形式不同。環境風險評價屬于建設項目環評的章節組成。由于建設項目須取得環評報告書(表)批復后方可開工建設,故這階段的環境風險評價是在項目開工建設前就要開展的工作;環境風險評估單獨成本,作為企業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向生態環境部門備案的重要文件之一。由于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是在建設項目已建成投產或處于試生產階段編制的,因此,這個階段的環境風險評估是在建設項目建成后進行的。
(2)法律法規或標準不同。環境風險評價被寫入環境標準《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 總綱》;環境風險評價估被寫入部門規章《企業事業單位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備案管理辦法(試行)》。
(3)審批或備案制度不同。環境風險評價屬于建設項目環評的章節組成,實行審批制度;環境風險評估作為企業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的組成部分,實行備案制度。
(4)適用范圍不盡一致。環境風險評價適用于要編制環境影響報告書或報告表、且有環境風險的項目。環境風險評估適用于:可能發生突發環境事件的污染物排放企業,包括污水、生活垃圾集中處理設施的運營企業;生產、儲存、運輸、使用危險化學品的企業;產生、收集、貯存、運輸、利用、處置危險廢物的企業;尾礦庫企業,包括濕式堆存工業廢渣庫、電廠灰渣庫企業;其他應當納入適用范圍的企業。
兩者聯系在于:
環境風險評價的技術依據是《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環境風險評估的技術依據是《企業突發環境事件風險評估指南(試行)》(以下簡稱《評估指南》)以及粗鉛冶煉、硫酸企業、氯堿企業、尾礦庫四個行業的環境風險評估技術指南。《評估指南》在大量引用《技術導則》技術方法基礎上,增加了企業環境風險自查、問題整改、突發環境事件等級判斷等內容。
環境風險評價在項目建設前開展,評價的對象多為項目可研或設計。但大多數企業的實際建設內容都可能優化調整,因此環境風險評價的作用更多是對項目選址環境敏感性和潛在環境風險的初步預判;而環境風險評估則是在項目建成后開展工作,是為企業編制環境風險應急預案服務的,企業需在環境風險自查的基礎上開展相應的評估、預測以及問題整改。
2.3 方法體系與國外相比尚待加強
美國、意大利、德國、英國等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就開始了環境風險管理方面的研究和實踐。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環境風險管理和評價在立法技術、理論以及方法體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尚難以滿足制度發展需要[5],即便是現行《技術導則》,也大量參考或直接引用了美國、加拿大、歐盟及成員國等的技術成果。同時在事故數據庫、劑量—效應基礎研究等方面,我國與國外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
環境風險評價是在對以往事故教訓和發生頻率進行調查的基礎上,篩選最大可信事故進行風險預測,而以往事故發生頻率統計基于龐大的歷史事故數據庫。付靖春等[6]研究發現,國外化學事故數據庫建立時間較長,事故信息全面、準確,便于統計分析。目前,美國、英國、荷蘭、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均建立了事故數據庫,這些數據庫涵蓋的事故數量最多達到37 000個,部分需付費訪問。我國化學事故數據庫主要有三個,即事故查詢系統、化學事故案例系統、每日事故動態系統,均在2000年后建立,且部分數據庫只允許部分職能部門或協會成員查詢。與國外相比,我國化學事故數據庫還存在事故數據可靠性差、事故信息不完整、數據結構設計簡單不便于統計分析等問題。
根據《〈建設項目環境風險評價技術導則(征求意見稿)〉編制說明》(2017年),我國在環境空氣污染物劑量—效應的數據研究尚依賴國外研究成果,國際上較為廣泛使用的短期急性接觸的空氣濃度標準包括急性暴露指導水平值(AEGL)、應急響應計劃指南值(ERPG)、暫定應急暴露限值(TEEL)、采取保護性行動標準(PAC)。我國環境風險評價標準引用了PAC值。污染物劑量—效應研究一般重點探討對動物的急性毒性標準。污染事故發生時,一般重點考量會造成急性毒性影響的影響范圍和影響人數,但是2018年版《技術導則》在污染物泄漏進入地表水、地下水時仍采用環境質量標準。
2.4 部分風險防范措施標準有待完善
事故應急池及相應的管路系統是避免事故廢水下河的重要措施。目前環境風險評價中事故應急池的容積計算主要參考了石化行業標準,如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的《水體環境風險防控要點(試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事故狀態下水體污染的預防與控制技術要求》等,然而不同企業標準對火災滅火時間、初期雨水量的計算要求亦有所不同,這會導致計算得出的事故應急池容積各異,沒有統一的標準尺度。
3 加強環境風險評價的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為推動我國環境風險管理的完善,不同職能部門應加強溝通和合作,將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評估有效銜接或合并,加強相關基礎研究和數據積累工作,在相關技術導則或評估指南中明確事故應急池等環境風險防范措施的設置依據。具體建議如下:
(1)加強與安全評價標準的協調。以德國為例,該國將安全和環境職能統一在同一個部門——環境、自然與核安全部,該部下設6個司,其中環境健康、設備安全及交通、化學品安全司不僅負責廠界外的環境污染處置,還負責企業內部的設備安全管理,防止設備安全事故對人和環境的影響[5]。在我國現有職能分工情況下,不同的職能部門應進一步加強溝通和合作,推動環境風險評價、安全評價技術標準和手段更好地統一,環境風險評價和安全評價在危險性辨識、源強估算、事故概率等方面的成果更好地銜接,以及如化學事故數據庫等基礎資料的共用共享。同時,也可考慮效仿國外,將安全管理和環境風險管理的職能部門進行統一,并制定統一的評價標準和統一的管理要求,將安全評價和環境風險評價相互融合,更有利于將事故因果環節的預防和管理更好地銜接統一,也將促進評價技術人員完善交叉領域的知識儲備、更好地完成相應的評價工作[7]。
(2)有效銜接環境風險評價與環境風險評估。合并統一兩者的技術標準,避免評價技術標準因發布時間先后而產生的不一致;完善須開展環境風險評估的企業名錄,使其更具體、更易操作。同時,為避免企業試生產或正式生產階段因環境風險防范措施不當造成環境影響,也可考慮將環境風險評價和環境風險評估合并。
(3)加強相關基礎研究和數據積累工作。完善我國化學事故數據庫,參照國外先進國家的標準,進一步完善我國化學事故數據庫的結構和數據分析統計功能,開放付費或免費權限;提高劑量—效應基礎研究水平,由專業機構負責逐步建立我國各環境要素中化學污染物急性毒性數據庫。
(4)明確環境風險防范措施的設置依據。在相關技術導則或評估指南中推薦不同行業的事故應急池設置要求,不僅可指導石化、天然氣等行業,也還應指導涉及易燃易爆品或有毒有害物質的其他行業,并提出位于不同水環境敏感程度區域的項目滅火時間范圍要求,以及不同類型廠區的初期雨水計算要求。

>>環境風險評價是環境風險防控的重要環節,為預防、控制、減緩環境風險提供技術支撐
4 結語
我國環境風險評價工作已歷經30年發展,環境風險管理領域的制度和技術方法不斷完善,環境應急管理體系已初步構建。但是,還存在包括環境風險評價與安全評價在技術方法上協調不足,環境風險評價與環境風險評估銜接不夠到位,環境風險評價方法體系與國外尚存在差距,部分環境風險防范措施的標準指導有待完善等問題。對此,本文提出了解決以上問題的相關建議。隨著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對生態環保事業的日益重視以及研發、管理、監管水平的提高,相信未來我國環境風險評價工作會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