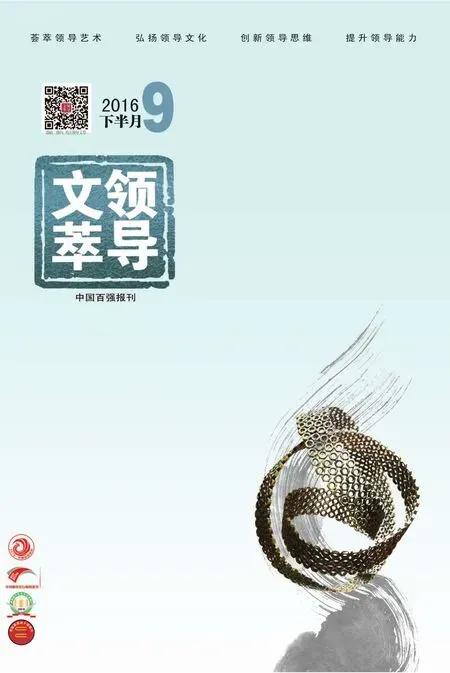不同的志節,不同的人生
徐志頻
一
左宗棠與李鴻章同為晚清重臣,是舉時代輕重的歷史人物。
左宗棠由民間草野書生入仕,儒學的“忠孝廉節”是他十分明顯的一根信仰主線。左氏遲至四十歲才出山辦事,中年后又迅速發跡,平步青云,朝廷待他的恩榮、典賞每每逾越常規,這讓他感恩戴德,竭力思圖回報,當然不愿利用名位、聲望來謀求個人利益。
作為“先秦儒學”的忠實信仰者,左宗棠在童年時習得儒學的“誠意、正心”,規牢了他畢生的忠心。他為官辦事的手段、方法,依靠的是“孔孟儒家”加“申韓法家”,前者是理想主義,后者是現實主義。
崇樸尚誠,左宗棠對事業、對朝廷的忠心,某些時候達到近似“愚忠”的程度。
當一個人對一門學說忠誠到完全“無我”的程度,便是信仰。左宗棠忠于儒學大于忠于朝廷,這從他同治十二年(1873)大膽冒犯慈禧太后的心意,不惜將慈禧太后安插的親信、烏魯木齊提督成祿拉下馬也可以看出來。
如果說,左宗棠辦事的動力源在儒學信仰,李鴻章辦事的動力源則在官階勢利。
跟草野民間成長的舉人左宗棠不同,李鴻章早年考中進士,仕途雖然也有一些艱阻,但在同齡人中已算最為順暢。
學問優長的李鴻章,跟曾國藩、左宗棠最醒目的不同的地方,偏偏就他最不相信道德文章。這跟李鴻章科場十分順暢大約有一定關系。從心理學角度看,人往往“缺什么才補什么”,“越是擁有,越不珍惜”,李鴻章本人的經歷能印證這點。
早年在京師、安徽兩地為官,李鴻章見慣了官場的“套路”跟“忽悠”,內心對那些寫在書本上的道義,其實已經是不信了的。在現實無數次的血與火的考驗面前,他看懂了,也看破了,他相信成功唯一需要的是依靠實力。一旦事權到手,他不惜打破傳統,大膽起用清一色的大老粗,根本沒將學問放到眼里。
實用至上的李鴻章,為官的心路轉折,發生在知天命之年。二十歲到五十歲,懷滿腹學問的李鴻章只是看不上“書呆子”,除了迷信官階勢利,他什么也不相信;但到五十歲那年,他連封賞給自己官階勢利的朝廷,也都發自內心地不相信了。
年輕時以“詩言志”夢想拜相封侯的李鴻章,畢生有一種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欲望,因此他的骨子里免不了有一種鶴立雞群之后沐猴而冠的心理。條件一旦具備,他開始迷醉于漫無節制的虛榮,似乎這是唯一實在且靠得住的東西。
隨著年齒日增,權勢日益烜赫,不信朝廷、不信書本的李鴻章耽逸習氣和虛榮心暴露無遺,這為他成為晚清衰世的“裱糊匠”鋪墊好最后一級臺階。這也是三人志趣的截然差異:“曾國藩拼命做學問,左宗棠拼命辦事,李鴻章拼命做官。”
官本位的“實用主義”取代一切,頭頂沒有信仰,內心沒有自律,帶來后果也需要自己內心慢慢消化。梁啟超在做《李鴻章傳》時,也忍不住要批評他“不學無術”。
曾國藩晚年時,曾以自身多年閱歷、心得提醒李鴻章,要他切記,“即數十年辦事之難,難在人心不正、世風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風,實賴一二人默運于淵深微漠之中,使其后來者為之應和”。這給他指明了儒家士大夫的道路方向,一兩個仰望頭頂星空的人,憑借自己的學理洞見,可以為自己的國家、民族找到出路,讓千百個應和者呼應跟從,實現個人的時代使命。以李鴻章此后的作為對照,曾國藩身后三十年,他似乎完全忘記了這句囑托。
因此,對李鴻章學問新舊駁雜,內心漂浮游移,成色不純,他個人在歷史演進中的作用,用得著梁啟超那句評價:“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
二
比較之下,左宗棠則有所不同:四十八歲前,左宗棠因太平天國時勢而起,屬“時勢所造就的英雄”;四十八歲到七十三歲,左宗棠主動謀國,事實上變身成了“造就時勢的英雄”。
雖然歷史從來不能假設,但我們可以依照邏輯最合情合理地推斷:中國如果從1860年到1901年沒有李鴻章,他所承擔的職事,一定有能力大致相當的人替代;如果中國從1852年到1885年沒有左宗棠,他所選擇的事業卻將不見于歷史,因為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替代他。
但左宗棠存在的問題,同樣在他的崛起起點時已經注定。作為草野民間成長出來的獨立士人,他獨有的“清氣”與個人素質中的“明澈”,讓他的家國事業能夠取得空前絕后的大成功,卻很難有第二個人能夠跟進與延續,因為能有他的天資稟賦又同時遭逢崛起機遇的人,萬中無一。
今天去探求左宗棠改變后世學問、陶冶風俗最見現實功效的地方,在于他開啟了中國近代技術類“實學”的風氣之先。他去世二十年后,八股取士取消,他當年所習的理工技術知識,成為所有新式學堂傳授的主課。對三千年來一直缺乏“科學”知識與“科學”精神的中國人,左宗棠無意中起到了先知與拓荒者的作用。
左、李相似的性格特點,是才高氣大。《清史稿》作者趙爾巽對這點曾有過寫實的評述:李鴻章一生“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左宗棠少年時代“喜為壯語驚眾,名在公卿間。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中年以后“鋒穎凜凜向敵矣,士論以此益附之,然好自矜伐”。
從中可以看出,兩人先天相同的稟賦,后天表現又大有不同:
李鴻章生平自負于才氣,將自己看得高人一頭,對部下習慣以金錢、官爵之類利益刺激加以籠絡,事實上并沒有真正得到他們的心。因此,社會上那些自恃有風骨、重操守的人才,都不樂意附從他,替他辦事。
左宗棠同樣自負于才氣,少年時代曾被人看作“狂生”;待中年出山辦事后,他的才氣轉化成進取的銳氣,剛毅過人,身先垂范,部屬對他都發自內心地由衷敬佩,自愿鞍前馬后跟從他,效死疆場,建功立業。待左宗棠位高權重、聲名顯赫之后,也免不了顧盼自雄,以“天下第一”自居,雖然“惕勵”如他,內心仍能保持足夠的清醒與克制。
通過比較左、李“自負于才氣”,大約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少年自負式的意氣是成大事者需要具備的一種強烈自信資質,畢竟成年后事業道路無論順逆,事實上都充滿了坎坷,遍布著荊棘。少年意氣是一個人在青少年時代建功立業的朦朧初心,也是出人頭地的原始動力,它支撐著人在事業的道路上不畏艱巨、義無反顧。
(摘自《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