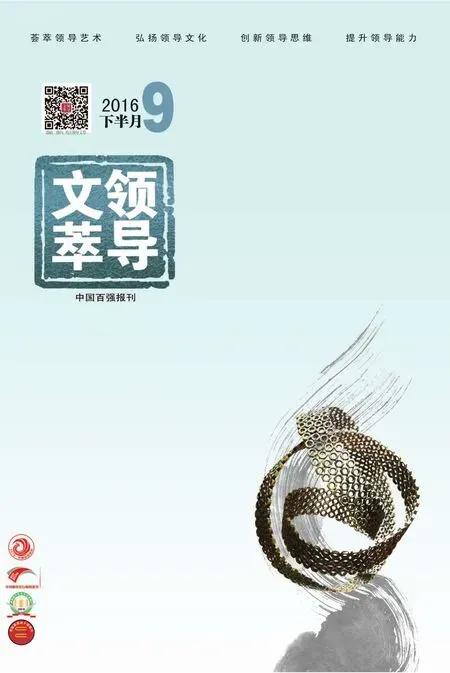全球博士過剩本質上是失敗的人力資本投資
關不羽
隨著全球主要經濟體進入了“后疫情時代”,就業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一個老問題也隨之浮上了水面:全球博士過剩,就業困難。
早在2004年7月,《讀賣新聞》就發表了專題文章,指出“博士過剩”與日俱增。同年8月5日,日本先端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近藤隆發表題為《博士過剩可惜》的文章,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注意。
2011年英國著名科學雜志《自然》發表題為《校正博士教育》的社論指出,當前全球博士人數越來越多,導致博士生畢業后出現就業問題,甚至出現了“像種蘑菇一樣培養博士”的現象。2016年,該雜志再次發表了類似主題的文章。
“像種蘑菇一樣培養博士”道出了博士過剩的直接原因,盲目擴招。日本尤為典型,戰后經濟崛起后,日本發現本國單位人口的研究生數量比例嚴重低于其他發達國家,深以為恥。政府為此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以擴招研究生的方式發起“高等學歷大躍進”。
近藤隆的研究顯示,2003年日本的碩士、博士數量是1983年的四倍。碩士這樣應用方向的人才數量增長尚能被企業消化,以專業科研和大學教職為“正途”的博士們就為難了。公立大學和科研機構受到財政規模的限制,人事擴編跟不上“大躍進”的步調。私立大學的經費則受制于少子化導致的生源銳減,也沒有增加教職的意愿。供需失衡,必然過剩。2003年日本畢業的14512名課程博士,就業率只有54.4%,人文專業僅有29.1%的博士畢業生找到了工作。
部分歐洲發達國家也存在擴招導致博士過剩的問題,成因則更為復雜。以法國為例,1994年博士畢業生比1990年增長了56%,增速尤甚日本。博士就業困難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法國戰略分析中心2010年7月29日發布的一份針對法國博士就業問題的分析報告發現,法國博士畢業3年后的失業率在2007年首次超過了碩士,并且法國博士失業率是其他經合組織國家的3倍。
歐洲大幅擴招博士的原因主要源于政府財政政策。歐洲發達國家普遍施行“大政府”,政府財政汲取度高達GDP的40%以上。政府財政支出高企,其中教育和科研支出很少受到民眾的反對,支出有增無減。人口老齡化后,接受普及教育的人數并未增加乃至下降,教育經費涌入了高等教育體系。再加上科研經費的扶植,高教系統有擴招的動力。仍以法國為例,博士生的科研費用直接從政府申請,不占用導師科研經費的份額,導師當然很樂意用政府的經費增加人手。于是,博士擴招勢不可擋,甚至本國生源不足還要引入外國留學生。法國在讀博士超過四成是外國留學生。但是,就業需求沒有相應增加,過剩不期而至。
明知博士就業困難,為什么還有那么多學子愿意成為“多余的博士”呢?日本的東亞儒家文化傳統崇尚學問,高學歷對家庭教育投資的吸引力非常大。而在歐洲發達國家,常年因高失業率困擾,接受學歷教育就成了很多學子的“就業避風港”,政府對此也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政府扶持之下,法國博士生的待遇相當于基層公務員,此外還有科研項目、助教等補充收入來源,經濟水平可以維持在中等以上,何樂而不為?無論出于東亞式的學歷崇拜,還是歐洲的經濟驅動,最終結果都是博士過剩。
博士過剩使得企業研究部門更容易獲得高端人才,但是這一正面作用不可高估。博士教育是以學術研究和高等教育為導向的,與大部分中小型企業的就業需求并不匹配。2016年,世界最大薪酬統計網站、美國的“PayScale”的數據顯示,企業中的博士薪酬水平并不比本科生高多少。成熟的就業市場對博士并不特別垂青。
培養博士生需要個人、家庭和社會投入大量資源,是人力資本投資中最為昂貴的一種。但是,政府主導的博士生培養制度,對就業市場的供需關系考慮甚少。大眾又在滿足教育、科技需求上一味求多,沒有意識到投入與產出的不對等及資源的浪費。這就是博士過剩的真相:失敗的人力資本投資。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