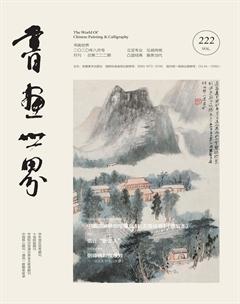近代我國臺灣地區供養福建畫家的風尚及其影響
翁志承


關鍵詞:近代;臺灣地區;書畫供養;福建畫家;影響
我國早在戰國時期就有豪門縉紳供養門客士人的風氣,如戰國四公子及其門客。清代的封疆大吏,也大都供養過幕僚,以作為他們的智囊團。到了晚清,封建王朝逐漸衰落直至滅亡,但供養門客士人的傳統風氣仍在延續。
近代閩臺地區的達官富賈或收藏大家,也仿效傳統之風,供養士人。除了政治、商業方面的精英,許多擅長丹青的文人墨客和精于藝道的藝師也常是他們供養的對象,這在當時已成為一種社會風尚。
福州的陳寶琛家族、龔易圖家族富于名家書畫收藏,又精于鑒賞,好丹青。他們退隱山林后,以延攬書畫名家舞文弄墨為雅事。許多文人墨客都曾是陳家、龔家的座上賓,他們常往來于府上,揮毫潑墨,切磋技藝。
臺灣的豪門世家也承福建之風,往往愛請文人墨客到家中做客,并成為社會風氣。李欽賢在《臺灣美術閱覽》中言道:“十九世紀中葉是臺灣文化社會內地化取向的巔峰,富賈名紳士競相延聘宦游或流寓書畫家以求邸宅蓬蓽生輝。”[1]由于閩臺兩地的各種親緣關系,福建畫家往往成為臺灣大戶世家禮聘的首選對象,其中福建畫家呂世宜和謝穎蘇是被臺灣士紳禮聘供養的代表性人物。
呂世宜(1784—1855),字西村,福建廈門人。呂氏愛金石、工考證、精書法,篆隸尤佳。“當時淡水林氏以豪富聞里闬,而國華與弟皆壯年,銳意文事。聞其名,見其書,心焉慕之,具幣聘,來主其家。世宜遂主林氏,日益收拾三代鼎彝,漢唐碑刻,手摹神會,悠然不倦。林氏建坊橋亭園,楹聯楣額,多其書也。”[2]據林宗毅《愛吾廬題跋后志》所言,呂世宜曾為林氏兄弟及其后人“致書十萬冊,金石書畫無計”。
呂世宜在臺灣畫壇影響深遠,不僅林家林國芳及林國華長子林維讓、次子林維源皆師之,而且呂世宜的手跡在臺灣社會流傳甚多,社會上不少人廣為效之。如新竹鄭神寶、豐原蔡說劍、銅鑼謝景云、嘉義羅峻明等都能得其風貌,臺灣畫壇稱其:“對中華文化在臺灣的浸潤,發揚光大,居功彌深彌遠。”
謝穎蘇(1811—1864),字琯樵,福建詔安人。謝穎蘇于清咸豐年間來臺,初受聘于臺南莊雅橋家,后在臺南海東書院、艋舳青山宮和臺北板橋大觀義學講授繪畫和書法藝術。又據《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謝在被聘至富紳莊雅橋家之前為臺南吳尚霑所禮聘,居于吳尚霑的宜秋山館。吳尚霑師事謝穎蘇,習畫梅、蘭、竹、菊,尤以畫蘭最為出色。謝穎蘇在臺灣三四年間,為臺灣南北名邸士紳所爭相迎聘,所到之處皆受禮遇。謝穎蘇在臺灣執弟子禮的除了林本源家的林維讓、林維源兄弟,臺南吳尚霑外,尚有淡水庠生鄭鵬翔、嘉義林玉書、基隆蔡大成、淡水洪詩清等人。謝在臺期間,對臺灣畫壇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被譽為“臺灣美術開山祖師”[1]。
除此之外,福建還有諸多畫家也被臺灣富賈名紳禮聘供養:或被供為座上賓,或被聘為西席,或主其家事。畫家寓居富賈名紳府邸中,傳道授業,交游作畫,酬唱應和。例如,福建畫家李霞(1871—1938)于1928年東渡臺灣,辦展授徒,被聘為“新竹益精書畫會”舉辦的“全臺書畫展覽會”審查委員,曾受邀寓居時任“益精書畫會”會長的鄭神寶家,與其交誼甚篤,也與畫會的范耀庚父女等人廣為聯系。福建廈門畫家吳芾(生卒不詳)擅長花鳥翎毛兼山水畫,于清光緒末年旅臺,初居鳳山,后應臺北大龍峒陳家陳天來之聘主其事有年,后多次往返于閩臺之間。乙未割臺后,晉江畫家蘇鏡潭客寓板橋林本源家,后應霧峰林家之聘任林家西席有年。晉江書畫家吳鐘善,受聘臺北板橋林家西席有年。晉江畫家許筠擅長花鳥畫,曾應板橋林家之邀至臺,亦曾指授臺北蔡大成。福建泉州惠安人辜捷恩,清光緒年間秀才,善詩文、工書畫,民國八年(1919)渡海入臺,為鹿港辜家西賓多年,后寓臺北,任板橋林家教席。
因文獻記載的匱乏,我們暫無法了解近代臺灣豪門望族供養禮聘福建畫家的全部細節,但通過上述管窺可見近代臺灣地區供養福建畫家的風尚之事實。綜合上述概況及參閱《林衡道先生訪談錄》《臺灣地區開辟史料學術論文集》等有關書籍,我們大致可知近代臺灣地區供養福建畫家的風尚之特點。
其一,書畫家為豪門縉紳望族所禮遇延攬,或供為座上賓,或當任西席,或主其家事,或協助收藏古董書畫,等等。書畫家寓居府邸中,除了能享受主人為他們提供的食、宿、用,有的還有一定的薪水。
其二,書畫家在主人的府邸中,多承擔教習其子弟或族人親戚詩文書畫之任,且常留有不少畫作于府中。
其三,望族府邸中多富收藏,受聘的書畫家也因此得以鑒賞經典收藏,開闊眼界。書畫家又在主人提供的優越環境中,常與地方文人雅士交游往來,廣交墨緣,切磋藝事。
縱觀這一時期臺灣書畫供養之風尚,究其內涵,仍是傳統養士性質的贊助方式,受供養的書畫家與供養主之間尚存有一定程度上的人身依附與禮尚往來關系。供養主大都是富商望族,他們多以貴族化的藝術供養贊助為主,還并未真正向大眾化、商業性的現代書畫藝術贊助轉變。然而,對福建畫家來說,渡海入臺鬻畫,面對陌生的社會環境與市場,雖然他們也可以通過只身闖蕩社會、鬻字賣畫,在臺灣安身立命,但是不可否認,這些福建渡海畫家為臺灣富賈名紳禮聘供養,供養主為其在臺灣的生活、創作、交游等方面提供了優越的條件,這無疑是許多初涉臺灣的福建畫家開拓事業的最佳選擇。望族巨室雄厚的經濟實力與禮聘的富足待遇,首先滿足了福建畫家在臺灣立足的必要物質生活條件,使許多福建畫家一到臺灣就不必為生活奔波,少了許多風險,可以直接在供養主提供的良好條件與環境中,一心傳道授業、交流技藝,為臺灣畫壇帶去“祖根”之地的藝術精神。
如廈門畫家吳芾擅長花鳥翎毛兼山水畫,光緒末年旅臺,初居鳳山,后應臺北大龍峒陳天來之聘主其事有年,多次往返于閩臺之間。吳芾畫風受海派吳昌碩、王一亭影響較大,擅長寫意花鳥。吳芾有堅實雙鉤之基本功,即便畫粗枝大葉,也不離法度,山水畫亦簡古可喜。根據文獻資料,吳芾在臺灣日據時期至少有三次應邀渡臺的記錄,在臺灣頗受地方名流歡迎,曾受到辜顯榮、林柏壽、陳天來等地方士紳的支持。“吳芾曾經在鳳山居住過一段時間,其畫風在臺頗受歡迎,雖然當時‘臺展開辦已是第六回,但其在臺仍獲許多支持。”[4]1934年,吳芾受“新竹麗澤書畫會”之邀到畫會授藝交流,現從臺灣畫家范天送后人所提供的珍貴照片上看,“新竹麗澤書畫會”成員與地方士紳在修園為吳芾舉行盛大歡迎會,并合影留念。由此可見福建畫家吳芾受臺灣地方士紳與畫會同道的歡迎程度,也彰顯出閩臺兩地書畫的親緣關系。
又如福建畫家李霞于1928年東渡臺灣,辦展授徒,與時任“益精書畫會”會長鄭神寶交誼甚篤。臺灣當地書畫人士與福建畫家李霞頻繁接觸、切磋畫技而受其影響。如:陳湖石(1888—1952),字鏡如,號陽云山人,新竹人,擅長人物,濃墨粗描,筆力雄健;陳心授(1862—1933),字道宗,新竹人,常與李霞等人切磋詩畫,對新竹地區國畫之發揚貢獻頗多;鄭玉田(1897—1965),字莜三,號劫塵,新竹人,平生喜好繪畫,尤擅長人物畫,畫法深受李霞畫風影響。另按臺灣畫師廖慶章的說法,李霞亦曾在鹿港天后宮留下壁畫,吸引許多臺南畫師前往欣賞觀摩[5]。
李霞在臺期間與活躍于當地的書畫家及士紳交情甚好,并時有筆墨酬唱、傳道授業等交流活動,在當地的書畫圈有一定的影響。2007年,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李霞人物畫展”,并評價:1928年李霞曾來臺寓居兩年,他與新竹地區藝文人士往來密切,擔任“新竹益精書畫會”舉辦的“全臺書畫展會”審查委員,在臺中新富町還舉辦過畫展。他為日據時期臺灣趨漸萎靡的中國傳統繪畫注入一股新的活力[6]。
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在書畫供養過程中,供養主固然有借重書畫名家來附庸風雅,甚至博得家聲的因素,但仔細考量這些名門望族,他們大都熱衷傳統文化,在這種禮聘供養的舉措中,自然流露出對中國傳統藝術的認同與向往之情,并期望借此教化族人子弟,以寄托讓傳統文化在后代子孫中傳承不斷的理想。如乙未割臺后,散落閩臺兩岸的臺灣板橋林家后人,一方面參與地方社會建設,創辦實業,一方面仍承襲祖訓,禮聘供養文人雅士,時有風雅聚會,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仍在林家府內傳播。林爾嘉內渡后在廈門興建“菽莊花園”,仿效臺灣祖上的傳統,延攬禮聘福建的文人雅士,聚集園內吟詩作畫、交相酬唱,影響甚大。留守臺灣的林家后人,繼續興辦文教,熱心文藝事業,常禮聘福建渡臺文士為西席,以教導族人子弟。又如1929年,為反對官辦“臺展”打壓傳統書畫,新竹鄭神寶策劃并舉辦“全臺書畫展覽會”,為傳統書畫藝術搖旗吶喊。這個展覽被譽為臺灣日據時期傳統書畫最大規模的展覽,成為與殖民同化藝術相抗衡的時代強音。
如此等等,不難看出在近代社會大變遷的急流中,臺灣的這些供養主身上依然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可以說他們的實業救國之夢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割舍不斷的情結,是促使他們常常樂于禮聘來自“祖根”之地的文人墨客,樂于為文人墨客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并借助自身的社會影響力,促進傳統書畫在臺灣傳承發展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來,近代我國臺灣地區供養福建畫家之風尚,是兩岸傳統中國畫藝術傳承交流的一個重要紐帶,也是兩岸人民守護傳統藝術的共同精神家園,它凝聚了兩岸人民的藝術理想與追求。憑借書畫供養的風尚,福建畫家在臺灣積極傳播“原鄉”的中國畫藝術,使傳統中國畫藝術在臺灣得以綿延,對臺灣的畫壇影響顯著而深遠。此外,臺灣的藝術追隨者在與福建畫家的交游唱和中,尋求到傳統藝術“祖根”的精神力量,牢牢維系著閩臺兩地長期建構起來的中國畫藝術的文脈,在近代閩臺地區風云變幻的特殊歷史時期,彰顯出特有的親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