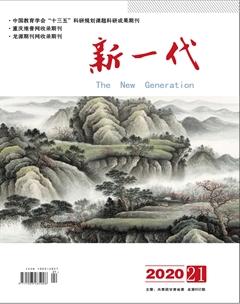我國當(dāng)代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問題與提升路徑
肖興婷 張鳴哲
摘 要:在2020年3月6日召開的決戰(zhàn)決勝脫貧攻堅(jiān)會(huì)上總書記指出,我國目前脫貧進(jìn)度符合預(yù)期,取得決定性的脫貧成就,但仍面臨著嚴(yán)峻的挑戰(zhàn)。教育精準(zhǔn)扶貧在脫貧攻堅(jiān)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教育精準(zhǔn)扶貧在引導(dǎo)多元主體參與、政策間的協(xié)同度和測評機(jī)制方面還存在諸多不足。對教育精準(zhǔn)扶貧存在的問題不斷反思總結(jié)、提升優(yōu)化,對于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有著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教育精準(zhǔn)扶貧;困境;路徑
中國扶貧事業(yè)進(jìn)行了幾十年,隨著我國關(guān)于貧困的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國扶貧事業(yè)取得了巨大進(jìn)展。同樣,在扶貧實(shí)踐的不斷推進(jìn)中,我國扶貧的方式也取得了質(zhì)的發(fā)展和突破。從原來的單一資助扶貧轉(zhuǎn)變?yōu)槎嘣鲐殻瑥脑瓉淼妮斞椒鲐氜D(zhuǎn)變?yōu)樵煅椒鲐殻瑥脑瓉淼拇笏嗍椒鲐氜D(zhuǎn)變?yōu)榫珳?zhǔn)扶貧。縱觀近年來的各種減貧方式,教育扶貧相較于農(nóng)林產(chǎn)業(yè)扶貧、旅游扶貧、科技扶貧、就業(yè)扶貧、健康扶貧等扶貧方式具有極大的優(yōu)越性,不少學(xué)者基于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更是認(rèn)為教育扶貧是解決貧困和防止返貧的根本途徑。但是,目前在我國的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實(shí)施進(jìn)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教育扶貧機(jī)制的不斷改善是我國社會(huì)主義本質(zhì)的要求,對于實(shí)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的目標(biāo)至關(guān)重要。
一、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內(nèi)涵
教育扶貧的內(nèi)涵發(fā)展至今,通常有著雙重的含義——“扶教育之貧”與“以教育扶貧”。針對不同的含義取向,在教育扶貧的方式上也會(huì)有所不同。在扶貧工作開展初期,對于教育扶貧的含義更多是“扶教育之貧”,針對每個(gè)地區(qū)貧困的原因,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鑒于部分貧困地區(qū)致貧的重要因素就是教育資源、教育環(huán)境的匱乏,在“扶教育之貧”的定義取向下,采取的扶貧措施更多是給予教育資源補(bǔ)助,支持農(nóng)村教師計(jì)劃、鄉(xiāng)村學(xué)校改造計(jì)劃,使得貧困地區(qū)的人力、物力獲得了極大的補(bǔ)充,但是貧困地區(qū)的硬件設(shè)施獲得了極大的提高。但是貧困地區(qū)的發(fā)展不僅需要硬件設(shè)施的支持,還需要持續(xù)不斷的人力。但是在單向的“扶教育之貧”的含義取向指導(dǎo)下,對于貧困地區(qū)的教育扶貧往往會(huì)造成大量補(bǔ)助物資的閑置,而教育扶貧下的人力資本輸入則需要大量的資金來維持,這也就是單向“扶教育之貧”定義下的教育扶貧措施存在的弊端。而單向的“以教育扶貧”則是針對部分貧困地區(qū),造成貧困的原因是多樣的,但是可以通過教育使得這些導(dǎo)致地區(qū)貧困的不利因素得到消減,甚至根除。比如由于貧困地區(qū)主要以農(nóng)業(yè)為主,加上惡劣的自然條件或者天災(zāi)導(dǎo)致陷入貧窮,那么通過教育,可以提高勞動(dòng)力素質(zhì),改進(jìn)技術(shù),從而走上致富之路。當(dāng)然,教育是一項(xiàng)長期投資,沒辦法做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作用于脫貧,因此,就需要多種方式的配合,而現(xiàn)在關(guān)于“教育扶貧”的含義也往往兼有以上的雙重含義。
1984年,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了《關(guān)于幫助貧困地區(qū)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提出“增加智力投資”,這是第一次在國家政策中提出“教育扶貧”的概念。2013年,總書記在湖南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考察時(shí),提出“扶貧攻堅(jiān)就是要實(shí)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dǎo),精準(zhǔn)扶貧。”這是首次明確提出“精準(zhǔn)扶貧”的概念,這也標(biāo)志著我國脫貧攻堅(jiān)工作進(jìn)入了以精準(zhǔn)扶貧為特征的新階段,這揭開了我國教育扶貧的新篇章。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提出展現(xiàn)出我國在消減貧困這項(xiàng)工程上正在把活越做越細(xì),與以往的粗放式的教育扶貧不同,它對于貧困對象的識別更加更精確,幫扶更加到位,避免了以往的大水漫灌式導(dǎo)致的浪費(fèi)。而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下發(fā)《關(guān)于打贏脫貧攻堅(jiān)戰(zhàn)的決定》,強(qiáng)調(diào)把精準(zhǔn)扶貧、精準(zhǔn)脫貧作為基本方略,并提出要著力加強(qiáng)教育脫貧,實(shí)施教育扶貧工程。這將精準(zhǔn)扶貧的地位提高到了一項(xiàng)基本方略,突出了教育扶貧的重要性,把它看成為了治療貧困的一劑良方。
二、教育精準(zhǔn)扶貧面臨的困境
首先,教育精準(zhǔn)扶貧主要以政府為主導(dǎo),多元主體的參與度不夠。雖然教育精準(zhǔn)扶貧最重要的主體是政府,但是貧困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性的問題,教育扶貧與其他社會(huì)公共品的投入一樣,投入大,成本高,僅僅依靠政府,無疑會(huì)加重政府的財(cái)政壓力。因此,必須要多方主體的共同參與,這樣才能充分激發(fā)教育扶貧的活力,使貧困地區(qū)重新煥發(fā)活力。不管是學(xué)前教育階段的《學(xué)前教育三年行動(dòng)計(jì)劃》和學(xué)前教育資助政策、義務(wù)教育階段的 “兩免一補(bǔ)”、還是高等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學(xué)生資助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實(shí)施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導(dǎo)的,主要用于扶貧對象的幫扶、對其他社會(huì)主體的激勵(lì)和引導(dǎo),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矚目的成績,但是,這些激勵(lì)與引導(dǎo)的背后,是每年教育經(jīng)費(fèi)的巨大支出。并且,社會(huì)資本主要流入的是在貧困地區(qū)中一些相對較有潛力的地區(qū),對于在一些深度貧困的地區(qū),對于其他主體比如社會(huì)組織、企業(yè)的吸引度和可參與性并不高,因?yàn)閰⑴c的成本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預(yù)期收入或者效益回收周期太長。
其次,教育精準(zhǔn)扶貧一體化程度較高,但是協(xié)同性還不足。這種不足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參與部門的單一性和政策之間的不協(xié)調(diào)。一方面,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制定、實(shí)施都是由政府牽頭、為主導(dǎo),其中參與的主要部門是教育部和財(cái)政部,其他部門參與度較低,部門間的相互協(xié)作與聯(lián)動(dòng)并沒有很好地發(fā)揮出來。另一方面,隨著教育精準(zhǔn)扶貧工作地不斷深入,與之相對應(yīng)的我國教育體系中,已經(jīng)建立起來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經(jīng)緯式”的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體系。“緯度”橫向涉及學(xué)生、教師、學(xué)校等不同的扶貧對象,“經(jīng)度”縱向包攬學(xué)前至高等教育、職業(yè)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各個(gè)階段。[1]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政策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gè)與我國教育體系相適應(yīng)的較為體系化的體制機(jī)制,但是在這樣一個(gè)整體性的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體系中,處于部分的各個(gè)政策之間協(xié)調(diào)度還有待提高。在職業(yè)教育政策中,《職業(yè)教育東西協(xié)作行動(dòng)計(jì)劃(2016-2020年)》與《職業(yè)教育東西協(xié)作行動(dòng)計(jì)劃滇西實(shí)施方案(2017-2020年)》均指向職業(yè)教育,但是“但政策工具的使用重心發(fā)生較大偏移,兩項(xiàng)政策之間工具使用的系統(tǒng)性、協(xié)調(diào)性明顯不足,這易導(dǎo)致職業(yè)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政策銜接出現(xiàn)縫隙、政策對接產(chǎn)生隔閡,進(jìn)而誘發(fā)相關(guān)政策被“變通性”“偏差式”執(zhí)行,影響政策效果的充分發(fā)揮。”[2]政策之間的相互補(bǔ)充、相互銜接還不夠成熟就有可能產(chǎn)生縫隙與隔閡,從而導(dǎo)致部分作用相加的和難以大于整體作用的總和,不利于整個(gè)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體系最大限度的發(fā)揮作用。
最后,教育精準(zhǔn)扶貧運(yùn)行機(jī)制已經(jīng)較為完善,但成熟的測評機(jī)制尚未建成。精準(zhǔn)扶貧是在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生態(tài)保護(hù)“雙輪驅(qū)動(dòng)”的基礎(chǔ)上,對包括精準(zhǔn)識別、精準(zhǔn)管理、精準(zhǔn)幫扶“三位一體”治貧方式的精準(zhǔn)發(fā)力的扶貧模式。[3]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模式同樣如此,但是可以明顯發(fā)現(xiàn)僅有“三位”還不夠,我們還需要 “精準(zhǔn)測評”,尤其是在脫貧攻堅(jiān)工作進(jìn)行到目前階段。教育精準(zhǔn)扶貧光有投入是不夠的,必須建立起科學(xué)的測評機(jī)制,對它的產(chǎn)出也做一定的評估,否則很容易造成投入的盲目性和投入的浪費(fèi)。只有建立起一個(gè)連續(xù)性的動(dòng)態(tài)運(yùn)行機(jī)制,包括了“精準(zhǔn)識別、精準(zhǔn)管理、精準(zhǔn)幫扶、精準(zhǔn)測評”四位一體,將教育扶貧的投入、產(chǎn)出作出精準(zhǔn)地評估,這樣教育精準(zhǔn)扶貧才能朝著更好的方向發(fā)展下去。
三、教育扶貧的提升路徑
第一,調(diào)動(dòng)多元主體參與教育精準(zhǔn)扶貧,為貧困地區(qū)注入更多活力。貧困地區(qū)難以吸引企業(yè)、外資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在于進(jìn)入成本太高。以往的教育精準(zhǔn)扶貧往往側(cè)重于直接投入資金、教育物資來改善貧困地區(qū)的狀況,但持續(xù)性動(dòng)力明顯不足,同時(shí)也是一筆巨大的花銷。要真正調(diào)動(dòng)其余主體的參與,就要為它們降低準(zhǔn)入成本,加快效益的回收,這樣企業(yè)有了可觀的收益,貧困地區(qū)也有了持續(xù)發(fā)展的動(dòng)力,達(dá)到雙贏。因此,教育精準(zhǔn)扶貧應(yīng)該致力于形成政府打造大環(huán)境、其余主體參與建設(shè),以政府為主導(dǎo)、其余主體為輔助的教育精準(zhǔn)扶貧大格局。
第二,統(tǒng)籌兼顧,提高頂層設(shè)計(jì)的精確性,對普適性政策和專項(xiàng)政策的作出明確的區(qū)分,防止范圍的重疊。政策的制定雖然是一方主導(dǎo)的,但是也是基于現(xiàn)狀和歷史,權(quán)衡多方利益之后的結(jié)果。“政策目標(biāo)的重合性和系統(tǒng)性,會(huì)對扶貧政策的執(zhí)行過程及成效產(chǎn)出形成影響。”[4]這種重合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政策資源的混合與相關(guān)政策的重疊,二是政策內(nèi)容和政策目標(biāo)群體的覆蓋的重疊。普適性政策更適合對普遍性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施策,但它的不足往往在于政策的普遍性難以適應(yīng)貧困地區(qū)致貧因素的多樣性,因此,就需要專項(xiàng)性政策來作為補(bǔ)充,因?yàn)閷m?xiàng)性政策往往更具有針對性。兩者通常可以混合使用,這樣在普遍之中把握特殊,覆蓋更多更廣的貧困地區(qū)。但是,二者間一定要作出明確的區(qū)分,否則就會(huì)導(dǎo)致對于政策的成效的評測出現(xiàn)盲區(qū)和施策成本的增加、浪費(fèi)。因此,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制定時(shí),應(yīng)注意政策之間的相互協(xié)調(diào)性。
第三,不斷加強(qiáng)教育精準(zhǔn)扶貧測評機(jī)制的理論創(chuàng)新,推動(dòng)教育精準(zhǔn)扶貧建立起完整科學(xué)的機(jī)制體系。通過采取教育扶貧措施后,貧困家庭是否達(dá)到了脫貧標(biāo)準(zhǔn),或者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措施是否有效達(dá)到預(yù)期目的,都亟待建立相應(yīng)的教育扶貧測評機(jī)制來檢驗(yàn)。首先,教育扶貧的測評機(jī)制需要一定的理論作為基礎(chǔ),但是由于目前我國的關(guān)于教育扶貧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扶貧的方式和必要性上,但是對于后續(xù)的測評和防止返貧的理論研究還不足,以致于教育扶貧的效果難以建立相應(yīng)的機(jī)制準(zhǔn)確衡量。其次,學(xué)界關(guān)于教育扶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扶貧政策這種顯性的表現(xiàn)上,缺乏對于內(nèi)源理論的創(chuàng)新。最后,尤其是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條件的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關(guān)于貧困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也在發(fā)生變化,相應(yīng)的教育扶貧的檢測機(jī)制也應(yīng)該建立完善,并且教育扶貧的測評機(jī)制同樣也應(yīng)該是一個(gè)持續(xù)性的動(dòng)態(tài)變化的過程。因此,只有不斷創(chuàng)新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測評機(jī)制的理論研究,才能精準(zhǔn)發(fā)力,推動(dòng)教育精準(zhǔn)扶貧體系的不斷完善。
縱觀我國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發(fā)展演變,它在不同的歷史時(shí)期有著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而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jiān)工作的不斷深入,對于教育精準(zhǔn)扶貧的要求也更嚴(yán)格,教育精準(zhǔn)扶貧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教育精準(zhǔn)扶貧更是要與時(shí)俱進(jìn),不斷加強(qiáng)改善,在減貧與防止返貧方面充分彰顯其優(yōu)越性,發(fā)揮出更多、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xiàn):
[1]姚松,曹遠(yuǎn)航.新時(shí)期中央政府教育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邏輯特征及未來走向[J].湖南師范大學(xué)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19.
[2] 王學(xué)權(quán).“十三五”時(shí)期扶貧新模式:實(shí)施精準(zhǔn)扶貧[J].經(jīng)濟(jì)研究參考,2016.
[3]吳霓,王學(xué)男.教育扶貧政策體系的政策研究[J].清華大學(xué)教育研究,2017(05):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