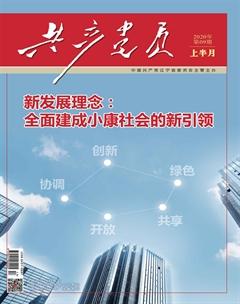“勾推法”溯源
朱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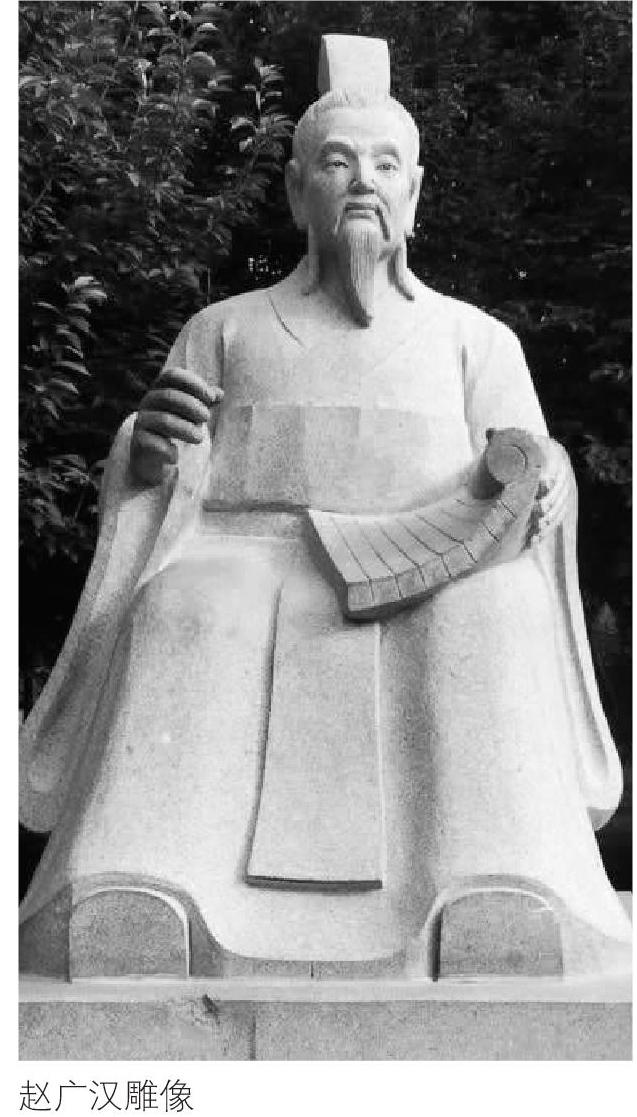
收錄于《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的文章《記者頭腦要冷靜》,是毛澤東同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的要點,時間是1958年11月21日。談話中,毛澤東根據其一貫強調的實事求是、大興調查研究的作風,對當時新聞界的一些情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指出:“記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說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靜的頭腦,要作比較。”接著他就舉了一個古人“善于比較”的例子:“唐朝有一個太守,他問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圍的人和周圍的情況,然后再審原告被告。這叫作‘勾推法。這就是比較,同周圍的環境比較。”
毛澤東談的是新聞工作,指出記者進行調查研究也須采用與司法偵查類似的手段。然而,“勾推法”究竟源于何人何事,該文文末并未加以注釋,筆者查閱多本古籍亦未找到答案,成為筆者心中多年未解的謎團。
“鉤距”或為“勾推法”源頭
近日翻閱《漢書·趙廣漢傳》,筆者驚訝地發現了這一詞匯之端倪:文中說趙廣漢此人“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對“鉤距”一詞,古人王先謙做的補注是:“鉤若鉤取物也,距與致同,鉤距謂鉤而致之。”意思是說:“鉤”字形容的是像用鉤子那樣去取物,“距”字在這里與“致”字相同,“鉤”“距”二字連用表示“將物件鉤取到手”。
再綜合其他古人對鉤距法的解說,大體上可歸納為以下兩種含義:其一是“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其二是“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案件偵查方法,即“鉤致其隱伏,使不得遁;距閉其行跡,使不可窺也”,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廣布眼線,深挖案件線索,隱藏行跡,示之以虛,從而占據案件偵破主動地位。至于后者,實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經驗推理基礎上的審訊方法或策略,可稱為迂回包抄法,為從罪嫌人或證人處獲得有關案件的關鍵細節,迂回設問,層層推進,最終鎖定證言。
再來看看趙廣漢本人的實例,該文中說趙“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后及馬,參伍其賈(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趙廣漢尤其善于運用“鉤距”的方法尋找線索并得知真相。所謂“鉤距”就是這么回事:假設想知道馬的價格,就先問狗的價格,完了問羊的價格,又問牛的價格,然后到馬的價格。比較查對它們的價格,由此推算馬的價格,推算結果往往與實際相符。
筆者注意到,原文中有“以類相推”一詞,而文中強調,“推”的前提是“鉤”,“勾(鉤)推”一詞由此呼之欲出。較之“鉤距”,“勾(鉤)推”表明還須做一番比較、推理,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過程,最終得出結論,無疑比“鉤距”一詞更精當。
趙廣漢善用“勾推法”
據《漢書》記載,趙廣漢年輕時當上了郡中小吏、州從事,因為他生性廉潔、處事通達敏捷而且謙虛待人,廣被世人所稱道。昌邑王劉征登上皇位后,行為荒淫,朝中重臣、大將軍霍光跟群臣共同廢掉劉征,推立宣帝繼位。趙廣漢因參與霍光此舉,被恩賜為關內侯爵位,升任潁州太守。
當時潁州境內大姓原氏、褚氏兩家族強橫妄為,其門客為非作歹、作奸犯科。而潁州的豪強紛紛借助錢財與大姓人家聯姻,官商勾結,欺壓百姓,橫行無忌,活似后世的“黑社會”,歷任郡守望之生畏、束手無策。趙廣漢得知,先是憂心忡忡,繼而又苦思對策。
趙廣漢的第一招是“設箱舉報,收集線索”。他受民間用的儲錢罐啟發,“教吏為缿筩(音‘向統)”,就是讓差役設計、制作多個舉報箱,到處放置。這是個歷史性的發明創舉,沿用至今。對舉報人留下的個人信息他為其保密,而對舉報中披露的事實則通過暗察私訪,一一證實。這個過程中采用的基本方法,正是互相比較,也就是“鉤距(勾推)法”。
趙廣漢的第二招是“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他對大姓家族中的中間分子采取獎勵、使用的政策,將舉報內容有選擇地透露給他們,并通過他們了解其家族中的內幕。然后他又故意向其泄露大家族之間一系列矛盾、對立的意見、信息,使得他們中間產生內訌,直至發展到公開攻訐的地步,不惜前來對簿公堂,然后趙廣漢就以官方名義受理、判決。由此,大姓家族之間互相為敵的局面愈演愈烈,由沆瀣一氣轉為分崩離析,而其中的作惡犯罪分子陸續遭到逮捕、懲處。
經過趙廣漢的巧妙治理,當地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壞人壞事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轄區上下政令暢通、人心思治,官吏百姓贊不絕口,上年紀的人紛紛贊揚:“自打漢王朝建立至今,沒有治理得這么好的時候!”趙廣漢由此聲名遠揚,連北方的匈奴人都知道其大名、業績。
遺憾的是,趙廣漢本人并未得到善終,他的口碑居然引來了殺身之禍。漢宣帝地節三年(前67)七月,丞相司直蕭望之上奏稱,趙廣漢折辱朝中大臣,用威力挾制奉公守法之人。坐穩了龍椅的漢宣帝當時也正想清除霍光的余勢,于是借此機會下旨將趙廣漢腰斬。雖然趙廣漢蒙冤而死,但他清明廉潔、懲辦豪強的功績不滅,“百姓追恩,歌之至今”。
“勾推法”源遠流長
事實上,趙廣漢的鉤距法只是開了個“源”,而“流”更在其后,“勾推法”在后世一直大有用武之地。在“勾推法”的傳承中,精于此道的干臣、能吏代不乏人,主要是將其用于司法實踐,特別是對疑難案件的審理上。囿于古代落后的科技水平,古人辦案更多依賴搜集輿情或邏輯推理手段。史書上具體提到善用“鉤距”的有這么些人:
唐朝中期曾任過京兆尹的李齊物,“為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為能”。他死后,唐肅宗褒獎他“擒奸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
晚于李齊物的另一京兆尹劉棲楚,“摧抑豪右,甚有鉤距,人多比之于西漢趙廣漢者”。
五代后晉時重臣安重榮,“目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
北宋初年的郭進,“聽訟善以鉤距得事情”。
宋太宗時大臣李惟清,“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強干”。
宋代名相杜衍,“發幽摘伏,鉤距繆數,奸不得隱,人服其神”。
元代浮梁令郭郁,“善為鉤距,以廉民隱,自比趙廣漢”。
明朝成化年間的地方官陳煒,“屢析于獄,善為鉤距,以得其情”。
上述歷代官員都和趙廣漢一樣,因其對鉤距法的嫻熟運用,贏得了百姓的口碑。
古籍《折獄龜鑒》收錄有宋代官員包拯和錢龢運用鉤距法順利破案的故事,值得關注。有趣的是,兩案皆與農家的耕牛有關——在宋代,私殺耕牛違法。這里僅舉錢龢的例子。他在嘉興縣做知縣時,有村民告狀說自己的牛被人盜殺了。錢龢讓他先回去,還囑咐他千萬別提自己告官的事。第二天,錢龢又接到舉報,丟牛的村子里有些村民在吃牛肉。錢龢馬上判定,這是此前來告狀說自己丟牛的人自導自演的一場戲。此人被收審后,果然很快就招供了。原來,錢龢早就暗地里查明,這個聲稱丟牛的人曾向鄰居饋贈牛肉,對與自己曾有過積怨的還加倍贈送。在《折獄龜鑒》一書的作者看來,錢龢的“鉤慝之術”就是源自趙廣漢的“鉤距法”。在證據的搜集、固定技術至為簡陋的古代,錢龢故布疑陣(“用譎”),誘使罪嫌人露出馬腳甚至自投羅網,顯示了他對犯罪心理學知識的嫻熟運用,手法之高明令人拍案叫絕。
總之,從古時的“鉤距”到毛澤東口中的“勾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需要我們不斷發揚光大。許多事物只要仔細考證、認真對比推理,就會有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