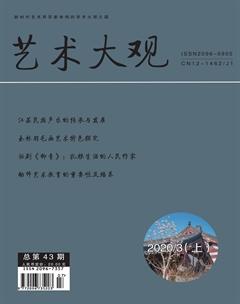淺談文化遺產視角下的中國長城及其歷史文化內涵
汪春美
摘 要:長城是我國社會物質文明發展中重要產物,具有重要的文學、教育、科學以及社會等價值,是漢文明“對立”思維方式的物化載體。“無形”長城見證了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從物質生活到社會生活,再到精神生活之間的融合之路,作為我國核心文化價值的集散地,體現出了漢文明變通的思維方式特點,是我國民族文化財富與精神象征。
關鍵詞:文化遺產;中國長城;歷史文化
中圖分類號:K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0905(2020)07-00-02
長城遺產價值主要包括長城的藝術價值、科學價值以及歷史價值,同時還包括長城所承載的管理制度、軍事防御以及建筑技藝等建筑價值,還包括長城地帶環境與社會文化等現象間規律性關系的探討價值。因此,在中華文明演變的過程中,對長城遺產中核心文化價值進行深入探討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帝國文明的見證
我國古代社會法制體系從戰國時期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權郡縣制方向轉變,并且戰爭主要以獲取土地與人口為目的,這是長城出現的社會歷史背景。長城的修建主要是農耕民族用來防御游牧民族,長城從建設至今,經歷了不同時期,長城由于自身戰略價值與一些因素,對農牧之間長期互動產生了一定影響,也決定了不同時期帝國文明的興衰。
從建設至今,長城歷經了中原農耕政權北部邊界南來北往的歷史演變,也見證了農牧民族間在政治、經濟以及文明方面的對立和融合。
長城雖然是人為的防御工事,但客觀上,長城卻是中國農牧業生產的分界線和中國農牧業的交錯帶,這自然也就成了農牧民族之間爭奪優勢土地資源的焦點地帶。比如我國古秦國為了獲得土地,對北方游牧民族發起了戰爭,產生了大片生產區。通過我國歷史能夠發現,不同統治者利用農耕社會大力修筑長城,比如從戰國到清代均有修建長城的歷史,其修建規模有一定的差別。分布在目前不同縣區的長城主要是一體防御工程體系,比如道路、墻體以及后勤等。[1]
二、“對立”思維方式的物化表現
(一)邊地居民交流的集散地
自長城修建后,從戰國時期開始對其逐漸進行修繕,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了不同朝代,最終形成以石磚為材料,以墻體為主的立體式防御體系。劉邦統治時期建設的長城,以“故塞”為邊界。在漢武帝執政時期,為了便于出使西域,同時將西北匈奴隔絕在外,并且擴展了自身的疆域;隨著時間的推移,隋代修建了長城,到了明代將長城作為重要的邊防,這也成為當時明代防務工作中的重要內容,并且通過修建形成了軍防體系,主要以軍堡、墻體以及關城等為體系核心,極大豐富了其功能,比如觀察、通訊以及隱蔽等,并且在此基礎上關城、軍堡等也是當地居民貿易、南北交流的集散地。[2]
(二)農牧民族間矛盾與融合的直接體現
經過上千年的發展,我國南北地區經濟形態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在較大程度上使文化價值取向有所不同。史前時期,北方游牧民族會根據氣候的不同而南下,長此以往逐漸成為北方游牧民族的正常事務,到了公元前2300年,游牧民族南下對中原農耕民族產生了較大威脅。在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長城修建是工作的重點,一些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修建長城作為防御,比如韓、趙、魏等國家均進行了長城的修建,其主要目的是處于防御作用。戰國中后期,南北沖突較為激烈,在以長城為防御的基礎上,產生了新型防御方法,為了對北方游牧民族實施防御,把中原國家之間修建的墻體用來防御,并將其移植到北部邊境,秦、趙、燕三國開始修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長城。自此以后,中原國家與北魏、金等區域性政權,為了防御南下游牧,修建了不同規模的長城。周王朝在征伐期間建設了最早的長城,以后便長期在中華北部區域中應用,形成了農牧民族之間矛盾與融合的直接體現。[3]
三、“變通”思維方式的集中體現
(一)農牧融合交流的平臺
長城氣候以及地貌處于過渡帶,其氣候與地質條件有所不同,決定了生態結構不同,這也導致了不同族群民俗民風和文化有較大差異。秦以前,游牧民族互不相屬,草原游牧民族政權統一,此后以長城為主的農牧民族間的互動是我國文明演變的主要旋律,此種演變過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主要是因農牧之間經濟、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利益等受到長城生態環境、民族構成以及經濟結構等影響,不同民族之間極易產生沖突,為了避免不同民族之間發生沖突,在國家政治戰略層面需要進行一定變通,發生沖突的主要標志便是長城,使農牧之間產生了矛盾,并且在此基礎上為農牧之間的有效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溝通平臺。
(二)發揮對內吸引和凝聚、對外融合的作用
我國歷史從公元前4世紀,農牧政權沖突較為激烈,其中修建長城可對有效緩解沖突,同時還可使社會持續有效穩定。在進行長城修建的過程中,對于草原民族而言,在南下期間受到交通的影響,所以長城逐漸為形成一種新型交通方式提供了有利條件,其中長城中的一些關堡以及相關設施,使北方交通體系得到全面完善。長城區域交通網逐漸形成,并且在對經濟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長城沿線產生了貿易市場,同時形成了物質集散中心地,從而長城成了聚合力量的中心,對內產生較強的凝聚力,對外發揮著橋梁作用。
四、“規矩”核心文化價值觀的集散地
(一)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重要過程
我國文明的發展經歷了部落、古城、王國以及現代文明,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打破了一定界限,比如文化、自然等,這在較大程度上可有效擴大交際范圍,并且也是不斷學會采用何種方法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和諧相處的過程,在此期間,不同時期產生的共識能夠體現不同時期的核心文化價值觀。
(二)文化傳統的沿襲
民族在進行融合發展期間與中華民族統一過程具有較高的同一性,中原在早期便有郡間置。在戰國時期,秦趙燕三國也進行了行政機構的有效設置,以此對邊防實施鞏固。秦帝國在義渠故地設置了三郡,西漢中央政府設置了職管,主要是兼管一些產品的交易。通過行政機構與游牧部落職官的設置,使北方地區出現了多種民族的融合居住。從客觀角度進行分析,能夠使農牧民族進行融合,其中此種融合具有更深層次。此外,唐代以長城南北為標志,構建了地域與政權,其中所構建的地域南北有一定差異,并且政權以族群為主,在逐步發展的過程中長城成了南北戰略要地。從國家治理角度分析,由于一些民族主要是以農業或者畜牧業為主,國家在對其管理期間采用了雙軌制實施管理,比如在農業民族中制定州、縣制度;在畜牧業民族區域設置不同等級官職,比如南北面官、屬國以及辦事大臣等,實行胡漢分治,也可以根據當地居民風俗習慣進行治理。長城不但是邊疆的防御邊界,而且還把不同文化相互連接與融合,也是跨文化融合與文明對話的重要橋梁,可大大提高區域思想意識,為經濟與文化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古代,長城區域中經濟、文化的發展有所不同,發展較快的便是中原經濟,是目前全國內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并且也為文化傳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所以通過修筑長城會體現出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差異,其中少數民族文化在發展期間會受到漢文明的影響,時至今日較多民族發展了古文化,比如《論語》《孝經》還有《禮記》木簡、帛書以及紙質的漢文經,其中漢文字被翻譯成民族文字,同時在長城地帶不同民族中有較為廣泛的流傳。同時,我國一些儒家思想在流傳中逐漸融入少數民族生活中,形成了一種民族習俗。此外,一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習俗在農耕文明中有較大體現,如服裝、坐具以及飲食等。
五、結束語
我國社會發展以來,文明建設主要是由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構成,中國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這對以長城為中心的民族融合意義重大。此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實體中,長城主要是社會治理理念、文化交流、人們思維方式等的綜合體現。人類文明包含文化價值、社會治理體系等,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人們處理行為中核心文化價值觀是其重要依據。文化遺產價值是不同子系統形成的價值體系,不同時代與民族文化價值體系具有一定的差別。在認知體系中,主要以科學與藝術為主導,并在技術的基礎上深入分析長城價值,“有形”長城是我國古代文化發展產物,是漢文明“對立”思維方式的物化表現,在多個領域中具有較高的價值。然而我國核心文化價值中,長城是文化價值體現的集散地,使農牧民族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有較好的體現,實質上這是漢文明思維變通的特點,這是我國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財富。
參考文獻:
[1]黃立平,傅惟光.認知歷史文化保護金代萬里長城[J].理論觀察,2019(08):137-139.
[2]李姝昱.董耀會:長城文化的歷史價值與新時代意義[N].光明日報,2018-11-10(004).
[3]任鳳珍,錢越.長城歷史文化傳承創新的當代價值——基于長城經濟文化帶的思考[J].河北地質大學學報,2017,40(02):135-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