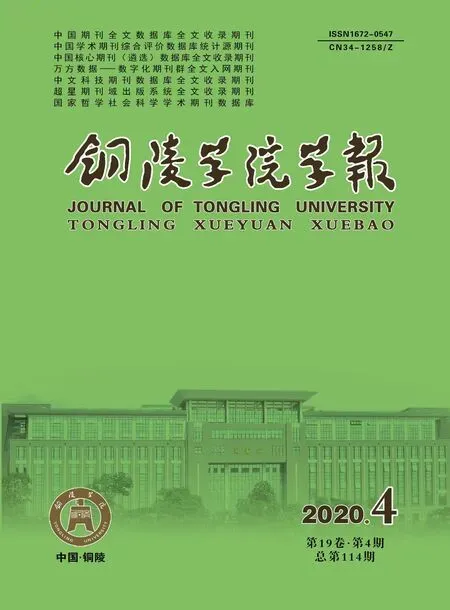基于人類價值的生態補償核算研究綜述
李志東 李冬敏
(合肥師范學院,安徽 合肥230601)
一、引言
生態系統服務總經濟價值于1985年提出,并建立了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分類框架[1](圖1),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成人類價值和非人類價值兩類。其人類價值是指生態資源為人類利用的價值,這實際上是將生態資源作為為人類服務的工具而存在的工具價值。其非人類價值是生態資源存在的本身價值,是它的內在價值,即生態系統中無論有無人類,生態資源仍然存在[2]。所以如果撇去人類價值而讓人類去評估生態資源的內在價值則沒有參照系,也就失去了評估的基礎。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人類價值就是評估生態系統對于人類來說它的總經濟價值。生態系統的非使用價值不產生現時的收益,無法納入到人類活動中去,也無法計算其當前時況的生態補償標準。在其使用價值中的直接使用價值是指這些生態資源可直接投入到生產中去的;間接使用價值是指雖未直接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未被記入成本的、但卻對生產過程產生影響的那些生態資源,如水文調節、植物授粉、氣候變化等;而選擇價值是對生態資源消費的時期做出選擇,即比較現在消費和未來消費哪個價值大,這是根據人類的效用而確定的。
基于生態系統的人類價值,生態補償的核算方法可從不同的視角分為按生態資源的要素價值核算、按生態治理的成本核算和按生態資源的效用核算。同時,在此基礎上,將生態資源的相對指標作為參照,衡量生態資源價值的方法也得到廣泛應用。

圖1 生態服務價值分類
二、基于生態資源要素價值核算方法
基于生態系統要素價值的補償核算,是將生態資源作為生產投入的要素之一,計算該要素在生產中的價值。然而在實際生產中,生態資源的投入量并不像原材料、勞動力那樣有明確的投入量的界定,所以其計算方法也不能直接地去計算生態資源的價值。通常用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計算模型和能值計算模型去計算生態資源要素的價值,從而核算生態補償標準。
(一)基于生態服務價值的生態補償核算

表1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核算類型
英國經濟學家Pearce于1989年發文研究如何利用市場機制來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并提出了該類方法計算生態補償標準。到1997年,Costanza和Daily的研究表明生態系統服務蘊含巨大的經濟價值[3]。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生態資源要素的成本不容忽視,生態補償是生態資源價值的體現。他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估研究推向研究前沿,成為生態補償核算一個重要里程碑。隨著生態補償實踐活動的開展和學者們對核算方法的研究,形成了三類生態服務價值評估的方法。分別是價值評估類、消費偏好類、和效益轉移類,其中最常用的是消費偏好類的條件價值法(詳見表1)。該方法是Hicks[4]提出,他將生態資源視為公共物品,根據公共物品供給改變,將生態資源的人類福利計量分為補償變差(CV)與等價變差(EV)的兩個指標。然后根據固定法設定消費者間接效用函數從而設定消費者在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的支出函數為(式1):

其中P為價格,Q為公共物品的供給量,U為效用水平,k為私人物品。
如果將消費者支出分為1和2兩個時期,那么,公共物品的補償變差(CV)為(式2):

等價變差為(EV)(式3):

P1為1時期私人物品價格,Q1為1時期公共物品供給量,L1為1時期消費者收入水平,U1為1時期效用水平;在時期2,對應的量分別為P2,Q2,L2和U2。
根據CV/EV與支付意愿/受償意愿之間的關系,可以評估生態服務系統價值,可在此生態服務系統價值的基礎上核算生態補償標準[5]。
(二)基于能值的生態補償核算
美國的系統生態學家H.T.Odum,提出了能值概念,并開創了一套全新的研究方法,這奠定了能值理論的基礎[6]。計算一個地區的能值狀態可從能值投入與能值產出兩端進行比較,當一個地區的能值投入小而能值產出多時,則這個地方的能值產出率高。那么該地在對外的商品交換中獲取了額外的能值;如果能值投入大而能值產出小,則該地能值產出率低,那么該地在對外的商品交換中,能值流失了。
該方法首先搜集投入該地生產的各能量要素,這些要素包括自然界能量和經過人類加工的能量,自然界能量包括日光能、風能、雨水的化學能和勢能、潮汐能、土壤流失能和化學能、河水流動能、自然資源能等,人類加工過的能量包括信息、技術、產品、勞動力等。再將這些能量根據能量轉換率轉換成太陽能值,其中信息、技術、產品、勞動力都根據不同的等級有相應的轉換系數。通過太陽能值可進一步計算該地的能值總量、能值自給率、能值交換率、能值流失量及能值使用強度等指標。最后將能值指標轉化為貨幣指標,可計算出能值貨幣比率與能值價值量。
在能值系列指標的基礎上核算生態補償標準,假設有生態資源相互影響的兩地,能值貨幣比率高或能值使用強度低的地域往往存在能值流失。再根據兩地的貿易情況,核算雙方生產資料貿易和消費品貿易的商品的能值,測算生態補償標準。能值法一般用于不同地區之間的生態補償,可將包含貿易聯系的兩地或多地納入到同一測算體系中,在總能值平衡的狀態下估算生態補償。
三、基于生態保護成本的生態補償核算方法
生態保護成本根據生態保護類型的不同,投入的生態保護設施的成本也各不相同。比如水資源保護需要投入的生態保護成本包括涵養水源發生的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水污染治理成本、水土保持成本、生態移民安置成本、林業建設成本及相關科研投入成本。這些發生的成本可視為開展不同項目建設的成本。此時生態保護的經濟成本可轉化為各項目建設成本的核算方法。在計算項目建設成本時,一要劃分資本性支出與收益性支出,收益性支出可進行費用化處理,按當年發生的數額直接計入當期成本;對于資本性支出,則要按一定的折現率在受益期內進行分攤。二要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
假設以項目的建設周期為n年,項目的運用的生命周期為m年,項目在投資建設期每年投入資金為Ci,在項目生命周期內每年的固定生態補償款為A,折現率為r,則可列出核算方程,見式(4)(5)。

則:

從機會成本方面而論,某地如果對生態保護進行投入,不僅放棄了用生態保護的投入發展其他產業的機會,也放棄了那些過度消耗生態資源產業的發展機會。人們一般將放棄的方案中最大的經濟收益,作為所選擇方案的機會成本[6]。
當某地放棄發展權時,會給當地政府、企業和居民帶來了發展權損失。那么機會成本就可分解為居民機會成本、企業機會成本和政府機會成本。
四、基于效用理論的生態補償核算
生態資源對于每個主體的效用是不同的。就目前的技術而言,生態資源是公共產品,還不能像普通商品一樣有著消費者個體消費的行為,則需要一個一般性的生態資源的價值計量方法[7]。
在生態補償中按照補償雙方是否處于同一生態資源區,可分為雙邊疊加生態補償和雙邊分離生態補償。雙邊疊加生態補償,是生態的消耗方和受償方處于同一地理范圍,雙邊分離生態補償是補償雙方處于相異地理范圍。在雙邊疊加的生態補償核算中,假設生態消耗方在沒有進行生態消耗情況下的收益為M0,在進行了生態消耗的情況下收益為M1,那么生態消耗方對生態資源可接受價格定小于M1-M0,這樣才愿意接受生態資源的價格,即他們愿意接受的生態補償的金額一定要小于M1-M0;而要計算受償方生態資源的價格則較為復雜,一般可采用受償方在沒有原來情況下的效用值(U0)與生態受損情況下的效用值之間的差額來衡量生態價值(U1),即為U0-U1。即受償方要求的補償金額為U0-U1。
在雙邊分離的生態補償中,生態保護方在保護生態系統價值所付出的成本C和為保護生態系統而喪失的機會成本OC,即為C+OC;而生態受益方從生態保護中的收益可表示為在對方進行生態保護時的收益(E0)與對方沒有進行生態保護時的收益(E1)的差表示,他對生態價值的心理預期價格一定要小于E0-E1。而在市場機制中,生態補償的雙方都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因此雙邊疊加的生態補償中,生態消耗方期望的生態補償價格是區間(0,M1-M0)與(U0-U1)中較小的值;而受償方期望的生態補償價格是區間(0,M1-M0)與(U0-U1)中較大的值。在雙邊分離生態補償中,生態消耗方的生態補償價格是區間(0,E0-E1)與(C+OC)中較小的值,而受償方的生態補償價格是區間(0,E0-E1)與(C+OC)中較大的值。生態補償的標準也將在此范圍內波動[8]。基于效用理論的生態補償適用于市場調節的補償機制,目前基于效用理論的生態補償還在進一步的研究中。
五、參照生態資源相對指標的生態補償核算
(一)基于生態足跡的生態補償核算法
由于在已有經濟核算體系中假定資源是可以被人造資本替代的,其核算價格不能反映自然資源的存量及再生狀況,其核算體系忽略了資源使用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生態足跡的計算經歷了從一維模型、到二維模型、到三維模型的發展過程[9]。

表2 生態足跡計算內容及其應用狀態
在二維模型中通過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算出生態盈余狀態,根據某地的生態盈余狀態確定生態補償標準。當某區域有生態赤字出現時,將生態赤字量換算成補償金額,向政府繳納生態補償款,生態盈余的地區則無需繳納生態補償款。
(二)基于脫鉤彈性的生態補償核算
學者Tapio建立的脫鉤彈性模型是應用廣的生態效率評價方法[10]。其計算公式為(見式6):

由于該公式是將直接將期初和期末的數據進行比較,難以反映“期間”的波動,有研究者將根據環境壓力和經濟增長之間的一致性,將“期間”分成若干“時段”,分別計算每個“時段”的脫鉤彈性,并根據每個時段的脫鉤指數(見式7),計算每個時段的生態補償,再綜合各時段的補償,計算總生態補償。

在公式中,EPj是“時段”末的環境壓力,EPi是“時段”初的環境壓力,EDJ是“時段”末的經濟發展,EDi是“時段”初的經濟發展,DIEP,ED是經濟發展與環境壓力的脫鉤指數。
在實際測算環境壓力時往往用環境污染、能源與資源消耗的指標,如污水排放量、固體廢物排放量、土壤流失量、各種廢棄排放量(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各種能源消費量、各種生態資源消費量等,經濟發展一般用GDP作為指標[11]。再根據Tapio對脫鉤狀態的分級,確定生態補償等級(見表3)。
基于脫鉤彈性的生態補償核算,一般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已發生的生態消耗進行補償的確認。在進行此種核算時對于處于衰退期的生態補償措施需要謹慎執行,因為生態補償往往會加重其衰退。
六、展望
當前生態補償標準核算是在將生態資源視為公共物品、將補償對象限于政府與政府之間或政府與居民之間的基礎上而建立的一套核算體系。因此,在理論上,生態補償標準不能從微觀上反應不同對象對于生態資源的評價;實踐上,在生態補償過程中會出現權力尋租、補償效率低下、補償款未用于生態資源恢復上等諸多現象。為此,一些學者提出生態補償應由宏觀向微觀轉變,補償標準的核算應從市場的角度出發,充分量化每個市場個體的生態資源效用以及生態資源的供求關系,建立一套生態補償標準核算體系。生態補償主要在市場個體之間進行,政府在補償過程中不占主導地位,政府只是從政策的角度規定對生態資源的要求。市場個體從各自的需求出發,選擇作為生態資源的供給者或是消耗者。生態補償的標準即相當于市場中的價格機制。所以生態補償的核算,將會從“成本——效用”的兩端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那么如何分別從企業成本和個人效用兩方面建立生態補償核算機制,既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又能夠體現公共產品的公共要求,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生態補償標準的核算,將是未來一段時期一個主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