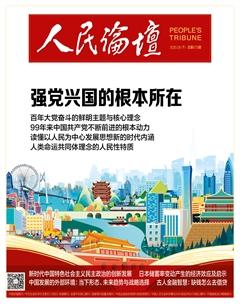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當下形態、未來趨勢與戰略選擇
王存剛

【關鍵詞】中國發展? 外部環境? 全球化? 國際體系? 國際安全? 國際輿論
【中圖分類號】D822? ? 【文獻標識碼】A
中國發展需要大體適宜的外部環境。而塑造和維護這種環境,需要因勢利導,積極作為。具體地說,就是要在正確認識外部環境的總體狀況、基本特點及演進趨勢的基礎上,做出恰當的戰略選擇并積極進行相關實踐。近年來,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的確發生了一些新變化,產生了一些新現象,呈現一些新特點,形成了一些新趨勢。限于篇幅,本文擬對全球化、國際體系、國際安全以及國際輿論等四個重要議題領域的當下形態與未來趨勢加以闡述,并據此探討中國的戰略選擇。
全球化進程:新逆流出現,總趨勢不會改變
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強大潮流。但在這一過程中,“逆全球化”現象屢有發生;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政府頻繁“退群”,被視為近年來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均呼吁應保持貿易開放狀態,但各國政府還是出臺了樣式不同、力度各異的貿易限制措施。權威報告顯示:從2020年初到5月中旬,超過85個國家和地區執行了針對醫療物資的共計156項出口限制措施,全球經貿體系開放性遭到新的損害。跨境貿易在全球商品產出中的占比繼續下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均是如此。國家中心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在某些國家重新抬頭,民粹主義進一步泛濫。由此,新的“逆全球化”現象形成,人們對全球化進程的悲觀態度進一步加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會創造一個不再那么開放、繁榮與自由的世界,“我們將看到當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進一步消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賴特(Robin Niblett)預計,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壓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從目前情況看,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嚴重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的確會讓各國政府在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更加關注國內事務,期盼控制住疫情、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社會心理也會對國家—社會關系的既有平衡產生重大沖擊,從而使得“強政府”時代加速回歸。在全球層面上,以新自由主義為基底的國際秩序坍塌也已不可避免。但鑒于經由經濟全球化長期發展而形成的人類不同群體空前相互依賴的總體狀況,因此不能斷言全球化將出現明顯倒退,更不應當對全球化的長期前景持悲觀態度。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特別是在全球范圍的快速蔓延表明,全球化已遠遠走在當今世人觀念的前面。與此相關聯,建立在既有認知和理念基礎上的全球治理體系,確已不能滿足全球化發展的新需要。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平息后,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必將會受到國際社會更大的關注,并在各國政府的對外事務議程中發生較大前移;各國圍繞這一改革的爭論、交鋒甚至對抗難以避免,從而為國際關系增添新的不確定因素,并對國際體系轉型產生影響。
國際體系:大國關系出現新起伏,金磚國家的重要性顯著衰減,國際格局前景難料
對一國發展外部環境的分析,必然涉及對國際體系的分析。而在國際體系中,大國關系的現狀及走向無疑占據核心地位。當下和今后一個時期,大國關系預計呈現以下特點和趨勢。
中美之間全方位、多領域的對抗烈度可能繼續上升。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中美關系一路震蕩下行,2018年開打的貿易戰、科技戰進一步加劇了下行趨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美關系大體呈現“小幅高開”“大幅低走”態勢。起初,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政府抗疫措施表示贊許。然而,隨著疫情在美國本土暴發和蔓延,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態的急劇變化,特朗普政府對華態度驟變,政策大幅調整,一種“利用一切機會對中國進行攻擊抹黑”的政治病毒在美國國內快速擴散。一些機構、媒體和政治人物無視基本事實,肆意編造針對中國的謊言,積極謀劃針對中國的陰謀。美國參議院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向該黨各競選機構發送長篇備忘錄,鼓動它們“積極攻擊中國”防疫舉措,并給出“中國掩蓋真相導致病毒蔓延”等三大攻擊路線,其核心內容是:只要提到疫情,就攻擊中國。5月下旬,白宮發布最新一份《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稱:自1979年與中國建交以來,美方一直希望通過接觸交往,能使中國“經濟開放”和“政治開放”,然而40多年后的今天,美國并未如愿。該文件重申了美國對華兩大戰略目標,并就如何落實做了詳細闡述。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演講中重申了上述論調。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后,美國在南海、臺灣、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一系列問題上頻頻出手、惡意畢露。種種跡象顯示,美國一些政治勢力試圖綁架中美關系,將這一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推向全方位、多領域的“新冷戰”。這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如得不到有效制止,不僅會葬送兩國多年積累的合作成果,也將損害美國自身的發展,并危及世界的穩定與繁榮。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美國東部時間8月24日下午正式提名現任總統特朗普為202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如果特朗普連任成功,他會有路徑依賴,不排除其將采取比之前更為非理性的對華政策;如果民主黨的拜登勝選,根據歷史經驗和目前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其上臺執政的最初階段,也不大可能在對華政策方面有重大調整。而這一切都將對全球大國關系框架構成新挑戰,并為亞太地區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俄美關系略有升溫,但仍未擺脫“死循環”。受彼此結構性深層矛盾以及美國國內右翼反俄勢力的影響,近年來俄美關系總體處于低谷狀態,彼此間明爭暗斗、齟齬不斷。新冠肺炎疫情在歐美國家集中暴發后,俄美關系出現某些緩和跡象,普京與特朗普一度互動頻繁,并就防疫合作、穩定全球能源市場等議題達成共識。然而,兩國關系中存在的痼疾依然不時發作。最近幾個月來,美國與中東歐、北歐盟國多次進行具有明顯指向性的聯合軍事訓練,美國空軍戰略轟炸機多次飛抵靠近俄羅斯領空的黑海、波羅的海和北極地區上空。美俄兩國還就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問題發生正面沖突,并在敘利亞問題、伊朗核問題上互有攻防。俄美雙邊關系之所以未能走出長期存在的“死循環”,根子還在于兩國對世界政治的前景以及彼此地位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期冀重振大國雄風的俄羅斯試圖構建一個“后西方”“后美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美國只是幾個主要大國之一,而非世界唯一霸主;美國必須承認俄羅斯的全球大國地位和勢力范圍,并徹底改變對俄長期實施的圍堵和遏制戰略。然而,目前還看不到美國有如此意愿以及由此展現的善意。美俄關系的持續“死循環”,勢必對俄歐關系、中俄關系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跨大西洋關系繼續波動下行,歐洲地緣形勢的未來走向值得關注。跨大西洋關系的形成與演化,既與歷史、文化和價值觀有關,更是地緣政治、經濟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利益驅動所致。在冷戰結束前,盡管跨大西洋關系中有摩擦、有爭吵,甚至有對抗、有背叛,但因蘇聯這一強大而危險的共同對手的存在,彼此關系總體上能夠正常運行。蘇聯解體后,大西洋兩岸國家的共同對手消失了,彼此關系的基石開始松動;而美國愈發明顯的輕慢態度,歐盟成立、擴容及一度良好的發展勢頭,加之俄羅斯持續采取的分化舉措……跨大西洋關系逐漸下行的態勢日益明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特朗普政府拋棄歐洲新老盟友的自私自利行為,顯著擴大了跨大西洋關系中已有的裂痕。這在對待世界衛生組織(WHO)問題上體現得最為鮮明。在特朗普高調宣布斷供WHO并終止與其合作關系后,歐盟國家與他拉開了距離。德國政府公開表示對特朗普此舉的失望,認為這將重創全球公共衛生體系。意大利政府官員強調如今需要的是經過改革后更加強有力的WHO,而不是弱化它。即使一貫給人“緊跟美國”印象的英國政府,此次也未亦步亦趨,聲明沒有從WHO撤資的計劃。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試圖擴大七國集團(G7)搞反華聯盟的舉動,也未得到顧慮重重的歐洲盟國的積極回應。當然,擁有相同價值觀并在現階段仍存在諸多重大共同利益的跨大西洋關系,也不會在一朝一夕之間就發生重大斷裂進而一拍兩散、形同陌路,彼此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仍有可能采取集體行動。總之,未來的跨大西洋關系雖然仍會不時有合作,但持續下行的總體態勢不會改變。而這一態勢對中歐、俄歐關系以及中美歐、中俄歐三邊互動會產生怎樣影響,都值得高度關注。
中歐關系整體緩慢上行,但隱患時有發作。近代以來,歐洲始終是關系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關鍵地區之一。在當今世界,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盡管存在諸多差異,但也確實存在諸多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有著相同或近似的看法。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舉行的記者會上指出:“中歐關系歷經國際風云變幻,總體保持合作的主基調,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中歐雙方總體而言有著較為積極的互動。習近平主席與歐盟及多個成員國領導人展開“云外交”“電話外交”,其中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通話就有三次。中國向意大利、塞爾維亞等國提供了大量抗疫援助,得到受援助國及歐盟的歡迎和贊賞。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以及國家治理方式的差異,還是對中歐合作產生了多方面的消極影響。比如,一些歐洲政治精英、主流媒體公開質疑中國援歐抗疫行動的目的,認為其具有地緣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考量。個別歐洲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更是漸行漸遠。比如,作為第一個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歐洲國家,瑞典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就出現了不少不利于中瑞關系良好發展的現象:部分媒體和政治人物將疫情政治化、對中國污名化;《瑞典日報》將疫情歸咎于中國的政治制度,《今日工業報》甚至宣稱“新冠病毒是中國制造的”;哥特堡(Goteborg)、林雪平(Linkoping)和厄勒布魯爾(Rebro)等瑞典中心城市相繼宣布與上海、廣州、西安等中國中心城市中斷友好城市關系;該國最后一家孔子學院在疫情期間被關閉,瑞典也由此成為第一個徹底關閉孔子學院的歐洲國家。中歐關系中既有隱患的新發作,不僅對中歐關系未來發展造成消極影響,也將給中國整體外交布局調整帶來新的困難。
中俄戰略互信再次經受考驗,雙邊關系將進一步加強。自俄羅斯1991年獨立以來,經過雙方共同努力,不斷經受考驗的中俄關系持續在高水平上運行。習近平主席曾稱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習近平主席同普京總統多次通話,在全球主要大國領導人中保持了最為緊密的溝通。俄羅斯是第一個派遣防疫專家代表團來華的國家,中國則是向俄羅斯提供抗疫物資支持最有力的國家。在全球經濟整體低迷的形勢下,中俄雙邊貿易逆勢增長。雙方第一季度貿易額增長3.4%,全年有望實現2000億美元目標。面對個別國家的無理攻擊、抹黑言論和挑撥行徑,中俄相互支持,彼此仗義執言,成為在全球肆虐的“政治病毒”攻不破的堡壘,體現了中俄高水平戰略協作的新氣象。可以相信,此次中俄共同抗疫的經歷將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疫后中俄關系提速升級的強大動力。
中國與印度的關系出現新問題,金磚國家的作用顯著衰減。中印關系既是一種周邊關系,也是一對新興大國關系,對地緣政治、地區安全和全球格局均具有重要影響。近年來,中印關系在兩國領導人的強力引領下總體向好,但近期在兩國邊境地區發生的流血沖突給雙邊關系的未來發展蒙上了濃重陰影。而個別域外大國日益公開的挑撥行為,將使得中印關系的未來具有更大不確定性。與此同時,一度為各方看好的印度經濟近期嚴重下滑,工業生產和服務業增長均處于十年來最低水平,商業信心指數則呈自由落體狀態,惠譽、穆迪等多家國際著名評級機構先后下調印度的評級等級。另一個新興大國巴西近年來飽受國家高財政赤字、政府高負債和社會高失業率等多種因素的困擾,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又遭受重創,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前景短期內不容樂觀。因烏克蘭問題而長期遭受西方制裁之苦的俄羅斯,近期又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低油價的雙重打擊,未來經濟發展將面臨更多難題。本來就因經濟發展成色不足而遭受質疑的南非,今年以來GDP正以“驚人的規模和速度萎縮”,固定資本占GDP的比率持續下降,企業債務超過GDP的100%,失業率節節攀升。驟然黯淡的經濟發展前景,自然對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產生嚴重消極影響,并導致世界力量走向新平衡出現不確定性。
總而言之,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無論是傳統大國間的關系,還是傳統大國與新興大國的關系,以及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對抗性、不穩定性的一面將有可能不斷強化,國際格局的未來難以預料。
國際安全領域:全球戰略穩定遭受新的嚴重損害,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題排序發生重要變化
全球戰略穩定遭受新的嚴重損害源自美國一系列不負責任的行為。今年5月2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鑒于俄羅斯未能遵守條約,美國將退出《開放天空條約》(Treaty on Open Skies)。俄羅斯對美國此舉提出強烈批評,認為退約理由站不住腳,事實上是美國自己違反了該條約。美國退約舉動也遭到其歐洲盟友的廣泛質疑。德國、比利時、西班牙、意大利、盧森堡、荷蘭、芬蘭、法國、捷克和瑞典等10國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遺憾。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等國多次向美國表示希望其能留在條約中。但從目前情況看,美國退出《開放天空條約》已不可逆轉。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還公開表示,正在考慮是否要延長美俄之間另一個重要軍控條約——即將于2021年到期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這無疑是對全球軍控體系的又一個沉重打擊,將對全球戰略穩定構成新的重大威脅。更令人不安的是,今年5月中旬舉行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就美國重啟核試驗問題進行了討論。美國國防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對外宣稱:一旦特朗普總統下達命令,美方就可以在“數月內”安排一次實彈核試驗。中國權威軍控專家認為,“美國如重啟核試驗,產生的連鎖效應會比以前特朗普退出的所有條約加一塊還要大,等于把一個巨大的魔獸放了出來”。
國際安全領域的一個新現象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議題排序發生重要變化,相關國際合作進一步加強。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和社會后果,使得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受到各國前所未有的重視。英國《金融時報》(FT)網站今年5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令長期占據國家安全支出首要地位的國防工業“退居二線”,各國軍費有可能因此大幅縮減。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性、擴展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依賴性,也使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進一步加強。這在6月4日舉行的全球疫苗視頻峰會上已見端倪。此次峰會有來自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包括32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世衛組織負責人和12個私營機構及民間團體領導人,為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籌集了88億美元的資金。各國在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積極合作,又將對彼此在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產生積極影響。
國際輿論場:非理性言論甚囂塵上,圍繞社會制度優劣的博弈重新浮現并可能激化
國際輿論環境是國家發展外部環境的重要一環。由于歷史原因,以英文國際媒體為代表的歐美主流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這些歐美主流媒體背后又總是閃現著國際壟斷資本和歐美主要大國、活躍政黨的身影。有觀察者認為,“這些媒體都是操控在同一批人手里,或者說操縱在同一類人手里”。而這“一批人”或“一類人”基于自己的價值、信仰特別是狹隘利益,對快速成長的社會主義中國通常并不友善。僅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國際輿論場上就出現了大量針對中國的污名化言論,諸如“中國病毒源頭論”“中國不透明論”“中國轉移責任論”“中國問責論”乃至“中國崩潰論”,林林總總,令人錯愕。某些反華政治勢力或團體甚至利用遠程控制的“機器人賬號”,協同轉發海量針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假消息,致使國外公眾對中國產生了新偏見、新誤解與新誤判。中國所面臨的外部輿論壓力也因此陡然增加。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制度競爭話題再度浮現并有可能進一步發酵。冷戰結束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社會制度競爭話題在國際舞臺上通常不會被公開提及,但其從未真正消失過,而是以隱蔽形式存在著,采取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抱持不同信仰和價值的政治精英,對此心照不宣并通常暗中較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既是對不同國家治理模式、治理能力的檢驗,也是對不同社會制度優越性的展示。社會主義中國的出色表現和資本主義制度領頭羊美國的狼狽不堪,使得社會制度競爭話題再次浮現。《華盛頓郵報》發文稱:抗疫考驗著東西方不同模式。法國政治學者布魯諾·吉諾(Bruno Gino)撰文指出,現實可能會令一些所謂的自由世界媒體不爽,但他們需要習慣這一點。中國做到了別的國家從未做到之事:通過國家與社會的大規模動員戰勝了一種流行病。吉諾甚至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見證西方體制的垮臺。知名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在其社評中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得到迅速遏制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為其他國家樹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樣”。面對這種不無尷尬的情勢,歐美國家的各界精英自然心有不甘。他們中的一些人或公開詆毀中國,或為自己所擁戴的體制進行辯解。3月下旬,美國駐波蘭大使喬琪特·莫斯巴赫(Georgette Mosbacher)多次在推特上發文,完全否認中國抗疫成果,公開詆毀中國現行制度。同月底,以西方制度衛道士著稱于世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雖然承認中國抗疫的成功和美國抗疫的失敗,但明確拒絕以體制論高下的觀點。他延續自己的既有思路,將中美抗疫結果差異拉到所謂的“國家能力”議題上。4月12日,日本《讀賣新聞》發表評論文章,公然斷定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是造成新冠肺炎疫情擴散的“人禍”。可以預見,重新浮現的社會制度競爭議題肯定不會很快消失。面對優越性益發凸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將為捍衛其制度的合理性而竭盡全力,在對華輿論戰方面可能會采取一些出人意料之舉。
就中國方面而言,最近幾年來,主流媒體特別是部分英文媒體的國際影響力確實顯著上升。比如,今年4月30日,新華社發布一則動畫視頻,以兵馬俑“VS”自由女神的形式駁斥美方對中國的抹黑行為。該視頻一經發布,立刻引起國外網民和歐美媒體的注意,短短1分半鐘的動畫,就收獲了150多萬次觀看、1.5萬次轉推、2.8萬次點贊。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也都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它們雖然都將該視頻稱為中國的“政治宣傳”,但也承認其中自由女神的話語有跡可循。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的國際影響力與歐美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部分歐美媒體的荒腔走板、狹隘偏私也給中國公眾好好地上了一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在國際輿論場上持續發出強有力的中國聲音,爭獲更大國際話語權,塑造更好中國形象,以為中國發展創造更為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對中國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來說,仍是一項十分艱巨但又不得不努力做好的大事和難事。
在正確運用統籌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的基礎上,全力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當今世界已經并將繼續發生多方面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某些特點,改變了某些態勢,加劇了某些趨勢。無論如何,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對中國而言,上述新變化、新態勢、新趨勢恰好與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在時間段上重合,挑戰直接而嚴峻,如何有效應對十分重要。我們應當在正確運用統籌思維、歷史思維、辯證思維、底線思維的基礎上,努力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繼續強化“四個自信”。“四個自信”是中國悠久的歷史特別是波瀾壯闊的現當代史的有效積淀,是改革開放輝煌成就的科學結晶,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克服萬千困難、砥礪前行的強大精神動力。要充分利用好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激發出來且廣受肯定的民心、士氣和強大凝聚力,努力把“四個自信”轉化為應對外部環境的新變化與新挑戰、推進國家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的強大動力。
二是努力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本態勢。解決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內外挑戰,都在于中國自身的發展,其中關鍵是要保持經濟平穩、持續、健康的發展。面對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發的新產業革命,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劇烈的沖擊,中國經濟應當在穩住陣腳的基礎上積極進取,努力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與此同時,還要穩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治理體系,促進體制機制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設的轉化與融合,激發和凝聚全社會的創造力。
三是更加積極地推動全球化向更為包容、普惠和平衡的方向發展。作為一種歷史必然趨勢的全球化猶如百川匯成、包容宏闊的大海,不可能再退縮到大小不一、相互隔絕的湖泊。拒絕全球化,為新的“逆全球化”現象過分焦慮,均是歷史短視;重拾國家中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舊幟,默認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泛濫,注定沒有前途。作為一個在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受益頗豐的國家,中國應當繼續全力推進全球化的發展,堅決反對各種“逆全球化”的政策、行為和思潮,努力維持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總體穩定;繼續大力弘揚多邊主義精神,更加有力地支持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各種多邊機制,更加積極地構建新的具有包容性、普惠性、平衡性的多邊治理機制,以有力提升全球治理的績效,推進全球化穩步、健康、持續地發展。
四是大力穩定國際體系特別是國際關系總體格局。首先是穩定大國關系總體格局,特別是竭力遏止中美關系持續下行勢頭。為此,既要在涉及自身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又要注意對美反擊、反制的節奏、分寸和著力點,同時持續弘揚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理念,以占據雙邊關系的道義制高點。其次是要進一步加強與俄羅斯和歐盟核心國家的關系。既要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展不斷增添新動力,又要通過不同方式逐漸消除中俄關系中的個別斷點和中歐關系中的“信任赤字”。再次是進一步鞏固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并把東北亞、東南亞放在周邊外交總體布局中更為重要的位置,以次區域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有力推進全區域周邊命運共同體建設。最后是進一步提升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大國關系的質量,努力打造內涵一致、形式各異的雙邊命運共同體,夯實中國總體外交的基礎。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山東省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專項重點課題“中國共產黨外交領導力研究”(課題編號:20AWTJ02-19)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Stephen M. Walt, “A World Less Open, Prosperous, and Free”,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②Robin Niblett,“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③周丕啟:《大戰略評估:戰略環境分析與判斷》,北京:時事出版社,2019年。
④袁鵬:《新冠肺炎疫情與百年變局》,《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5期。
⑤孫吉勝:《新冠肺炎疫情與全球治理變革》,《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5期。
⑥“How the World Will Look Like After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責編/周小梨? ? 美編/陳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