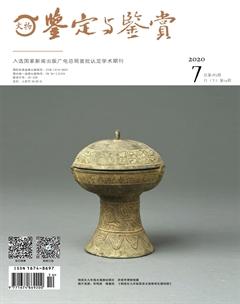對涇縣日軍侵皖鐵證武運旗的溯源探究及史實印證
徐偉川


摘 要:在安徽省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有一面日本國旗,展出至今,通過文物說明只知它是“新四軍在蔣家河口伏擊戰中繳獲的戰利品,是女戰士諸曉和生前的珍藏”,文物說明內容過于單薄,讓觀眾難有記憶。文章以蔣家河口伏擊戰為切入點,對此旗相關信息進行梳理完善,通過呈現其背后的故事,讓更多人勿忘歷史,砥礪前行。
關鍵詞:新四軍軍部舊址;武運旗;蔣家河口伏擊戰;侵皖鐵證;敵后抗日第一仗
在安徽省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有一面日本國旗(圖1)讓筆者印象極為深刻。略遺憾的是,從展出至今,該旗的名稱、作用、來源背景、旗主身份等重要信息均不完善,對被殲日軍的累累惡行和蔣家河口戰斗的深遠意義也鮮少提及。本文嘗試以蔣家河口伏擊戰為切入點,對此旗相關信息進行梳理完善,并將考證依據總結如下。
這不是一面普通的日本國旗,它是新四軍女戰士諸曉和生前的珍藏,也是新四軍成立后在首次對日作戰—蔣家河口伏擊戰中繳獲的戰利品。據諸曉和生前介紹,她本人并未參加蔣家河口戰役,是1938年10月,新四軍成立一周年之際,安徽省涇縣云嶺的新四軍軍部大禮堂曾舉辦過一場繳獲日寇勝利品的展覽,并允許戰士們在展覽結束后從中挑選一件留作紀念,于是她就選了這面旗子,并一直留在身邊。
由于長期折疊保存,在長84厘米、寬68厘米的絲綢旗面上留下對稱的血漬和污跡。旗面右側從上至下寫有“贈加藤茂君、加藤博久”字樣,旗面正中為紅色太陽徽,環繞太陽徽的空隙處密密麻麻呈放射狀簽有159名參戰官兵的名字,其正上方自右向左橫寫“祈武運長久”五個大字。這種寫有“武運長久”字樣的日本國旗被稱為武運旗,日本人堅信此旗在戰場上有躲避槍彈之效,能保佑持有者武運昌盛、健康平安。日本士兵出征時,通常會將其當成護身符貼身攜帶。
值得一提的是,“武運”一詞并非源于日本。早在中國南北朝時期(420—589年),文學家謝朓在《酬德賦》中有云:“奉武運之方昌,睹休風之未淑。”可見“武運”屬于漢語詞匯,后被日本大量援引,用以代指武士的命運。當時日本武士相信每個人都有武運,甚至認為武運大小能影響人在戰場上的生死存亡,如果活下來則說明其武運還在,如果戰死則說明武運不佳或武運已盡。因此,武士出征時親人都會說一句“祝武運長久”。后來這句話逐漸成為一種日本禮儀被保留下來,即使西南戰爭結束后武士階級被徹底廢除,這句話依然和日本軍人聯系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旗面右側上下方均有一個金色三角形的硬質包角,通常是起加固作用,在懸掛時可減少綁扎繩對旗子的磨損。此旗若只限于貼身攜帶,硬質包角則顯多余,所以推測它應作為指揮旗,曾懸掛于日軍步槍的刺刀之上。據史料記載,侵華戰爭期間,日軍隊伍里掛旗士兵的職務至少是班長以上,且多為有經驗的老兵,主要負責指揮小團隊作戰,相當于戰場指揮官。掛在刺刀上的國旗也不全然是身份象征,更多的是用作指揮。戰場上,我軍首要的狙擊目標就是這類掛旗士兵,一旦掛旗士兵被擊斃或失去指揮能力,就會由替補指揮兵立即頂上,并迅速用隨身攜帶的武運旗代替國旗,指揮戰斗。因此,這面旗的旗主加藤茂君與加藤博久的身份應當是日軍隊伍里的替補指揮兵。
如今,這面武運旗已成為日軍侵皖的鐵證,它不僅記載了一段血腥罪惡的歷史,也勾起所有江淮兒女關于抗日戰爭的記憶。1937年8月,正是在這一面面武運旗的引導下,日軍兵分四路,大舉入侵安徽。從此,江淮大地田園化作焦土,村莊變為廢墟,民眾深陷苦難和屈辱的深淵里。然而,日軍的殘酷暴行和血腥屠殺并未讓皖人就此屈服,反而在槍林彈雨中高高舉起“保衛中國、保衛家鄉”的旗幟,軍民團結一心,開始奮起抵抗。
1938年5月,抗戰形勢已發展到非常緊張的階段,上海、南京、杭州、蕪湖相繼失陷。日軍從蕪湖出發,一路攻占含山、巢湖、合肥等地。與此同時,新四軍第四支隊抵達皖中,他們一邊宣傳動員群眾抗日,一邊偵察敵情,發現位于巢湖東南的蔣家河口是日軍擾民的一個主要區域,日軍自4月底占領巢湖縣城后,為了補充給養,幾乎每日都派幾十名日軍到蔣家河口一帶燒殺搶掠,從未受到襲擊,所以氣焰極其囂張,戒備極其松懈。由于蔣家河口一帶蘆葦茂密,河道縱橫復雜,四支隊經過一系列的周密偵查和充分準備后,決定在此設伏,痛擊日軍。5月12日上午,幾十名日軍乘船到達蔣家河口后,一上岸就被埋伏在此的新四軍用槍和手榴彈打了個措手不及,最后我軍在無一傷亡的情況下,將這股日軍全部殲滅,并繳獲10余支“三八”步槍,1支手槍,少許彈藥及軍用品,以及這面日軍武運旗。這面武運旗以戰利品的形式,讓我們見證了新四軍抗日第一仗的完全勝利。
蔣家河口伏擊戰由新四軍第四支隊打響是不爭的事實,但被殲日軍屬于哪只部隊一直未考證清楚,直到最近才在東京1975年出版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一書上找到依據。被殲日軍屬于日軍巢縣守備隊,這支守備隊隸屬于侵華日軍坂井德太郎少將指揮的第六師團坂井支隊。而第六師團是當年首先進攻南京的六個師團之一,曾經參加過南京大屠殺,所以蔣家河口一戰殲滅的應是曾經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軍。
蔣家河口伏擊戰打響了新四軍敵后抗日的第一仗,第一勝仗,毋庸置疑,有多份歷史檔案可以佐證。第一份是1938年5月13日由新四軍第四支隊發出的《抗戰支隊在江北蔣家河口殺敵》的捷電(圖2),電文稱“五月十三日抗戰支隊捷電:十二日午我九團之一部,阻擊巢湖南岸蔣家河口附近登陸之敵,當斃、傷敵六十余人,繳槍二十余支,敵旗一面,彈藥及軍用品一部,殘敵狼狽登船逸去,我無傷亡。”這份捷電現存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第二份是1938年5月14日新四軍駐漢辦事處錢之光給國民政府軍令部的電文:“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隊阻擊巢湖南岸蔣家河口附近登陸之敵,當斃、傷敵六十余人,繳槍二十余支,敵旗一面,彈藥及軍用品一部,殘敵狼狽登船逸去,我無傷亡。”這份電文現存于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第三份是193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主辦的《新華日報》刊登的蔣家河口伏擊戰勝利的消息:“我新編第四軍第四支隊:十二日午,我第四支隊阻擊巢湖南岸蔣家河口附近登陸之敵,當斃、傷敵六十余人,繳槍二十余支,敵旗一面,彈藥及軍用品一部,殘敵狼狽登船逸去,我無傷亡。”第四份是蔣介石給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和副軍長項英發去的嘉勉電文:“葉、項軍長吾兄:A電悉。貴軍四支隊蔣家河口出奇挫敵,殊堪嘉慰。希飭繼續努力為要。”這份電文現存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另外,1939年元旦,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新四軍軍部召開的新年慶祝大會上做的題為《本軍抗敵一年來的經驗與教訓》的報告,其中也明確提到“江北部隊到達指定作戰地區之時,正是敵人向合肥進攻,企圖在巢湖東岸渡過西岸,在蔣家河口上,開始本軍第一次戰斗。戰斗結束,把巢湖登陸敵人完全擊潰,繳獲了11支槍,一面日本旗子,這是本軍在江北作戰的第一次勝利。”后來由新四軍參謀處編寫的《新四軍的前身及其組成與發展經過概況》一書中,再次將新四軍第四支隊蔣家河口伏擊日軍的戰斗稱為“開江北第一次的勝利”。
當新四軍老戰士蔣復強同志把妻子諸曉和珍藏多年的出征旗交給博物館收藏時,老人深情地說:“我捧得動這面旗子,可我捧不動這段歷史,這是一個民族的苦難和血淚吶。”是的,歲月可以把青絲染成白發,可是誰又能洗去一個民族在心靈上的創傷呢。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透過這面日軍侵華武運旗,我們仍需充分汲取那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為開創和平未來獲得更多的智慧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