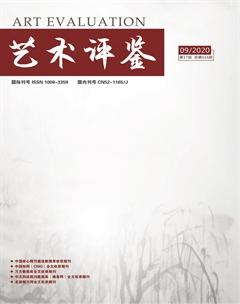摹仿與超越:翻改電影《誤殺》的藝術成就分析
馮藝
摘要:國產電影《誤殺》作為一部以現實主義為題材的懸疑敘事片,是對印度高分電影《誤殺瞞天記》的本土化翻改,堪稱中國電影史上口碑最高、翻拍最成功的華語影片之一。在模仿原作的懸疑敘事鏈下,以創新手法糅合多部外國經典電影的閃光點,運用多種蒙太奇增加多個情節反轉與懸念設置激化故事矛盾,強化華語觀眾的視聽感受與情感共鳴,通過對人性的豐富呈現引發深度思考,實現對原作電影的成功摹仿與超越。
關鍵詞:誤殺 ?藝術成就 ?本土化翻改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17-0153-04
原作《誤殺瞞天記》為印度犯罪懸疑高分電影,故事主題以親情、性別、等級階層、道德與倫理為中心,取景印度本土,貫穿本土特色樂舞,在真實再現印度風土人情的同時展現了其多元化的特點。該片除了劇作內容題材本身精彩、藝術表現手法精湛之外,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其因貼近社會現實內核而彰顯出的道德教化與啟示作用。本片講述了生活在印度小鎮中平凡和樂的一家四口,在收養的大女兒安玖參加野營歸來,被同行的警察局局長兒子薩姆偷拍洗澡并意圖借此威脅強奸時,安玖因想毀滅偷拍證據并營救被要挾的母親而錯手殺死了薩姆。只讀到四年級就輟學卻熱愛觀影的父親維杰為守護家人,處理薩姆尸體后,用從偵探懸疑類電影里學來的反偵察手法,結合蒙太奇與家人串口供,制造不在場證據與警察“斗智斗勇”,最后成功瞞天過海的故事。而國產版《誤殺》基于原作的故事鏈,與中國大環境下的社會現實相融合,在劇情、手法、內涵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編、深化與創新,力求把中國傳統精神中對家庭的守護、故土的眷戀等優良傳統精神傳遞出去。
一、基于原作《誤殺瞞天記》的翻改敘事成就
《誤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翻拍片,而是在保留原作特征與主題精神不變的基礎上進行的本土化翻改,其對事件、人物等內容進行了大幅度本土適應性調整,增強故事懸念與敘事節奏,激化矛盾沖突,深化主題內涵,使影片劇情更為豐滿緊湊,“本土化”元素的使用讓文化實現跨域轉換的同時更能引發中國觀眾的審美心理與共情能力,實現本片對現實主義深思與批判的功能。
(一)基于原作的本土化改造
1.故事情節加峻
《誤殺》將原作的故事背景從印度“搬”到有“架空”意味的“泰國唐人街”,雖是在泰國,但主角一家在吃飯場景中就強調“我們都是中國人”,講述的是實實在在的中國人、中國魂故事。除了故事背景的搬遷,作為人物主角的父親李維杰也遭遇了道德、生活、行為、階層的連續降維,從本土居民身份轉為自小便因經歷暴亂失去雙親的孤兒;受害大女兒由收養改為親生;主角一家從中產階層改為低收入僑民,拉大對立雙方階層差距。此外,編劇還把原作劇情中的大女兒被偷拍威脅改成更引人憤懣的下藥迷奸并威脅,深化血海深仇的矛盾與道德沖擊;把“聽經”替換成更貼近中國人口味的激烈、緊張的“觀看泰拳打斗比賽”,增強視聽感官效果;把施害者被直接打死改編成因“吞舌”現象造成假死被埋,再因主角的見死不救導致真正的窒息而死,增設懸念的同時,也使劇情更符合《誤殺》影片之冠名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開頭較原作增添了女局長的破案情節,其犀利的手段與極其機敏的頭腦為后面與主角斗智斗勇做了鋪墊,另外在察覺真相時,設置了一段女局長翻查主角觀影記錄,從懸疑類電影中見識到主角的作案手法,找到破案苗頭的情節,與原作中的女局長“突然領悟”相比,更符合客觀事實與邏輯。且結局也并沒有照本宣科照搬主角成功瞞天過海,而是增加了群眾暴亂的場面和主角瞞天過海后因對人民深感愧疚與對后代教育深刻反思而選擇了自首道歉的環節,這恰恰也符合了中華傳統優良道德精神,呈現不一樣的價值觀念,實現“本土化改編”。本片時長較于原作的163分鐘直接縮減到112分鐘,省去原作略顯冗長且重點不突出的故事鋪墊,《誤殺》幾乎從第20分鐘就進入了敘事重點,明顯提高了敘事效率,加上故事情節的加峻,整部影片較原作更具懸疑片特有的緊張、刺激與流暢感。
2.羊的符號意象運用
羊作為一種符號,不論是在影視作品中,還是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具有種種復雜豐富的含義①。影片《誤殺》中羊的多次出現引起了觀眾的普遍注意,其豐富的象征內涵與外延運用可謂是本次改編的一大特色亮點。羊在電影里一共出現了四次,第一次是作為“見證者”,在李維杰(主角)于湖邊沉車時出現,見證了棄車沉湖的全過程,畫面使用慢鏡頭在羊的眼睛與李維杰緊張的表情中來回切換,直直凝視著李維杰消滅證據時內心的恐懼與不安。第二次是作為“替罪者”,西方基督教《圣經》中就有“替罪羊”的說法,中國從古至今也有很多人用“替罪羊”一詞暗喻蒙冤替人承受罪孽的人或弱者②。在惡警桑坤把本應在李維杰身上發泄的憤怒,轉移到一旁的山羊,羊被桑坤一槍打死時,其就作為第一次“替罪羊”出現了,而這只無辜死去的山羊尸體在掘墓現場代替素察(被誤殺的施害者)被挖掘出來,則再一次成為了替罪者。第三次是作為“審判者”,在臨近結局,李維杰成功瞞天過海卻間接引發社會暴亂,以及小女兒造假成績時,本性善良的他深感煎熬與懺悔,為制止暴亂、挽救家庭教育、平復內心罪惡感,他選擇承擔罪孽,決定自首。自首前李維杰最后一次前往佛寺朝拜,羊以“審判者”的身份,迎著金光闖入李維杰的視線,光輝閃耀的畫面與之前布施遭到僧人拒絕的陰暗畫面形成鮮明對比,羊仿佛一個正義的使者見證著李維杰從罪孽里走出并實現內心的自我救贖與解脫。第四次是以文字形式作為“迷途者”出現的,暗指劇中亦愚亦善的平明百姓,即“迷途羔羊”。影片中警察來到主角受害大女兒學校盤查素察之死時,課堂上教師正在講述關于羊的常識:“羊的視力不好,很容易離群,所以經常被大型動物吃掉。”意指大眾百姓在李維杰案件中的集體無意識跟風,忽視真正存在的客觀事實,僅從片面事實進行盲目判斷,最后一邊倒而致使暴亂,猶如迷途羔羊般橫沖直撞。而“容易被大型動物吃掉”以及影片結尾群眾的一句“羊只要能好好吃草,才不會管誰在薅它們身上的羊毛”則映射面對社會現實與矛盾沖突時百姓“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漠然態度與在被不斷剝削和壓迫下的平民反抗意識缺失,致使階層之間矛盾不斷加深的中國社會常態。
如今,電影和電視都已經成為影響大眾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藝術,它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豐富和完善了人的知識系統。《誤殺》作為一部成功的翻改影視藝術,它的成就不止是“技”的創新,更是“道”的深化,用最直觀豐富的畫面、精彩刺激的鏡頭、生動形象的內容吸引觀眾的注意、帶動觀眾的情緒、引起觀眾的共鳴,較之文字創作更具視覺沖擊,更能引起思想教育啟迪。
《誤殺》是一部具有真實罪案原型的影片,素察迷奸平平再以污言穢語脅迫兩母女而被“誤殺”的故事其實可以對應我國社會屢屢出現的諸如“我爸是李剛”“十三歲少年奸殺10歲女童”“15歲少女弒母”等青少年惡性犯罪事件,側面印證了我國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缺失。為此,國家教育方針明確指出“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中國最早的一部教育綱領性著作《大學》也把明德至善作為所有教育的根本目標: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國家、教育部、學校教育上更大力推進“課程思政”的建設,深刻落實“課程思政”的理念,倡導先立德、再樹人的育人順序,以期為學生培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其成為全面發展的人、完善的人。
然而教育不僅僅發生在校園,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除去身處學校學習的時間,家才是孩子生活最久的環境。我國著名現代教育專家朱永新教授就曾說過:“在所有問題兒童身上,都可以找到他們家庭的原因。家庭教育才是我們整個教育鏈的基礎之基礎,關鍵之關鍵。”中國傳統家教中也有強調“以德為先,把做人成為教育之根本”的理念,與現代教育方針相一致。從《誤殺》的“原生家庭”縮影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長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家長在面對孩子犯錯的問題上,不應直指學校的教育不當,而應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習慣和教育模式是否有做到規范與模范作用。殊不知孩子是父母的縮影,父母的言傳身教與溝通陪伴往往才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如同孔子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總之,《誤殺》中呈現的復雜人性與青少年的行為操守,都值得觀影家長對自身實施的家庭教育進行深切地反思與修正,努力讓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能成為培養孩子良好品性的課堂。
四、結語
《誤殺》基于《誤殺瞞天計》的本土化翻改,實現了藝術手段創新、觀念深化傳遞的摹仿與超越,展現出影片與觀眾共趣、共情、共鳴的特點,為現代翻拍電影的題材編改、用典、觀念傳遞、教育啟示等做出了模范作用。但這并非說《誤殺》就是完美的翻拍,影片由于想把太多社會議題都裝進電影里,反倒出現了部分內容欲滿則散的結果,以及內容太多導致故事重點不突出,部分情節與現實脫節的問題,這對翻拍片的創作具有警示作用。講好中國故事、呈現社會積極意義、提高觀眾的審美素養和共情能力、發揮對現實主義的批判功能,一直都是影視藝術創作的根本宗旨和目的,所以無論是原創影視作品還是翻拍作品,都理應更加用心細膩地制作和呈現,才能發揮它最大的道德引領與社會教化作用,實現其創作價值。
參考文獻:
[1]雋曉宇.民族化語境中《誤殺》與《誤殺瞞天記》的敘事異同[J].視聽,2020,(06).
[2]龔儀.試析電影《誤殺》的結局改編[J].漢字文化,2020,(11).
[3]申林,齊子洋.元電影《誤殺》中的迷影魅力[J].電影文學,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