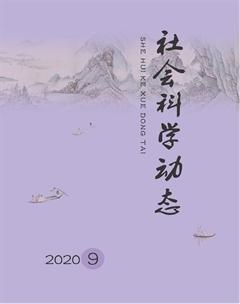“青記”的創新性實踐及其啟示
摘要: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是中國新聞史上一個著名的新聞團體,在其輝煌的歷史上寫有許多創舉:它率先訂立“記者公約”,主動開展戰地服務,設立記者之家,開展自我教育,創辦國際新聞社,舉辦新聞教育。樁樁件件,表現出“青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的奮發有為和創新性實踐,他們為中國新聞史寫下了壯麗篇章,“青記”的事跡和精神,對今天發展中國新聞事業具有啟示意義。
關鍵詞:青記;新聞團體;創舉;歷史貢獻
中圖分類號:G21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0)09-0107-05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由范長江、羊棗、夏衍、惲逸群等人發起創辦。1938年3月30日在武漢正式成立。“青記”為抗戰而生,為抗戰而努力。“青記”從上海創立時僅20多名會員,1938年底發展到五六百人,到1940年11月統計已有1156人,最多時達2000多人。在全國(包括國統區和解放區)建立了幾十個分會。“青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支持下,成為抗日戰爭期間團結進步青年新聞記者的中心,解放戰爭時期其部分分支機構繼續活躍在新聞戰線上。“青記”后來被確認為“中國記協”的前身。
在“青記”誕生之前,中國的新聞團體特別是早期的團體大多是以同業公會組織出現的,它是報人們自發地組織起來的,其作用主要是“互相長益、互相扶助、互相交通”。它通過業務工作及其組織工作,以同業組織的形式表達報人群體的政治參與,在捍衛國家主權、表達自身獨特的職業訴求和社會訴求、積極抵制對報界的鉗制、維護報界權益、培養新聞傳播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青記”誕生之時,正是國家民族面臨危亡之際。為抗戰而奔走呼號,是“青記”的信念,也是其使命。作為新聞團體,“青記”在出色履行其政治使命之外,在組織自我建設和社會服務方面也有諸多創新性實踐。
一、“青記”的創舉
(一)訂立“記者公約”
加強新聞工作者的新聞職業道德修養,是中國新聞工作者的優良傳統。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立后,“青記”領導人范長江在其會刊《新聞記者》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其中一篇《建立新聞記者的正確作風》就對新聞工作者忠實于客觀事實、廉潔自律提出了要求。他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聞記者。有了健全的人格,才可以談到其他和技術問題。新聞記者應當是社會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點,就不能算做新聞記者。”他認為,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最低限度要“第一,必須絕對忠實,必須以最客觀之態度,從事新聞工作……第二,必須生活于自己正當收入的工作中,無論如何個人不能取非工作報酬的津貼與政治軍事有關之津貼”①。
在“青記”武漢時期,“青記”提出的會員信條是:“努力自我修養,健全本身人格,鞏固共同意志,促進新聞事業,維護大眾利益,發揚民族精神”。汪精衛公開投敵后,“青記”又向會員提出了一個“記者公約”草案,規定6條:“一、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促進中華民族之解放與建設;二、堅持新聞崗位,為新中國新聞事業而奮斗;三、不收受非法金錢,不曲用自己筆尖;四、發揚集體主義,加強新聞記者之團結;五、建立平凡堅韌之工作與生活作風;六、努力自我教育,提倡工作與學習并重之精神。”② 這個公約的出臺,比馬星野依照美國相關記者信條所撰寫、在國民黨操辦的1941年中國新聞學會第一屆年會上通過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要早許多。
“青記”言行一致。抗戰之初,國民黨將領湯恩伯指揮南口之戰,英勇阻擊日軍,贏得稱贊。在當時《大公報》上,范長江對湯恩伯作了許多正面報道:“湯恩伯先生因為日夜辛勞的結果,瘦得不成樣子”,“故日夜操勞精密指揮,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機會,整天和電話、地圖接近,時時注意敵人一尺一寸的移動”。“青記”成立時,活動經費困難,便開展募捐。湯恩伯聽說后,開了一張5000元的支票,說是送給范長江個人的,范長江聽后大為惱火,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侮辱,當場擲還了支票,狠狠地罵了湯恩伯一番。這件事情,對“青記”會員們是一個很大的教育,也成為“青記”恪守廉潔、踐行公約的一個優良傳統。③
“青記”的重要成員馮英子后來講到過自己的一次經歷。1939年9月,馮英子從重慶東下,來到李宗仁所轄第五戰區的游擊區。在當時監利縣政府,他從縣長口中得知,駐守仙桃鎮的是第128師師長王勁哉。此人長期占地為王,割據一方。馮英子決定去仙桃鎮采訪,縣長極力阻止,因為此前第49師師長曾派一位參謀去聯絡王勁哉,結果被他活埋了。馮英子仍然堅持前往,到達仙桃鎮后,他卻受到王勁哉的禮遇。王勁哉不僅接受了馮英子的采訪,與他共進晚餐,還安排他住在自己一個姓馮的副官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們一起吃完早餐之后,王勁哉拿出自己的照片送給馮英子,并送他100塊錢。馮英子想,自己是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會員,決不能接受任何饋贈。為防不測,他收下了這筆錢,但向王勁哉告辭后,轉身來到馮副官家,將這100塊錢送給了馮家兩個小孩。從這件事可見,“青記”的會員們在工作中是自覺約束自己、修煉人格的。④
(二)主動開展戰地服務
“青記”在前線采訪的同時,還主動開展戰地服務。武漢保衛戰期間,記者們在采訪中發現,部隊士兵很多都是北方人,飲食上吃不慣南方的米粉,加上部隊在盛夏南方的山岳地帶行軍作戰,水土不服,瘧疾流行。最糟糕的時候,病員占到全軍半數以上,而部隊卻沒有治療虐疾的藥品。記者們將自己親眼看到的這些問題寫在戰地通訊中加以報道,同時利用采訪軍事委員會高層的機會向相關領導人反映。
“青記”會員記者們在采訪中還發現,除了飲食和疾病之外,部隊作戰的地方,由于廣播還不普及,報紙也沒有辦法送到,官兵對外界信息知道得很少。記者們呼吁要改變這種情形。此時,“青記”總會和幾個救亡團體正在籌備設立“戰地文化服務處”,還指定在江西南(昌)潯(九江)線上隨軍采訪的孟秋江、李洪等人組成“戰地書報供應隊”,利用上前線的機會,為部隊送去一部分書報。后來,又在陽新、通山一帶的31集團軍中建立“三十一文化兵站”,為軍隊供應一部分報紙雜志和士兵讀物。⑤ 1938年8月,孟秋江等購買了在漢口出版的《大公報》《新華日報》《武漢日報》《掃蕩報》和在南昌出版的《工商日報》《劍報》《政治日報》等共460份報紙,派人送到前線。8月27日,孟秋江赴前線采訪,又購買了大批《大公報》和《新華日報》送到前線。后來,范長江、陸詒到南昌,又帶去了“青記”總會和長沙分會、生活書店捐贈的2000份報紙。這一次,除了部隊機關外,每個師分配到了72份報紙,對鼓舞前線將士的士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⑥
(三)設立記者之家
“青記”成立后,記者們立即開赴前線,進行戰地報道。1938年9月,長江下游戰事吃緊,日軍溯江而上,直逼武漢。從前線回到漢口的戰地記者也日益增加。為了安置從前線回來的各報社記者,“青記”在漢口長春里租了幾間房子,開辦記者之家。記者之家的開辦,使得大家能在一起共同工作,成為一個戰斗的集體。例如:記者們向報社發回的電訊,都要由自己譯成電碼,才能迅速發出,如果電碼不熟,一份電碼得花費不少時間,但大家集中在一起,就可以取長補短,相互合作,比較快捷。因此,記者之家很受大家的歡迎。
記者之家盡管房舍簡陋,但讓無處安身的記者們有了休憩場所,使入住者有了家的感覺。婦女文化工作者胡耐秋撰文道:“在民族復興的血戰里,我們是生息在沙場上的。千萬的居民,失去了他們的房屋,我們流浪的記者,哪有家呢?有的,這就是能讓我們暫時安居一日、兩日的漢口記者之家。這里有年長的哥哥,新來的弟弟,統統在一個偉大的企圖之母親的策動下活動著!我愛著記者之家呵!正因為愛它,然而職務叫我不斷出發前方,所以我還得迅速地離開它!”⑦ 重慶《大公報》采訪部主任徐盈曾寫一首打油詩:“又到記者之家,記者之家生意興隆,容光煥發。碧星閃爍于上,寶瑚堤決于下,藥眠大師使用法寶蒲拉托。乃見——高天共長江一色,有綠椅一架正向西出發。”打油詩中的碧星指陳碧星;寶瑚指石寶瑚,此時正患腹瀉;藥眠指黃藥眠;蒲拉托是一味補藥名;高天、長江系高天和范長江;綠椅是陸詒的諧音。這首打油詩描寫了在記者之家里,作者見到了6位青年記者當時的狀態,并且用他們的名字巧妙地描繪出他們當時的精神和生活狀態,充分體現了“記者之家”里年輕記者青春飛揚、團結友愛的精神面貌。為記者之家寫過詩和短文的還有陸詒、高天、胡蘭畦等。⑧
(四)進行自我教育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起初的名字叫“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登記時,由于國民黨當局不允許成立職業性組織,于是以學術性組織“學會”的名稱登記。成立大會通過了學會章程。章程指出:學會的宗旨是“研究新聞學術,進行自我教育,促進中國新聞事業之發展,求取新聞事業及其從業員之合理保障,以致力中華民族之解放與建設”。⑨ 范長江在致開幕詞時,著重說明組織學會的目的之一,就是進行自我教育。進行自我教育的方式,一是出版討論戰時新聞工作和新聞學術的刊物,一是利用座談會或討論會的方式,學習新聞界前輩的經驗,交流工作經驗,促進相互學習。⑩
“青記”主辦的會刊《新聞記者》,在武漢出版7期,在長沙出版1期,后移到桂林繼續出版。《新聞記者》的出版是實現學會章程提出的學會宗旨努力。刊物第一卷第2期的主題是“抗戰建國問題”,第3期主題是“歡迎世界學生代表團”,第4期主題是“戰地工作”,第6期主題是“探訪工作”,第6—7期主題是“戰地新聞工作”,第9—10期主題是“戰時新聞政策”。第二卷第3—5期主題是“戰地報紙問題”,第7期主題是“戰地新聞事業”,第9期主題是“新聞事業介紹”,第10期主題是“東亞新聞事業”。其中一些文章如《論新聞采訪與報道》《怎樣寫空戰報道》《怎樣處理新聞》《怎樣做一個戰地通訊員》等是對新聞業務的研究,還有一些文章如《西南的新聞事業》《廣西的新聞事業》《香港的新聞界》《澳門的新聞事業》等是對我國新聞事業宏觀的研究。
除了學會刊物之外,學會還由各地分會在所在地報紙上出版新聞專刊,如廣州、桂林《救亡日報》,桂林《掃蕩報》《廣西日報》,吉安《大眾日報》《民國日報》,甘肅《民國日報》,成都《新民報》,韶關《大光報》,香港《星島日報》,重慶《國民公報》等。這些刊物、專刊的主要內容是進行新聞理論指導,交流學習與實踐經驗,提高記者的思想和業務素質。{11} 學會領導人范長江對會員們的學習抓得很緊。他曾撰文說:“我們這班青年的新聞從業員對于新聞工作,是想把它做成事業,不只是一個職業。事業是為公共服務的,比較永久的,職業只是個人的一時的生活問題。要能開展事業,一個新聞工作者沒有不斷進步的知識和能力,是絕對無法勝任的。要進步就要有學習。學習與工作是不能分離的事情……不能不斷學習,不能不斷進步,怎樣能擔負真正指導輿論的工作呢?”{12}
范長江在不同時期,結合當時的形勢,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具體要求。他認為,要提高新聞報道的質量,記者必須加強自我教育,培養高尚品質和優良的工作作風。他在《怎樣做新聞記者》中提出青年記者加強自我教育的要求:第一,要有堅定地政治方向。沒有正確的政治方向,等于航海的船沒有了指南針。第二,要有操守。新聞記者面臨各種誘惑與壓迫,“要能堅持著真理的火炬,在夾攻中奮斗,特別是在時局艱難的時候,新聞記者要堅持真理,本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實在非常重要”。第三,是學習知識。這個知識,既要博,又要精。要終生不停地刻苦學習,向博和精的途上邁進。第四,是學會各種技術,既包括新聞專業技能如打字、攝影、譯電等,也包括與新聞采訪有關的社會技能如騎自行車、駕船、開飛機等。{13}
除了辦刊物,“青記”自我教育的方式是每周在記者之家舉行座談會、討論會,以提高認識,聯絡感情;每周出版墻報,交流工作、學習心得。陸詒撰文說:“有了記者宿舍,不僅僅是睡得比門板稻草要強一些,而且這里有集體的生活,集體的工作,集體的學習!期望會友們來住的更多,期望在全中國各處都有美滿的記者之家。”{14} “青記”在長沙期間,長沙分會組織會員文化界、新聞界座談會,討論“戰時新聞政策”。撤到桂林后,成立南方辦事處,南方辦事處組織會友小組,每周定期組織小組會議,交流工作經驗和讀書心得。當時建立會友小組的有南方辦事處本部工作人員、國新社、救亡日報社、新華日報桂林分館、掃蕩報桂林分館和華僑戰地記者團等。{15}
(五)創辦國際新聞社
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在武漢淪陷前的1938年9月開始籌備。當時,云集在武漢的外國記者因為無法得到正確的戰地消息而不滿,為了滿足外國記者的需要,國民黨不得不成立了“國際宣傳處”。這個機構歸屬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領導。由于周恩來同志積極貫徹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國際宣傳處的處長對于進步的新聞工作者也有比較合作的態度。在周恩來同志參與籌劃下,范長江、胡愈之等經過商量,決定以“青記”會員作為骨干成立新聞通訊社。由于此前從上海撤到香港的惲逸群等人在香港成立了國際新聞社,向海外發稿,頗有影響,遂借用其名,香港的國際新聞社變更為香港分社。10月20日,國際新聞社在長沙正式成立,向國際宣傳處供稿,同時向國內報社發稿。國新社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通訊社。“青記”是一個統一戰線的群眾組織,國新社則是一個革命新聞事業機關。
11月12日,長沙燃起大火,國新社與“青記”一起撤到桂林。為了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堅持革命立場,國新社不接受經濟上的資助,采取生產合作社的形式。為了讓國內外讀者了解政治形勢和動向,國新社約請了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寫專稿,供各地報紙采用。這些專家學者有張友漁、張鐵生、劉思慕、羊棗、夏衍、陳瀚笙、駱耕漠等。國新社在發布新聞稿時,采用了以不同形式、類別的稿件發給不同的新聞媒體的方式,以適應不同讀者的需要。對國內讀者的媒體,發給他們新聞稿、特約專電、新聞通訊、專論等;對國外媒體,則發給他們祖國通訊、國新通訊,后來在香港還發布英文的遠東通訊等。{16}
(六)舉辦新聞教育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成立之前,新聞教育除了高校之外,大多是依托媒體或大學成立的新聞團體開辦的新聞學校來開展的。“青記”成立后,積極嘗試創辦新聞教育,它所進行的新聞教育雖不如學校教育那樣正規,但在戰爭歲月里,它通過吸收會員,因地制宜,以多種形式不遺余力推動進步的新聞教育,這在中國新聞教育史上,是一個創舉。
“青記”的新聞教育開展,是在各地舉辦的新聞學院、新聞工作研習班、星期新聞講座、新聞學術講座等,形式多樣。“青記”總會與分會請當地新聞界有名望、有學識、有能力及經驗豐富者為講師,給當地新聞記者及有志于新聞工作的青年授課。
“青記”轉移到桂林后,設立了南方辦事處。廣西當局覺得自己辦的報紙不能令人滿意,新聞人才太少,于是支持“青記”辦培訓班。經過不到兩星期的籌備,“青記”的“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就開班了,學員大約80人,晚上上課。講習班講授戰時新聞學概論、新聞采訪與編輯、國際形勢講話和對敵宣傳等課程,也講授一些辦油印報的技術。上課的教師有范長江、孟秋江、陸詒、夏衍、鐘期森、王文彬等,徐特立同志也來講習班做過報告。{17} 講習班提高了會員的新聞理論學養和新聞業務水平,并為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青年記者鞏固了抗戰必勝的信心。
1939年4月,“青記”香港分會創辦中國新聞學院,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辦的新聞學校。日寇侵占香港時停辦,解放戰爭時期又復校,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結束,先后共辦了5期。此外,于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又開辦了函授班和函授學院。新聞學院和函授班、函授學院先后畢業的人數達300人以上。{18} 在中國新聞學院授課的教師中著名的人士有:郭步陶、金仲華、劉思慕、樓適夷、喬冠華、邵宗漢、羊棗、徐鑄成、惲逸群、范長江、薩空了、高天、千家駒、廖沫沙、黃藥眠、陸詒等。{19} 學會每周還出版一期《記者通訊》,以提高會員的新聞業務水平,另外還出版了《中國新聞手冊》,以供新聞工作者平時參考。
二、“青記”創舉的啟示
“青記”從誕生至今已有80多年歷史,2000年國務院批復中國記協,將“青記”創立的日期定為中國記者節。回首“青記”往事,對今天我們團結廣大新聞工作者,創造性地做好新聞工作,仍有啟示意義。
1.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是抗日戰爭中誕生的群眾性團體。參與者是一群熱血青年,他們十分重視“新聞宣傳工作的影響,對于抗戰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認為“新聞輿論可以堅定抗戰勝利的信心,可以鼓舞抗戰的勇氣,可以打擊敗北主義,可以激勵英勇的士氣”。他們團結在一起成立這樣一個組織,一方面是為了當前的抗戰新聞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組織團體訓練造就未來新聞事業的人才。“為了補救目前抗戰中新聞工作的缺點,為了失去崗位的同業,為了訓練成功大批健全的新聞干部以應付將來新聞事業的需要,我們不能不起來組織,不能不趕緊以集體的力量,加強自我教育,加緊自我扶助。”{20} 正是這種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這個群體中的進步力量勇于實踐,敢于擔當,并且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自覺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辦成了一個追求進步、在新聞團體建設中多有創新的組織。
2. 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在其存續期間,做了諸多在中國新聞史上無人出其右的工作:其一,為加強自身組織建設,訂立“記者公約”,這對約束記者職業行為,形成職業規范,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二,“青記”是一個記者團體,它的使命和職責是做好新聞報道,但它深入前線,主動開展戰地服務,擔負起組織的社會責任,十分難能可貴;其三,它為會員切身利益著想,設立記者之家,為前線采訪歸來的記者們提供便利,讓記者們有家一般的感覺;其四,“青記”重視隊伍建設,重視對會員進行自我教育,通過刊物學習、通過開座談會、討論會等形式,讓會員在政治上保持堅定地立場,專業技能上有過硬的本領,能夠擔負起引導民眾、引導輿論的時代重任;其五,“青記”在自己的組織之內創辦一個新的組織——國際新聞社,在一個統一戰線組織中內生出一個完全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新聞事業機關,為國統區進步青年提供了通過革命實踐,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機會,為黨培養了一支能打硬仗的新聞隊伍;其六 ,為適應抗戰需要,“青記”舉辦新聞教育,在桂林舉辦“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在香港開辦“香港中國新聞學院”、函授班和函授學院,為抗戰新聞事業和新中國建設事業培養了大量的各方面人才。所有這些都是“青記”領導人和“青記”群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緊密結合實際斗爭的需要,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結果,在中國新聞史上閃耀著奪目的光輝。
3. 新聞團體是一個民間組織,它是不同媒體的新聞從業者的聯合體,但它又有共同點旨趣,大體相似的目標,因此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具有其獨特的作用。“青記”組織的成員來自海內外各個媒體,成員有各自的政治傾向,有各自的個性,“青記”通過前述各種方式,將不同的成員緊緊團結在自己的周圍,為民族救亡的偉大斗爭而努力,這是“青記”的卓越之所在。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溫“青記”事跡和精神可資借鑒的地方。
注釋:
① 范長江:《范長江新聞文集》,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95—796頁。
② 馮英子:《重慶的斗爭》,《新聞研究資料》總第7輯,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頁。
③ 馮英子:《回憶長江》,《新聞研究資料》總第28輯,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頁。
④ 馮英子:《鄂中探險記》,《新聞研究資料》總第13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55-60頁。
⑤⑩{15} 韓辛茹:《陸詒》,人民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3、147—148、154頁。
⑥⑧ 馮英子:《在武漢的日子里》,《新聞研究資料》總第7輯,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4、55—56頁。
⑦⑨{11}{13}{14}{16}{18} 方蒙:《范長江傳》,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218、222、228—230、223、245—248、222頁。
{12} 廣西日報新聞研究室編:《國際新聞社回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8頁。
{17}{20} 范蘇蘇、王大龍:《范長江與青記》,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203頁。
{19} 鐘華:《香港中國新聞學院——記解放前一所新型的新聞學府》,《新聞研究資料》1986年第2期。
作者簡介:廖聲武,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62。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