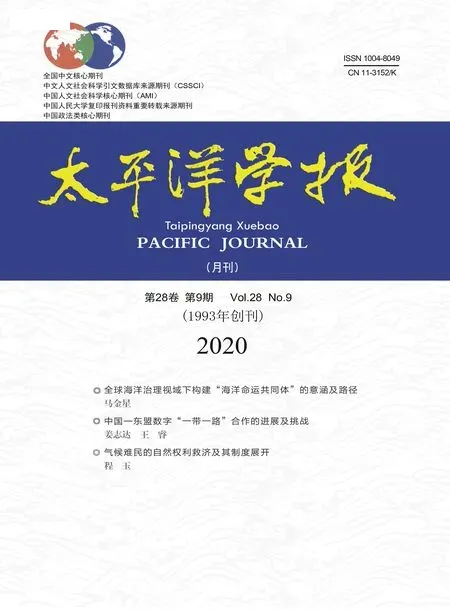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進展及挑戰
姜志達 王 睿
(1.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北京 100005;2. 重慶大學,重慶400044)
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驅動下,第四次工業革命快速發展。數字經濟(1)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站,2016年9月29日,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作為一種新興經濟形態正在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成為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2)《數字經濟治理白皮書(2019)》,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版,第1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帶來的全球危機進一步推進了數字經濟發展,并將在全球經濟復蘇后產生持久影響。
數字“一帶一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數字經濟發展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結合。中國大力推進“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建設,就是要發揮數字經濟的優勢和效應,推動“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抓住數字化發展機遇,促進數字要素資源創新集聚和高效配置,帶動產業融合發展,助推“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提升信息化水平,積累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
2017年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在論壇上正式提出數字絲綢之路倡議。(3)“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年5月14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514/c64094-29273979.html。自該倡議提出以來,中國與沿線國家相關合作進展迅速,成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亮點。但是,數字“一帶一路”處于發展初期,許多方面還屬于探索階段,需要通過實踐不斷發展完善。作為中國的近鄰,東盟既是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也是“一帶一路”合作的重點區域,深化與東盟的數字“一帶一路”合作對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及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考察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基礎,梳理其成果,力求剖析這一合作面臨的挑戰,提出應對思路,并展望合作前景。
一、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基礎
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除了雙方都有強烈的合作意愿外,更為重要的是雙方具備開展合作的重要基礎,展現出廣闊的發展空間。
1.1 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數字化進程加快
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活躍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4)“習近平出席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開幕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8年5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05/28/content_5294268.htm。數字化、網絡化、綠色化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顯著特征,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深度融合。在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推動下,全球競爭格局正加速調整。對中國而言,其已深度嵌入全球創新網絡,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同時,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及環境壓力增大,中國經濟亟需產業轉型升級,從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邁向中高端。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與中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為中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了重大機遇。(5)王皖君:“找準科技創新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經濟日報》,2019年7月25日。對東盟國家而言,新一輪科技革命也使東盟國家領導人意識到,原有的依靠低廉勞動力降低制造業成本的模式將受到沖擊,需要抓住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歷史機遇,通過大力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的數字化轉型,以此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投資并推動經濟的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6)Badri Veeraghanta,“Digitalisation Key to ASEAN Attracting China Trade War Exodus”, The Business Times, October 23, 2019.但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世界經濟原有的產業鏈、價值鏈受到較大沖擊,亞洲出口導向型國家大受其害。(7)“‘恐怖陷阱’沖擊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人民日報》,2018年7月15日。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產生了較大影響,加速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價值重構。因此,借助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雙方可在數字經濟和高科技產業領域深化交流合作,促進創新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整合與高效配置,通過建立更為緊密的產業分工和區域價值鏈體系,緩解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
1.2 中國—東盟關系制度化程度較高
東盟與中國毗鄰而居,鄰居大國的身份定位是雙方關系中最基本且最本質的部分。(8)聶文娟:“東盟對華的身份定位與戰略分析”,《當代亞太》,2015年第1期,第21頁。基于這種身份定位,一方面,東盟重視與中國發展全方位關系和全面合作,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另一方面,東盟又擔心中國的不斷強大可能會制約自身的地區影響力,故而在中國和其他大國之間實行平衡外交。2003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大國,中國與東盟的政治互信得以加深。在實踐中,東盟意識到中國的發展為本地區提供了重要機遇,由此堅定支持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隨著雙方政治互信加深,2003年10月8日,中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簽署并發表《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9)“落實中國—東盟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的行動計劃(2016—2020)”,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6年3月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344899.shtml。雙方正式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此外,東盟所有成員國與中國之間都已建立了伙伴關系。就中國—東盟合作而言,中國作為地區大國,以實際行動回應東盟國家的期待,發揮著負責任大國的作用,積極提供制度性的區域合作公共產品。在中國的倡導下,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衛生等方面建立了諸多合作制度,也取得了顯著進展。自2002年中國和東盟啟動自由貿易區進程以來,雙方貿易額由2002年的548億美元提高至2019年的6 415億美元,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18年雙向投資158億美元,累計達到2 057億美元。(10)“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議定書》全面生效”,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2019年10月23日,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zhengwugk/201910/41659_1.html。自“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雙方在產業園區、港口、鐵路等領域的合作取得多項積極成果。(11)“中國—東盟國際產能合作初具規模”,新華網,2016年9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13/c_1119559123.htm。中國與東盟已經構建起以文化產業合作、教育交流和合作、青少年交流,以及國際旅游合作等為主要內容的人文交流機制。雙方互訪由2003年的387萬人次增至2018年的近5 700萬人次。截至2019年10月,每周有近4 000個航班往返于中國與東盟國家,雙方互派留學生達20萬人。(12)“東盟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釋放哪些信號?”,新華網,2019年10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0/10/c_1125086882.htm。
這些制度安排既發揮了合作渠道的功能,促進了雙方的務實合作,又增強了雙方關系的韌性,使中國與東盟的整體關系并未因東盟部分成員國與中國的某些權益爭端而受到沖擊。在特朗普政府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后,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公開表示: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必須容納一個更有影響力的、日益強大的中國。美國也必須接受,阻擋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美國必須與中國尋求建設性的關系,以及在經濟上互相依存的關系。(1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須接受阻擋中國崛起是不可能的”,中新網,2019年8月19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9/08-19/8930896.shtml。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與東盟互通疫情信息,加強抗疫合作。中國先后向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提供醫療物資援助,并向老撾、柬埔寨、菲律賓派出醫療隊,譜寫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新篇章。
1.3 雙方新的發展戰略契合度較高
為抓住數字經濟革命帶來的機遇,中國政府近年來大力發展“互聯網+”經濟,先后出臺《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信息化規劃》《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等指導性文件,不斷完善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領域國際合作的頂層設計,以期達到經濟發展制高點。
冷戰結束后,東盟將互聯互通作為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內容,而信息互聯互通是其建設的重要一環。為此,東盟除了在《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2025》《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等政策文件中強調信息互聯互通外,還專門制定了《電子東盟框架協議》等政策措施和框架,希望借助數字“一帶一路”促進東盟國家市場緊密聯合,提升數字互聯互通,力爭使東盟成為數字經濟領先型地區集團。(14)“Digital ASEAN”,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www.weforum.org/projects/digital-asean,訪問時間:2020年2月3日。為更好地實現區域數字化轉型,東盟在已有發展戰略的基礎上,正抓緊制定“第四次工業革命綜合戰略”,旨在解決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治理、經濟和社會等方面面臨的問題。基于本國國情和發展目標,東盟各國亦推出各自的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參見表1)。目前,中國與東盟已在電信、電子商務和智慧城市發展等共同關注的領域探討科技創新合作,力求抓住數字經濟和技術的創新機遇,實現創新驅動發展。(15)“中國與東盟共享數字經濟合作機遇”,《中國報道》,2020年第6期,第71頁。2020年6月,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正式啟動,雙方在數字化防疫抗疫、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展開密切合作,進一步推動了雙方戰略的契合和深化。

表1 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
1.4 雙方在數字經濟發展方面具有較強互補性
中國與東盟在發展數字經濟方面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合作前景廣闊。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的持續深化為雙方數字“一帶一路”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市場空間。中國在跨境貿易、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支付等數字產業化方面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工業互聯網和智能制造等產業數字化領域具有較強的比較優勢。中國的全球競爭力隨著自身數字經濟“迭代升級”而不斷增強。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開展的全球數字競爭力排名,中國的排名在2019年躍升至22位。(16)“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digital-competitiveness-rankings-2019/,訪問時間:2020年2月8日。而東盟數字經濟發展總體上還處于早期階段,數字經濟價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僅為7%,但東盟發展數字經濟的潛力很大,主要表現在:勞動適齡人口數量超過4.3億,擁有龐大的數字經濟潛在群體;互聯網活躍用戶數量達到3.3億,是全球互聯網用戶增速最快的地區;到2025年,東盟數字經濟規模將達到3 000億美元,約占東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8%,(17)“E-Conomy SEA 2019”, Bain & Company, https://www.bain.com/globalassets/noindex/2019/google_temasek_bain_e_conomy_sea_2019_report.pdf,訪問時間:2020年3月3日。東盟數字消費者預計突破3億人,(18)“聚焦東盟數字經濟發展(三):東南亞數字消費前景廣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20年8月19日,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2008/20200802993956.shtml。一個具有較大規模和較好成長性的消費市場正在形成。
二、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進展
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基于各自的比較優勢,不斷加強政策溝通與對接,創新合作機制,推動雙方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進入全方位發展新階段。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為中國與東盟進一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拓展了新空間,注入了新動力,也為打造中國—東盟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提供了新的實踐探索。
2.1 發展戰略對接不斷推進
數字經濟政策對數字經濟發展極為重要,中國與東盟開展“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需加強雙方的政策協調與對接。(19)“The Digital Economy in Southeast Asia: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s for Future Growth”, World Bank, January 1, 2019, p.17,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2894155870 8267736/The-Digital-Economy-in-Southeast-Asia-Strengthening-the-Foundations-for-Future-Growth.2020年,中國提出“深化數字絲綢之路、‘絲路電商’建設合作,在智慧城市、電子商務、數據跨境等方面推動國際對話和務實合作”等八項舉措,進一步明晰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頂層設計和合作框架。(20)“關于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20年6月1日,https://www.ndrc.gov.cn/xwdt/xwfb/202006/t20200601_1229648.html。東盟成員國則于2019年1月簽署了《東盟電子商務協議》和《東盟數字融合框架》,為“數字絲綢之路”與東盟建立整體性政策對接奠定了基礎。在合作進程方面,2017年12月,中國與老撾、泰國等國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致力于實現互聯互通的“數字絲綢之路”。(21)“多國共同發起‘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光明日報》,2017年12月4日。2018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21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雙方通過《中國—東盟戰略伙伴關系2030年愿景》,對接《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與“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重點領域,并且促進數字創新領域的戰略對接。在2019年7月底召開的中國—東盟外長會上,雙方確定2020年為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在電子商務、科技創新、5G網絡、智慧城市等領域加強合作。(22)“確定!2020年: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中國—東盟博覽會網站,2019年8月1日,http://www.caexpo.org/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420&id=236772。2019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發表了《中國—東盟關于“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國—東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議領導人聲明》《深化中國—東盟媒體交流合作的聯合聲明》等三份合作文件,(23)“李克強在第22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9年11月4日,http://www.gov.cn/premier/2019-11/04/content_5448249.htm。進一步深化和明確了雙方在數字經濟領域合作的重點和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東盟國家數字經濟發展階段有所差異,中國與東盟各國開展政策對接的重點領域也不盡相同,如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其對接重點在數字技術、智慧城市等領域;而對于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數字經濟發展相對薄弱的國家,則側重于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化轉型等方面的合作。這種差異性的戰略對接,既體現了雙方合作的靈活性和務實性,更體現了雙方開展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迫切愿望。
2.2 合作范圍日益擴大
隨著東盟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需求增加,中國—東盟“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由先前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跨境電商,拓展至智慧城市、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等多個領域,涵蓋了基礎設施、平臺建設、市場拓展和數字內容等方面,合作領域越來越多,合作規模越來越大。僅2019年上半年,中國對東盟科技領域的投資達到25億美元,超過2017年全年投資額。(24)“Digital Economy Is Becoming the Tie Connecting the Destinies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aixun, August 23, 2019, https://haixunpr.org/info/19082373936.在基礎設施方面,華為和中興承擔了東盟多個國家的5G項目,中國電信運營商和通信企業已與部分東盟國家合作建成數條跨境光纜和國際海纜。中國設計的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海底光纜系統已于2015年開始建設。(25)方芳:“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國際環境與路徑選擇”,《國際論壇》,2019年2期,第67頁。中新(重慶)國際數據互聯互通專用通道已于2019年正式開通,通道以新加坡為樞紐,推動東盟國家共同參與通道運營和使用,更好地服務于東盟國際通信網絡體系。在平臺建設方面,以基礎設施、信息共享、技術合作、經貿服務和人文交流五大平臺為建設重點的中國—東盟信息港,已經成為面向東盟的國際通信網絡體系和信息服務樞紐。在市場拓展方面,廣西南寧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于2018年12月正式運營,具有東盟區域特色的跨境電商產業帶及集聚地正式形成。(26)“中國—東盟跨境電商‘逆風飛翔’”,《中國報道》,2020年5月28日。與此同時,中國數字經濟領域龍頭企業通過股權投資與并購等方式加速布局東盟數字經濟市場,以電子商務平臺為特征的跨境貿易發展迅速。中國企業入股印度尼西亞電商,并在馬來西亞啟動了首個世界電子貿易平臺(eWTP)海外“試驗區”——馬來西亞數字自由貿易區。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大量應急救援物資通過該平臺運送到全球各地,該平臺成為全球抗疫救援和恢復生產的關鍵通道。中國企業投資的數字支付平臺已覆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等6個東南亞主要市場,其中11個平臺已服務超1.5億用戶。(27)“阿里、騰訊投資的11個東南亞數字支付平臺已成當地巨頭 服務超1.5億用戶”,移動支付網,2020年7月1日,https://www.mpaypass.com.cn/news/202007/01111703.html。在數字內容方面,中國企業的數字內容服務平臺已在泰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印度和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落地。可以預期,隨著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進程的持續,雙方合作的領域將進一步拓展,合作的成果將更加豐富多元。
2.3 合作機制不斷完善
建立和完善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機制是未來擴大雙方在數字經濟領域深度合作的重要保障。在現有的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一帶一路”倡議、瀾湄合作等多邊和雙邊合作機制基礎上,雙方初步形成了以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和中國—東盟電信部長會議兩大政府間對話機制為重點,以中國與東盟各國、行業組織、企業、智庫的合作機制為補充的多層次、多渠道的合作機制體系。中國與新加坡在蘇州工業園區、天津生態城及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等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的基礎上,已形成副總理級、部長級和地方級不同層級,信息技術、數字貿易等不同領域較為完善的溝通協作機制。另外,中國還與泰國建立了“數字經濟合作部級對話機制”,與越南、柬埔寨分別簽署“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與馬來西亞啟動雙邊跨境電子商務合作諒解備忘錄的商簽進程,推動雙邊合作機制建立。(28)“中國東盟共建數字經濟之路潛力巨大”,《經濟日報》,2019年4月24日。中國還充分發揮中國—東盟信息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產業聯盟、廣西—東盟智慧城市博覽會等平臺的作用,以南寧、廈門、杭州、濟南、昆明、深圳、南京、成都等城市為載體,加強與東盟各城市間智慧城市等重點領域的合作與交流。(29)“中國—東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議領導人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站,2019年11月8日,https://www.ndrc.gov.cn/fggz/cxhgjsfz/dfjz/201911/t20191108_1201879.html。除了政府部級對話機制外,中國—東盟商務理事會等行業組織、企業、智庫間多層次和多渠道的合作機制也正加快建立和完善。需要強調的是,除了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建立多邊和雙邊合作機制外,中國還創新其他合作機制,如2018年5月,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了《關于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在第三方市場開展合作,其中大部分項目均布局在東盟地區。中日已將泰國東部經濟走廊(Eastern Economic Corridor,簡稱EEC)確定為兩國第三方合作的發軔之地。(30)王競超:“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日本的考量與阻力”,《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3期,第84-85頁。
三、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面臨的挑戰
在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因得益于合作雙方的互補性和發展潛力,數字“一帶一路”在東盟及其成員國兩個層面都取得了積極進展,且依舊保持著良好的發展趨勢。盡管如此,數字“一帶一路”合作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影響了合作績效和未來發展。
3.1 數字合作頂層設計有待完善
數字“一帶一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技術支撐。自2017年習近平主席正式提出數字“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建設就成為中國與東盟合作的重點領域:一是,通過虛擬空間的打造,支持五大領域互聯互通;二是,通過開放中國的巨大市場,用“輕資產”方式促進沿線國家傳統產業轉型、促進創新就業;三是,整體利用中國已經形成的數字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主動優化產業布局,形成區域經濟利益共同體基礎。(31)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數字“一帶一路”藍皮書課題組:“激發數字化企業潛力 共同打造數字‘一帶一路’”,《光明日報》,2019年4月22日,https://news.gmw.cn/2019-04/22/content_32761743.htm。
但相較于物理層面“一帶一路”合作的實際操作,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缺乏頂層設計和統一規劃,缺少制度性安排固化實際推進的合作進程。同時,數字“一帶一路”的倡議目標、合作機制、優先發展方向和實施路徑也不明確,導致合作各方在共同推動技術創新協同、數據資源共享和市場開放等領域缺乏必要的協同。這顯然既與建設數字“一帶一路”的初衷相背離,也與該地區在中國總體外交中的特殊重要性不相符合。
在東盟內部,雖然各成員國相繼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但相互之間缺乏相通性,特別是涉及跨區域、跨領域的項目難以銜接。如前文表1所示,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較為懸殊,各國發展數字經濟的起點不同,目標相差較大,直接結果就是導致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數字經濟呈現碎片化特征。還要指出的是,東盟作為地區組織在整合各國數字經濟戰略方面的作用不太明顯,這顯然與目前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缺乏戰略性安排有關。與此同時,由于東盟地區存在“合作機制擁堵”的現象,其他域內外大國也通過現有的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加強了與東盟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換言之,在建設數字“一帶一路”方面,東盟同樣沿襲了在其他領域所使用的“大國平衡”這一對沖策略,對與中國合作建設數字“一帶一路”持既歡迎又防范的立場,這也成為中國在數字“一帶一路”建設中與東盟在政策協調上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從微觀層面上看,參與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的中方企業是私營企業和少數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參與合作更多是出于商業利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雙方合作規劃的統籌協調。
3.2 數字治理滯后于合作需要
數字經濟依托技術快速迭代帶來各種機遇的同時,也帶來許多數字治理挑戰,涉及安全、標準規則和治理機制諸方面。在安全方面,數字經濟對國家主權、社會穩定、網絡安全的影響日趨深入,一些項目涉及東盟國家之間能源、交通、水利、民航等領域的重大合作,這些合作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政策具有很大關聯性,因而包含諸多敏感信息,隨著越來越多的信息系統和數據暴露在開放的互聯網上,原有的網絡安全防范措施受到新的挑戰。(32)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編著:《數字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數字經濟的機遇與挑戰》,人民郵電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頁。在社會經濟方面,數字經濟帶來了跨境電子商務的征稅困境,導致國家稅源流失,并引發國家間的經濟糾紛。(33)Richard Rubin,“Italy Follows France in Levying a Digital Tax”,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5, 2019.在標準和規則方面,商業和技術的快速變革使東盟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相關法律亟待完善。(34)Heejin Kim, “Glob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Change: The Interplay of Laws and Technologies in E-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Vol.35,No.5,2019,pp.1-20.例如,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國擬籌劃征收電商稅,保證電商與實體零售商的公平競爭,但各國稅收制度不一致,容易產生各類糾紛。在數字監管方面,東盟各國面臨監管思路和監管手段的制約,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監管制度、措施建設還存在滯后、空白等問題。這些治理困境不僅影響數字經濟的發展,更制約著數字經濟合作的進程。
其中,中國—東盟“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存在的數字治理滯后問題,主要表現為在數據收集、個人隱私、數據安全、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物流、海關等諸多方面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和規范,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雙方數字經濟領域合作的廣度與深度。在治理機制方面,現階段中國—東盟“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的協調工作主要由電信部門牽頭,但由于部委主要側重單一業務板塊,在諸如網絡空間安全、征收“數字稅”、縮小“數字鴻溝“等社會、經濟與安全方面缺乏整體協調能力。與此同時,由于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階段和重點不相一致,其數字治理也存在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
3.3 東盟國家存在巨大的“數字鴻溝”
數字經濟與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產業基礎和發展環境高度相關。除新加坡是發達國家外,東盟其他國家處于工業化中期或初期的發展階段,各國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經濟發展的信息化支持存在較大差距,由此形成東盟成員國之間巨大的“數字鴻溝”。例如,2019年新加坡在全球63個國家數字競爭力的排名中位列第二,而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東盟國家的數字競爭力排名靠后。(35)“IMD World Digital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201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https://www.imd.org/wcc/world-competitiveness-center-rankings/world-digital-competitiveness-rankings-2019/,訪問日期: 2020年3月2日。在印度尼西亞的網購消費中,網銀和電子錢包等支付方式只占10%左右。(36)“中國金融科技企業扎堆‘出海’ 印尼緣何受青睞?”中新網,2018年4月25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8/04-25/8499437.shtml。根據環球金融創新公司統計,90%的菲律賓人沒有信用記錄,66%的菲律賓人沒有任何銀行賬戶。(37)張信宇:“目標東南亞 螞蟻金服境外本地化戰略”,移動支付網,2018年9月14日,http://www.mpaypass.com.cn/news/201809/14092210.html。此外,受資金短缺的限制,大部分東盟國家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導致信息化程度較低,寬帶服務網絡使用成本居高不下。特別是東盟各國之間互聯互通的數字基礎設施供給嚴重不足,跨國跨區域通信網絡不完善,缺乏跨境電子商務平臺體系及完備的物流供應鏈基礎,這些都使中國企業難以獲取一體化的規模經濟效益。
與此同時,東盟國家的“數字鴻溝”還表現在數字人才資源匱乏。大部分東盟國家在推動數字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面臨嚴峻的人才資源短缺困境,東盟國家的人才結構和素質與中國—東盟“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合作的要求并不適應,面臨數字技術和產業經驗的跨界人才及初級數字技能型人才的“雙重缺失”。目前,東盟國家主要采取吸引對外融資和國外數字科技公司等方式,引導國外人才參與本國數字經濟建設,其中包括吸引在西方發達國家工作的東盟人才回流。由于數字經濟具有資本密集性、技術密集性和數據密集性相互疊加的特征,東盟大多數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和培訓系統尚無足夠的靈活性來應對這種變化,(38)James Manyika, Susan Lund, Jacques Bughin, Jonathan Woetzel, Kalin Stamenov, and Dhruv Dhingra,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February 24, 2016,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digital/our-insights/digital-globalization-the-new-era-of-global-flows.這也導致中國企業難以在當地找到合適的員工,企業的生存與獲益空間被大大壓縮。

表2 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排名
3.4 面臨其他國家的激烈競爭
自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總統以來,美國強化了與東盟的基礎設施合作。(39)劉飛濤:“美國‘印太’基礎設施投資競爭策略”,《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4期,第1-20頁。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印度尼西亞發表公開演講,提出美國要在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等方面與中國展開競爭,美國國會撥款600億美元組建國際發展金融公司,推動美國企業加強對東盟的投資。(40)陳菲:“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的建立及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挑戰”,《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第26-30頁。美國還宣布建立美國—東盟智能城市伙伴關系,旨在促進美國對東盟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刺激增長和發展,“加強東南亞的安全”。(41)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Pence in Southeast Asia: Ways forward for U.S.-ASEAN Cooperation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Brookings Institution,November 27, 201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11/27/pence-in-southeast-asia-ways-forward-for-u-s-asean-cooperation-on-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美國還通過夸大華為5G網絡安全問題阻擾東盟國家使用華為設備,逼迫東盟國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42)Brian Harding,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nd Southeast Asi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February 15,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digital-silk-road-and-southeast-asia.與此同時,日本、澳大利亞更是在美國的戰略框架內推進印太地區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在數字經濟等領域加強與東盟的合作。(43)“The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nounce Trilateral Partnership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Indo-Pacific”,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Australia, July 30, 2018, https://au.usembassy.gov/the-u-s-australia-and-japan-announce-trilateral-partnership-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in-the-indopacific.其中,日本戰后一直深耕東南亞地區,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與援助一直處于較高水平。日本為保持和鞏固其在東盟的經濟利益與戰略優勢,也進一步加大了在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的投資和援助力度。盡管中日兩國于2018年在泰國東部經濟走廊共同開展了關于智慧城市項目的第三方市場合作,但中日間在東盟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關系不會得到根本改觀。加之,美日在二十國集團(G20)等國際場合倡導“高質量基礎設施投資原則”,試圖謀求在數字經濟征稅、數據流動標準等方面的主導權,削弱中國數字“一帶一路”的先發優勢,加大了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阻力。(44)王凱、倪建軍:“‘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的路徑選擇”,《現代國際關系》,2019年第10期,第31頁。域內外國家加強與東盟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既有經濟收益的因素,也有同中國競爭數字標準制定權,以平衡中國在東盟地區影響力的考量。美日等國的競爭對中國推進與東盟的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造成了較大干擾和破壞。(45)趙明昊:“大國競爭背景下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態勢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2期,第4頁。
四、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的未來路徑
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挑戰與機遇并存,雙方應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2020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為契機,將搭建政策對接機制與平臺、制定發展規劃、加強人才培養、推動區域數字治理建設等作為未來數字“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與優先方向,推進各領域合作提質升級。
4.1 加快各方政策深度對接
中國與東盟需加強雙方在數字經濟領域的高層溝通,促進戰略對接,共同確定發展合作的方向,提升雙方合作的戰略協調性與契合度,通過設立高級別戰略對話、經貿高層對話、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等合作機制,持續深化政治互信,促進雙方合作共識,為雙方的合作提供更加適宜的政治基礎。針對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中國可采取靈活務實的對接策略,進一步明確各國發展定位,特別是數字技術創新的定位,在此基礎上形成差別化的協調發展格局。具體而言,針對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數字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在強化和鞏固現有對接的基礎上,中國可在科技金融、智慧城市、數字貿易、知識產權、數字治理等方面與其建立全方位對接機制。對于柬埔寨、老撾、緬甸等數字經濟發展基礎相對薄弱的國家,中國可以進一步挖掘這些國家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人才培養、電子商務等領域合作機制的廣度和深度,拓展新的合作機制。在區域層面,中國與東盟可進一步增加創新性制度設計與供給,通過深化政策對接機制,強化數字經濟合作機制的有效性,積極搭建更多戰略合作平臺,將數字經濟合作納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中國—東盟“10+1”合作及瀾湄合作等機制性會議議題,推動建立新的數字經濟合作機制與合作框架。在具體操作層面,中國可積極引導數字經濟領域企業實施更多的雙邊、多邊、第三方數字經濟合作項目,打造數字經濟發展的示范項目。在規則方面,雙方需加快完善跨境電子商務、數據跨境流動等領域的國際規則、法律規范、技術標準,以及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國際稅收政策。
4.2 共商數字經濟合作規劃
中國需加快完善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布局,做好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的整體設計與目標定位,提升規劃設計的系統性和前瞻性,通過強化中國與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的合作與聯系,促進區域資源要素高效匯聚與流動。積極推動中國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共同制定“數字‘一帶一路’與東盟合作發展規劃”,將其納入國家外交、科技、商務等國家間合作框架協議。圍繞東盟電子商務、移動支付、數字娛樂、在線旅游等數字經濟重點領域,(46)Jeff Desjardins, “Southeast Asia: An Emerging Market with Booming Digital Growth”, Visual Capitalist,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southeast-asia-digital-growth-potential/。中國需加快制定相關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明確雙方合作的路線圖、實施路徑及政府職責和企業規范,注重各項政策措施銜接配合與項目落地,為企業“走出去”、開展重點領域合作提供指導。同時,可進一步突出中國與東盟各國以數字鏈推動產業鏈、創新鏈發展,形成“數字鏈、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四鏈融合協同發展,將數字經濟規劃編制融入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和新興產業合作的各個環節,加快推動雙方產業升級。中國需根據東盟各國國情差異與經濟發展水平,準確評估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和現實需求,與東盟及其成員國共同制定并實施差別化、精準化的數字經濟行動路徑,推進政策創新與精準施策。中國需聚焦合作的重點領域和重點國家,有針對性地推進中國與相關國家開展合作,其中,可進一步加大對老撾、緬甸、柬埔寨等周邊國家數字經濟規劃編制的援助力度。此外,基于參與數字經濟行為體呈現多元化的現狀,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要積極發揮國際組織的作用,加強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金磚銀行等國際組織的合作,與東盟共同開展數字經濟相關規劃編制和項目設計工作。
4.3 創新數字經濟人才培養模式
中國與東盟可將人才培養作為雙方數字經濟合作的優先議題,共同建立數字經濟和相關治理的知識體系,(47)Zhai Kun and Yang Xueying,“Empower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hina Daily, November 25, 2019.強化中國與東盟人才結構和數字產業的合理匹配,推進人才鏈與數字鏈、創新鏈協同配合。中國可根據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特點,推動構建深度融合的科教互利合作共同體,加強中國高校與東盟各國高校和教育機構聯建數字經濟特色學科、專業和培教基地,搭建人才培養、科技研發平臺載體,在課程研發、教師培訓、人才認證、職業服務等方面為東盟各國提供優質教育服務。中國可加強與相關國際組織和各類教育服務機構的聯系,推動其參與中國—東盟數字經濟人才教育合作,搭建多層次專業化培訓體系,聯合當地華人科技公司共同開辦培訓機構,開發適應東盟各國語言、宗教文化的網絡教程和課程體系,提升數字素養和應用技能。同時,進一步創新合作培養人才新模式,以在東盟地區開展數字經濟業務的重點企業作為依托,在重點國家設立數字經濟海外辦學機構和職業培訓基地。通過市場化力量為東盟國家提供數字經濟培訓項目,強化技能實訓環節設計,為相關培訓企業提供信貸優惠、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提高企業參與數字經濟人才培養的積極性。為進一步強化東盟數字經濟高端人才支撐,中國與東盟可考慮共建跨境科技園區、數字經濟小鎮、技術研發和轉移中心等平臺,積極引導中國科研機構與東盟國家在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領域開展技術交流和項目合作,聯合開展技術攻關、創新研發和技術合作等,推動其成為高端人才集聚地和龍頭企業研發策源地。雙方可探索建立中國與東盟各國數字經濟人才跨境交流機制,推動與相關國家開展雙邊或多邊學歷學位、技術職業資格的關聯互認,放寬東盟數字經濟人才在中國開展相關行業市場準入的執業限制。中國政府可加大對東盟數字人才培養的政府援助力度,在“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下設立中國—東盟數字經濟人才培養專項。
4.4 推進區域數字治理
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建設要摒棄“先發展后治理”的治理老路,突出“邊發展邊治理”理念,推動數字技術與治理理念深度融合。中國可憑借在民生服務、社會安全、災害預測、應急管理等領域數字技術應用的優勢,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東盟各國的示范與應用。在治理框架和治理模式上,雙方盡快建立中國—東盟數字治理框架,提升數據治理的規范化、標準化與協同性,共同探索政府、企業、平臺和個人等多方參與及多元治理的區域數字經濟治理新模式。雙方可建立雙邊、多邊綜合性協調機構負責數字經濟治理問題,將數字治理融入現有雙邊和多邊法律法規、貿易協定,以及條約與全球標準之中。在網絡空間治理上,雙方可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的網絡空間,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推動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完善網絡安全與數據保護機制,提升數據流通安全性,努力開創網絡空間安全的國際治理新格局。(48)張耀軍、宋佳蕓:“數字‘一帶一路’的挑戰與應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第38頁。在數字沖突管控上,中國與東盟各國可進一步增強數字信任和數字安全,加大管控數字沖突力度,妥善處理數字貿易摩擦、個人隱私數據、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打擊網絡犯罪等問題。(49)“大力發展‘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光明日報》,2018年4月26日。由于技術的快速迭代,數字經濟在不同階段呈現不同的治理熱點和難點,需要中國與東盟加快縮小技術與政策之間的差距。(50)“To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isation, Southeast Asia Need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echnology 4.0 and Policy 1.0”, OECD, August 24, 2017, https://www.oecd.org/newsroom/to-seize-the-opportunities-of-digitalisation-southeast-asia-needs-to-close-the-gap-between-technology-4-0-and-policy-1-0.htm.在治理主體上,雙方可充分發揮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國際組織的作用,推動數字治理建設,促進國家間相關標準的互換互認,聯合東盟國家共同制定國際標準,完善數字經濟國際標準體系。在治理規則上,中國與東盟各國可共同參與數字經濟領域的相關國際規則制定,共同提升發展中國家對數字治理問題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4.5 防范和對沖其他國家的干擾
中國需繼續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體現親、誠、惠、容的理念,進一步深化與東盟各國的關系,積極回應東盟的安全訴求和合作信號,防范和避免“場外因素”影響中國與東盟各國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一方面,中國政府需采取對沖措施,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藍點網絡”計劃、打壓華為公司、渲染網絡安全等對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產生的干擾。另一方面,盡管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比較優勢不盡相同,各方在與東盟數字經濟開展合作時存在競爭,但很多方面是互補的,甚至是可以合作的。針對其他國家的干擾,中國可創新溝通與合作方式,采取靈活有效的差異化策略。例如,對于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中國可就數字“一帶一路”倡議與其數字經濟戰略進行戰略調適,協調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利益沖突,弱化“對抗”意圖,避免在東盟地區形成戰略對抗,爭取形成由競爭向競合轉變的良性互動。而對于韓國和俄羅斯等國,中國可尋求多方共贏和最大利益契合點,共同建立良好的產業生態,鼓勵數字企業采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模式,與其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避免惡性競爭,共同參與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進程。
五、結 語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深化中國—東盟合作是促進東盟乃至東亞地區發展的最佳路徑。(51)張群:“東亞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與中國—東盟合作”,《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5期,第44頁。數字“一帶一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中國與東盟進一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新實踐。近年來,中國與東盟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合作進展迅速,合作領域和層次不斷深化與豐富,現有合作的基礎也更加牢固。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催生出中國與東盟在數字經濟領域新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中國與東盟的數字經濟合作進入關鍵時期,面對雙方在當前合作中的現實挑戰,加強與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的全方位對接和合作,促進雙方在數字基礎設施、人才培養、產業培育、穩妥應對美日等大國競爭方面進行合作,可作為未來的重點方向。可以預見,隨著中國—東盟數字“一帶一路”合作進程加快推進,雙方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建設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