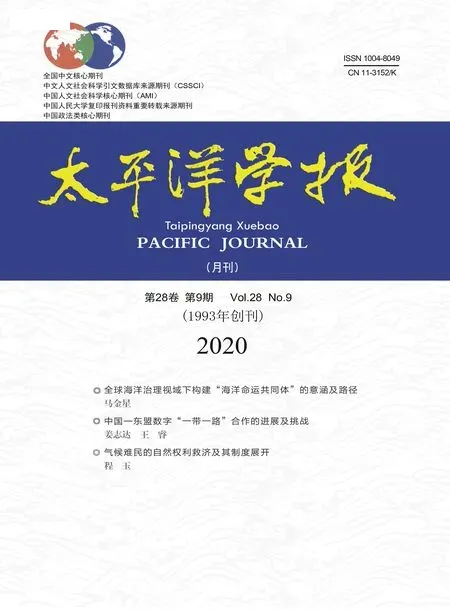論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實踐困境與國際立法要點
王金鵬
(1.中國海洋大學,山東 青島266100)
長時間以來,在陸地環境保護中保護珍稀瀕危物種的棲息地或者特定景觀與空間被證明是恰當的措施。(1)Paul F.J. Eagles, Stephen F. McCool, and Christopher D.A. Haynes, Sustainable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Guidelines for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UCN, 2002, pp.5-8.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科學技術逐漸發展,人類對海洋認知加深,海洋漁業、海底石油和礦產開發日益蓬勃,“海洋革命”隨之興起。(2)Carleton Ray, “Ecology, Law and the ‘Marine Revolu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Vol.3, No.1, 1970, p.7.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人類對海洋的破壞也日漸嚴重,(3)Committee on the Evaluation, Design, and Monitoring of Marine Reserve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Ocean Studies Board, Commission on Geosciences, Environment,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Marine Protected Areas: Tools for Sustaining Ocean Ecosystems,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1, pp.146-147.國際社會借鑒陸地環境保護的經驗,逐漸開始通過設立海洋保護區保護海洋環境。世界自然保護聯盟(4)“Protection of the Coastal and Marine Environment”, Resolution 17.38 of the IUCN General Assembly, 1988,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efiles/documents/GA-17th-011.pdf, p.105.、《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5)“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COP/DEC/VII/5, April 13, 2004,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07/cop-07-dec-05-en.pdf, p.2, note 1.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6)FAO, “FAO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No. 4, Suppl. 4, Fisheries Management. 4. Marine Protected Areas and Fisheries”, 2011, http://www.fao.org/3/i2090e/i2090e.pdf, p.9.等先后提出了海洋保護區的不同定義。目前,尚沒有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海洋保護區的定義,但通常認為海洋保護區概念的核心是指在一定的海域,采取更為嚴格的措施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棲息地或生態系統。(7)Robin Churchil, “The Growing Establishment of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mplication for Shipping”, in Richard Caddell, D. Rhidian Thomas, eds., Shipping, Law and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Emerging Challenges for the Law of the Sea-legal Implications and Liabilities, Lawtext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pp.56-57.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海洋保護區被建立,但《生物多樣性公約》科學、技術和工藝咨詢附屬機構在2010年的評估中發現全球海洋中僅有0.5%的海洋被保護,且其中絕大部分海洋保護區處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內。(8)“Report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of Work on Marine and Coastal Biological Diversity”, UNEP/CBD/SBSTTA/14/INF/2, April 14, 2010, https://www.cbd.int/doc/meetings/sbstta/sbstta-14/information/sbstta-14-inf-02-en.pdf, paras.135, 161.國際社會也認識到了海洋保護的不足。2010年在日本愛知縣舉辦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愛知目標”的目標11提出,到2020年應有“10%的沿海和海洋區域,尤其是對于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區域,通過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態上有代表性和相連性好的保護區系統和其他基于保護區的有效保護措施得到保護”。(9)“2011—2020年《戰略計劃草案》和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UNEP/CBD/COP/10/DEC/X/2, October 29, 2010, https://www.cbd.int/doc/decisions/cop-10/cop-10-dec-02-zh.doc, p.9.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14“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中也規定,“到2020年,根據國內和國際法,并基于現有的最佳科學資料,保護至少10%的沿海和海洋區域”。
作為全球海洋治理最重要的法律框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把海洋空間分為若干區域。其中的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根據《公約》,公海適用公海自由原則。任何國家不得有效地聲稱將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權之下。國際海底區域及其資源是人類共同繼承財產,任何國家不對國際海底區域的任何部分或其資源主張或行使主權或主權權利。(10)《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9、136、137條。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約占全部海洋的64%。(11)Nilufer Oral,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Marine Ecosystem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Can International Law Meeting the Challenge”, in Anastasia Strati, Maria Gavouneli, Nikolaos Skourtos, eds., Unresolve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to the Law of the Sea: Time Before and Time Aft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p.85.隨著人類海洋科技和開發能力的不斷發展,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日益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12)林新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管理”,《太平洋學報》,2011年第10期,第95-96頁。非法、未報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撈(簡稱IUU捕撈)等漁業活動,海上傾廢,航運等帶來一系列不良影響,威脅了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存續,導致生物多樣性的喪失。(13)Kristina M. Gjerde, “UNEP Regional Seas Report and Studies No. 178, Ecosystems and Biodiversity in Deep Waters and High Seas”, UNEP/IUCN, 2006,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13602/rsrs178.pdf?sequence=1&isAllowed=y, pp.22-30.氣候變化也威脅著海洋生物,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14)IPCC,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2019,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3/2019/12/SROCC_FullReport_FINAL.pdf, pp.450-456.將海洋保護區作為養護生物多樣性的管理工具引入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成為國際社會可能的選擇。(15)白佳玉、李玲玉:“北極海域視角下公海保護區發展態勢與中國因應”,《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4期,第24頁。一些國家在區域法律框架下開始了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探索。目前這些探索面臨著明顯的困境和激烈的爭議。本文中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是指在公海或國際海底區域劃定的采取養護與管理措施保護物種及其棲息地或生態系統等的界線明確的海域。(16)本文沒有采用“公海保護區”的概念,原因在于“公海保護區”概念并不能涵蓋現有的既包括公海也包括國際海底區域的海洋保護區實踐,例如東北大西洋米爾恩海山復合區海洋保護區(Milne Seamount Complex Marine Protected Area)和查理·吉布斯南部海洋保護區(Charlie Gibbs South Marine Protected Area)。此外,BBNJ國際協定擬適用的范圍不僅包括公海,也包括國際海底區域。所以相對于“公海保護區”,“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概念能夠更好地概括現有實踐,也更符合BBNJ國際協定制定的初衷。聯合國大會框架下正在進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問題的協定(以下簡稱BBNJ國際協定)的政府間會議,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是其核心議題之一。本文將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現有實踐進行闡述,分析這些實踐面臨的主要困境,繼而結合在聯合國大會框架下正在進行的BBNJ國際協定談判,提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立法的要點,并就相關規則擬定提出建議。
一、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概況
現有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包括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CCAMLR)分別于2009年和2016年設立的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和羅斯海保護區,以及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OSPAR委員會)分別于2010年和2012年設立的共計七處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17)法國、意大利與摩納哥于地中海設立的派拉格斯保護區(The Pelagos Sanctuary for Mediterranean Marine Mammals)西部也曾包括公海部分。但根據“2003年4月15日關于在共和國領土周邊建立生態保護區的第2003-346號法律”和“2004年1月8日關于在共和國地中海領土周邊建立生態保護區的第2004-33號行政法令”,法國宣布在地中海設立生態保護區,其覆蓋了派拉格斯保護區的部分區域。法國在生態保護區內可對非法排放的外國船舶課以罰金。根據“2011年10月27日的第209號總統令”,意大利宣布在地中海西北部、利古里亞海和第勒尼安海設立生態保護區。根據“2012年10月12日關于在共和國地中海領土周邊建立專屬經濟區的第2012-1148號行政法令”,法國宣布了其在地中海區域的專屬經濟區。法國和意大利設立的相關生態保護區和專屬經濟區已覆蓋了派拉格斯保護區的原有公海部分,本文認為派拉格斯保護區已非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故未將其納入分析。
1.1 南極海洋保護區
1959 年《南極條約》第4條成功“凍結”了長期以來的南極大陸主權紛爭。(18)陳力:“論南極海域的法律地位”,《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5期,第150頁。《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是南極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規則,與《南極條約》一同成為南極條約體系最重要的兩個支撐。《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規定設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履行確定養護需求,制定、通過和修訂養護措施等職責。相關養護措施包括在公約適用范圍內為養護目的確定禁捕區域等。2008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確定了11個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優先區域。(19)CCAMLR, “Report of the Twenty-Seven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ctober 27-31, 2008, https://www.ccamlr.org/en/system/files/e-sc-xxvii.pdf, para.7.2(vi).2009年為保護漁業第48.2分區內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設立了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SOISS MPA)。(20)CCAMLR, “Report of the Twenty-Eigh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ctober 26- November 6, 2009, https://www.ccamlr.org/en/system/files/e-cc-xxviii.pdf, para.12.86.2011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通過了“關于建立《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下海洋保護區的總體框架”。(21)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 91-04 (2011), General Frame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CAMLR Marine Protected Areas”, https://www.ccamlr.org/sites/default/files/91-04_6.pdf, 訪問時間:2020年4月16日。.2016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又通過了設立面積約155萬平方千米的羅斯海保護區的決議(Ross Sea MPA)。羅斯海保護區的目的包括:保護重要的物種棲息地;監測自然變化以更好地了解南極的生態系統;促進關于海洋生物資源的研究與包括監測在內的相關科學活動。羅斯海保護區由三部分組成:一是由三個區域組成的一般保護區,二是特別研究區, 三是磷蝦研究區。(22)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 91-05 (2016): Ross Sea Region Marine Protected Area”, https://www.ccamlr.org/sites/default/files/91-05_11.pdf, 訪問時間:2020年4月21日。.
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和羅斯海保護區均對漁業活動進行限制。前者禁止除科學研究以外的漁業活動(23)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 91-03(2009): Protecting of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Southern Shelf”, https://www.ccamlr.org/sites/default/files/91-03_9.pdf, 訪問時間:2020年4月29日。,后者的約占總面積72%的一般保護區內禁止漁業活動。在羅斯海保護區特別研究區內可基于研究目的進行捕撈,但要遵守相關養護措施中規定的捕撈限額。在磷蝦研究區和特別研究區捕撈南極磷蝦還應遵守“南極磷蝦探捕的一般措施”(24)CCAMLR, “Conservation Measure 51-04 (2016): General Measure for Exploratory Fisheries for Euphausia Superba in the Convention Area in the 2016/17 season”, https://www.ccamlr.org/sites/default/files/51-04_35.pdf,訪問時間:2020年5月3日。的相關規定。此外,兩個保護區內均禁止漁船傾廢和轉運活動。在海上交通監測方面,兩個保護區均鼓勵經過的漁船向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秘書處提供船旗國、船舶型號、國際海事組織的識別碼和航線等信息。兩個保護區有一點顯著的不同,即是否明確設置了“日落條款”。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僅規定每五年進行一次評估,而羅斯海保護區則明確規定將持續35年,在2052年進行評估從而決定是否撤銷或延續保護區,或者根據需要采取新的養護措施。
1.2 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
《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公約》的適用范圍中約有40%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域。(25)B.C.O’ Leary., et al., “The First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Ps) in the High Seas: The Process, the Challenges and Where Next”, Marine Policy, Vol.36, No.3, 2012, p.599.《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公約》要求締約方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來保護海洋區域不受人類活動的負面影響,繼而保護人類健康與海洋生態系統,修復被損害的海洋區域。(26)The Article 2(1)(a) of the OSPAR Convention.2003年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成員方作出了在東北大西洋海域建立具有生態一致性且管理完善的海洋保護區網絡的政治承諾。(27)OSPAR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2003/3 on a Network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https://www.ospar.org/convention/agreements?q=marine%20protected%20areas, 訪問時間:2020年5月3日。2010年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網絡,包括米爾恩海山復合區海洋保護區、查理·吉布斯南部海洋保護區、阿爾泰海山公海保護區、安蒂阿爾泰公海保護區、約瑟芬海山公海保護區、亞速爾群島北部大西洋中脊公海保護區。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于2012年又新增設立了查理·吉布斯北部公海保護區。(28)OSPAR Commission, “MP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ttps://www.ospar.org/work-areas/bdc/marine-protected-areas/mpas-in-areas-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 訪問時間:2020年5月3日;中文譯名參考范曉婷主編:《公海保護區的法律與實踐》,海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頁。這七個保護區面積共計約46萬平方千米。(29)OSPAR Commission, “Key Figures of the MPA OSPAR Network”, http://mpa.ospar.org/home_ospar/key_figures, 訪問時間:2020年5月3日。
根據其覆蓋范圍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可以分為三類:(1)既包括公海部分又包括國際海底區域部分的米爾恩海山復合區海洋保護區和查理·吉布斯南部海洋保護區;(2)僅包括公海部分的查理·吉布斯北部公海保護區,其下的海底部分屬于冰島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提交大陸架外部界限劃界案的范圍且尚未采取保護措施;(3)僅包括公海部分的其余四個海洋保護區,其下的海底部分屬于葡萄牙提交的大陸架外部界限劃界案的范圍并已由葡萄牙采取了保護措施。在保護區內采取的管理措施方面,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僅通過了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建議。(30)OSPAR Recommendation 2010/12, 2010/13, 2010/14, 2010/15, 2010/16, 2010/17 and 2012/1, https://www.ospar.org/work-areas/bdc/marine-protected-areas/mpas-in-areas-beyond-national-jurisdiction, 訪問時間:2020年5月3日。審視這些建議可以發現,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措施主要是提升保護意識,鼓勵相關信息和知識共享,支持關于人類影響和保護措施的科學研究,促進保護區管理措施為公眾知曉,通過與非締約方合作和參與其他國際組織促進保護區目標的傳播等鼓勵性和促進性的措施。
二、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的困境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現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均是在區域性法律框架下由相關國際組織在其管轄和職權范圍內設立的。但由于設立這些海洋保護區所依據的國際協定在一些方面的有效性及其設立與管理過程存在問題,這些實踐面臨著明顯的困境。
2.1 合法性的質疑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設立通常意味著對其中特定人類活動進行限制或禁止。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設立海洋保護區并執行相關管理措施可能與公海自由產生沖突,影響捕魚自由和航行自由等。(31)Sarah Wolf, Jan Asmus Bischoff, “Marine Protected Area”,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013.有學者甚至將“部分沿海國和國際組織推動設立公海保護區”稱為“新海洋圈地運動”,認為海洋保護區的設立旨在“限制其他國家在該海域開展科學研究和資源勘探等活動”,保護其“業已獲得的利益”。(32)丘君:“悄然興起的‘新海洋圈地運動’”,《中國海洋報》,2012年3月2日,第4版;劉明周、藍翊嘉:“現實建構主義視角下的海洋保護區建設”,《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7期,第87頁。可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面對的主要合法性挑戰即在于為實現海洋保護區的目的或宗旨,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措施會對在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的相關活動進行限制,可能會影響現有海洋法秩序已確立的相關國家在公海或國際海底區域中的捕魚或資源勘探開發等權利。實踐中有些國家也質疑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這些質疑主要集中于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國際組織沒有相關權限或缺乏法律依據。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國對南極海洋保護區合法性的質疑。俄羅斯和烏克蘭質疑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權力,認為《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沒有規定海洋保護區的定義或相關的保護措施。烏克蘭質疑在公海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法律基礎,認為“《公約》規定了締約國在其管轄范圍以內建立海洋保護區,但目前法律上沒有看到任何建立公海保護區的可能性”。(33)CCAMLR, “Report of the Second Special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July 15-16, 2013, https://www.ccamlr.org/en/system/files/e-cc-sm-ii_1.pdf, paras.3.18 and 3.26.此外,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的一些成員方也質疑建立海洋保護區是否有實際意義,以及保護區設立提案所依據的科學信息是否充分。(34)同③, paras.3.57 and para.3.23.有學者也認為設立大規模的南極海洋保護區可能使主要職責為漁業管理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無力應對更加緊迫的挑戰,包括日益擴大的南極磷蝦捕撈。(35)Cheryle Hislop, Julia Jabour, “Quality Counts: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Ocean Yearbook, Vol.29, 2015, p.191.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作為其海洋保護區網絡的一部分也引發了對其合法性的討論,包括對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是否有權限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域設立海洋保護區的質疑。(36)Erik J. Molenaar, Alex Oude Elferink,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e Pioneering Efforts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 Utrecht Law Review, Vol.5, No.1, 2009, p.17.
2.2 管理的碎片化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的另一個明顯困境是管理的碎片化。呈現管理碎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相關主管機構的職權分散,即不同的海洋活動往往由不同的國際組織負責管理。這些相關國際組織在規制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的人類活動中通常只有特定方面的權力,因而需要尋求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才能實現基于生態系統的海洋環境保護與管理。然而由于這些國際組織有著不同的宗旨和不同的成員方,合作并不容易達成。例如在南極,商業捕魚由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負責管理,而科學研究、旅游或其他活動則受《南極條約》及其議定書的規制。(37)Lora L. Nordtvedt Reeve, Anna Rulska-Domino, Kristina M. Gjerde, “The Future of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cean Yearbook, Vol.26, 2012, pp.284-285.即便在漁業管理方面,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仍需要與條約適用范圍之外的其他漁業管理機制進行協調,包括《南方藍鰭金槍魚養護公約》、中西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和《保護信天翁和海燕協定》等。通過長時間的協調,這些組織間已可以相互作為觀察員參加彼此的會議,還可通過秘書處之間定期的郵件往來實現信息交換。但是這些安排仍然被限定在協同行動的范圍內,其有效性有賴各自秘書處之間的交流,還無法通過對特定議題進行協商的正式會議實現合作與協調。(38)Julien Rochette, et al., “The Regional Approach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Marine Policy, Vol.49, 2014, p.114.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海域人類活動的管理也涉及不同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組織。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OSPAR委員會)規制海洋科學研究、管道鋪設、傾廢、設施和人工島嶼建設等人類活動,也有權評估和監測人類活動對海洋環境的影響。但目前對東北大西洋海洋生物多樣性影響最顯著的活動包括漁業和航運活動。東北大西洋漁業活動主要由東北大西洋漁業管理委員會(NAFAC)管理,航運活動則主要由國際海事組織(IMO)管理。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與它們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尚不充分。盡管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和東北大西洋漁業管理委員會的咨詢機構都是國際海洋勘探理事會(ICES),但兩者的管理措施并不協調。其后在國際海洋勘探理事會的建議下,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劃定的海洋保護區才開始與東北大西洋漁業管理委員會禁止底拖網捕撈的區域有重疊。(39)阿爾泰海山公海保護區、安蒂阿爾泰海山公海保護區和亞速爾群島北部大西洋中脊公海保護區有禁止底層拖網捕魚的區域。See “NEAFC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OSPAR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Document Intended for OSPAR-Madeira II Workshop, January 9, 2012, http://www.aires-marines.fr/Media/Agence/Fichiers/Divers/Management-NEAFC-OSPAR-Madere.此外,目前尚沒有任何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被國際海事組織認定為特別敏感海域和特殊區域。
2.3 與沿海國權利的沖突
海洋不會被人為劃設的邊界而隔離,國家管轄范圍內外海域是相互聯系的。位于公海或國際海底區域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設立和相應養護措施的實施可能與沿海國在其鄰近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上特定的海洋活動與相關權利發生沖突。鄰近沿海國也可能會為自身利益采取與海洋保護區相沖突的措施。例如,冰島沒有對查理·吉布斯北部公海保護區下的屬于其外大陸架的海床和底土采取任何保護措施,而其在這些海床和底土的開發利用活動會對保護區造成影響。此外,即便沿海國采取保護措施,也需要與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所采取的措施相協調才能避免沖突。如前所述,四個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下的海床和海底的部分屬于葡萄牙提交的大陸架外部界限劃界案的范圍。雖然大陸架外部界限尚未明確,但葡萄牙在相應海床及底土設立了海洋保護區。這實際上擴大了葡萄牙管轄權覆蓋的地理范圍(40)Marta Chantal Ribeiro, “Marine Protected Areas: The Case of the Extended Continental Shelf”, in Marta Chantal Ribeiro, ed., 30 Years after the Signa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imbra Editora S.A, 2014, p.197.,例如葡萄牙政府在海洋保護區建立后開始監督這些區域的礦產資源勘探活動。(41)Marta Chantal Ribeiro, “The ‘Rainbow’: The First National Marine Protected Area Proposed Under the High S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5, No.2, 2010, p.190.葡萄牙所采取的具體管理措施需要與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在相應公海保護區采取的措施進行協調,否則水層與其下海床和底土所采取的措施相互沖突會導致該海域生態綜合管理無法實現。
2.4 非締約方的忽視
公海自由和船旗國管轄已成為海洋法的重要規則。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的規定,在締約方同意的基礎上可對懸掛締約方國旗的船舶實施限制,但這種限制通常不能約束非締約方。換言之,如果目前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宣布設立一處海洋保護區,其僅適用于同意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國家,非締約方可忽視海洋保護區所采取的措施。(42)Petra Drankier, “Marine Protected Area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7, No.2, 2012, p.295.但是如果非締約方在這些海域從事威脅生物多樣性的活動,這些海洋保護區可能會起不到保護的效果。此外,僅要求締約方實施嚴格限制會使締約方與非締約方相比面臨不公和劣勢,非締約方則可“搭便車”,繼而導致締約方也不愿實施或遵守限制措施,最終導致海洋保護區起不到實效。典型的例子是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成員方僅愿意為七處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制定不具有約束力的建議性措施。在這種背景下,現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主管組織均呼吁非締約方能注意到保護區內采取的措施,試圖促使非締約方也認可這些措施。例如,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在有關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決定和建議中都呼吁非締約方認可保護區的保護原則和目標。不過這些呼吁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保護區的主管組織在現有國際法框架下采取養護措施,不得妨礙或損害非締約方的合法權利。正如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要求管理海洋保護區所實施的措施應符合國際法,不損害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根據《公約》和習慣國際法享有權利和義務。(43)OSPAR Commission, “Decision 2010/1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ne Seamount Complex Marine Protected Area”, https://www.ospar.org/documents?v=32821, 訪問時間:2020年5月6日。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難以影響非締約方,而這會削弱其實現保護目標的能力。(44)Erik J. Molenaar, Alex Oude Elferink,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e Pioneering Efforts under the OSPAR Convention”, Utrecht Law Review, Vol.5, No.1, 2009, p.19.與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不同,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作為在其適用范圍內具有漁業管理職能的國際組織,有權在防止非法、未報告及不受管制的捕撈活動等漁業管理方面采取措施促進非締約方遵守其相關養護措施。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也在其設立的南極海洋保護區的養護措施中規定了促進非締約方注意相關養護措施,例如對于有國民或船舶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公約》所管轄海域開展活動的非締約方,提請其注意羅斯海保護區的養護措施。但如上所言,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成員國在內的國家對南極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的質疑損害了其提請非締約方注意的實際效果。
2.5 監測與評估的困難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的困境還包括對其及采取相關措施的監測與評估存在困難。其一是因為設立海洋保護區的管理機構不重視通過監測與評估了解海洋保護區的實際效果;其二是因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常遠離陸地,對其所采取措施的效果進行監測與評估的成本較高,締約方不愿付出額外的高昂成本。目前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沒有采取有法律拘束力的措施,也缺乏監測和評估的要求。即便在管理機構相對完善的南極海洋保護區,其監測和評估也面臨明顯的困難。例如根據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設立時每五年進行一次評估的要求,歐盟于2014年9月提交了對該保護區相關養護措施的實施效果的評估。(45)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view of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Southern Shelf MPA (MPA Planning Domain 1, Subarea 48.2)”, CCAMLR-XXXIII/24, 2014.但該評估中僅指出,五年時間不足以評定該區域生物多樣性特征的變化,既有的措施將不做調整。截止2019年,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也仍未通過針對已設立10年的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的研究與監測計劃(RMPs)。(46)CCAMLR, “Report of the Thirty-eighth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ctober 21-November 1, 2019, https://www.ccamlr.org/en/system/files/e-cc-38_1.pdf, para.6.26.由此可見,南奧克尼群島南大陸架海洋保護區所采取養護措施的效果尚無法判斷。而羅斯海保護區養護措施的實施情況與效果更有待進一步觀察。缺乏監測與研究計劃,往往無法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及其采取的措施的實際效果進行考察,也無法了解是否實現了其設定的目標,而這違背了設立海洋保護區的初衷。由于監測與評估困難,有學者指出,有些海洋保護區僅能提供“虛假的安全感”,缺乏確保養護措施得到執行的能力。(47)Cheryle Hislop, Julia Jabour, “Quality Counts: High Sea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Ocean Yearbook, Vol.29, 2015, p.185.
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立法的要點
200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59/24號決議,成立了“研究關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和可持續利用問題的不限成員名額特設工作組”,對包括海洋保護區在內的劃區管理工具等重要議題進行討論。基于該特設工作組的建議,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69/292號決議決定,根據《公約》的規定就BBNJ問題擬訂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文書(BBNJ國際協定)。(48)“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9 June 2015”, UN Doc A/RES/69/292, July 6, 2015, para.1.在2016年和2017年四次籌備委員會會議后,2018年BBNJ國際協定政府間會議在紐約召開,正式開啟協定磋商談判進程。迄今政府間會議已進行三次,第四次政府間會議將于2020年召開。(49)歷次政府間會議的信息參見“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an International Legally Binding Instru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ttps://www.un.org/bbnj/, 訪問時間:2020年5月9日。國際社會針對BBNJ國際協定的談判協商已進入關鍵階段。如果BBNJ國際協定得以成功制定,其將是《公約》下的第三個執行協定,(50)王勇、孟令浩:“論BBNJ 協定中公海保護區宜采取全球管理模式”,《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5期,第1頁。這可能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國際環境立法之一,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51)Dire Tladi,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and the Proposed Treaty on Biodiversity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The Choice between Pragmatism and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Vol.25, No.1, 2014, p.131.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與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分別設立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可以為BBNJ國際協定中海洋保護區方面的立法提供借鑒。本文將圍繞現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的困境,結合BBNJ國際協定談判,分析其國際立法的要點。
3.1 構建合法性基礎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區域性實踐面臨的合法性質疑,可以為BBNJ國際協定建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全球性規則提供啟示。BBNJ國際協定需要構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基礎,而這也有助于特定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保護區的建設。例如有學者指出,南極海洋保護區建設的進展尚有待全球層面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制度的制定。(52)Laurence Cordonnery, Alan D. Hemmings, Lorne Kriwoken, “Nexus and Imbroglio: CCAMLR, the Madrid Protocol and Designating Antarctic Marine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ern O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30, No.4, 2015, p.764.BBNJ國際協定中關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規定可使其全球范圍內數量廣泛的締約方認可在其框架下設立的保護區的合法性,并遵守相應管理或養護措施。為構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基礎,BBNJ國際協定應重點對需要保護的區域的標準和科學基礎、提案與決策等具體事項進行明確規定。在標準和科學基礎方面,在滿足風險預防方法和生態系統辦法等要求的基礎上,應考慮到不同海域所面臨不同的環境威脅,擬定具有靈活性的標準。在提案與決策方面,應規定由BBNJ國際協定的締約國提案,在特定的科學技術機構評估的基礎上由締約方大會進行決策。BBNJ國際協定還應通過實現各國普遍的參與、締結或接受來夯實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屬于沒有具體權屬的生物資源,資源沒有權屬往往會導致個人或組織缺乏足夠激勵來防止其經濟價值縮減或增進其價值。(53)A. Mitchell Polinsky Steven Shavell,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North Holland, 2007, p.818.為促進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BBNJ國際協定需要各國的普遍參與以防止“公地悲劇”和避免“搭便車”。BBNJ國際協定案文草案序言中“渴望實現普遍參與”的措辭也表明了這一點。(54)“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 Doc A/CONF.232/2020/3, November 18, 2019.各國的普遍參與也將有助于使海洋保護區不僅停留在紙面上,而能采取有效的養護或管理措施。例如相較于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權限范圍內南極海洋保護區采取了明確的漁業限制措施,其原因之一在于南極海洋生物資源養護委員會的成員方囊括了在南大洋進行漁業活動的主要國家。在協商一致的前提下,這些國家都公平地遵守南極海洋保護區采取的養護措施。為促進各國的普遍參與,除了要求海洋保護區提案需經協商一致通過外,還可在BBNJ國際協定案文中規定允許締約方對于特定條款做出排除或例外聲明。
3.2 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國際協定磋商應強調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公約》第197條、117條和118條表明,各國有合作保護海洋環境與養護公海生物資源的義務。2001年國際海洋法法庭在MOX Plant案中表明,“合作的義務是在《公約》第12部分和一般國際法下防止海洋環境污染的一項根本原則”。(55)ITLOS, Order of 3 December 2001, Joint Declaration of Judges Caminos, Yamamoto, Park, Akl, Marsit, Eiriksson and Jesus on the MOX Plant Case (Ireland v. United Kingdom).據此,秉持善意進行合作以應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生物多樣性面臨的威脅和風險是各國的法律義務。(56)Tullio Scovazzi,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the High Seas: Some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19, No.1, 2004, p7.如前所述,現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著管理碎片化帶來的困境。聯合國大會框架下就BBNJ問題的討論也注意到管理碎片化帶來的挑戰。早在工作組會議中,就有與會者指出,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擁有不同職權的政府間組織和機構之間務必進行合作與協調。(57)“Letter dated 15 May 2008 from the Co-Chairpersons of the Ad Hoc Open-ended Informal Working Group to Stud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Beyond Areas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Doc A/63/79, May 16, 2008, para.24.現有BBNJ國際協定案文草案第6條專條規定了國際合作,對加強BBNJ國際協定與其他機構及其成員之間的合作,以及必要時設立新的機構等做出了原則性規定。BBNJ國際協定案文草案在“包括海洋保護區在內的劃區管理工具”部分中也規定“締約國應為協商和協調做出安排”,以加強合作和相關機構所采取的措施之間的協調。(58)同①。不過協定沒有規定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的具體途徑。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推動的軟法協議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鑒。(59)Ingrid Kvalvik, “Managing Institutional Overlap in the Protection of Marine Ecosystems on the High Seas: The Case of the North-East Atlantic”,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Vol.56, 2012, pp.35-43.東北大西洋海洋環境保護委員會與東北大西洋漁業管理委員會簽署了“東北大西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特定海域主管國際組織合作與協調的協議”(60)OSPAR Agreement 2014-09 (Update 2018), “Collective Arrangement Between Competen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on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Regarding Selected Areas in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n the North-East Atlantic”, https://www.ospar.org/documents?v=33030, 訪問時間:2020年5月9日。,旨在將東北大西洋海域相關國際組織納入一個協同管理計劃,以促進該海域的協同管理。(61)OSPAR Commission, “Summary Record of Meeting of the OSPAR Commission”, 20-24 June 2011, https://www.ospar.org/meetings/archive/ospar-commission-please-note-change-of-date-for-ospar-2011, Annex 15.通過不同機構或成員之間的正式協議來加強關于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管理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將有利于應對管理碎片化帶來的困境。
3.3 適當顧及沿海國權利
應對與沿海國權利的可能沖突也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立法的要點之一。在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設立的海洋保護區的良好管理有賴于毗鄰的沿海國的配合,而沿海國在國際法下享有的合法權利和利益也應被“適當顧及”(due regard)。在BBNJ國際協定案文草案中規定“不應損害沿海國在毗鄰的本國管轄范圍以內區域所采取的措施的效力,應適當顧及《公約》相關條款所反映的各國的權利、義務和合法利益”也體現了這一點。(62)“Revised Draft Text of an Agreemen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UN Doc A/CONF.232/2020/3, November 18, 2019.“適當顧及”一般指要求適當、公正、合理地對待其他國家的權利。(63)張衛華:“專屬經濟區中的‘適當顧及’義務”,《國際法研究》,2015年第5期,第50頁。《公約》中涉及不同權利、利益和秩序的協調的多個條款規定了“適當顧及”。(64)《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7條、第39條、第56條、第58條、第60條、第66條、第79條、第87條、第142條和第148條等。例如,《公約》第142條規定國際海底區域內活動涉及跨越國家管轄范圍的國際海底區域內資源時,應適當顧及沿海國的權利和利益。《公約》規定的沿海國和其他國家的“適當顧及”義務也是相互的,例如《公約》第56(2)條和第58(3)條的規定。可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立法中規定適當顧及沿海國權利有《公約》相關規定作為基礎。此外,應注意到適當顧及是原則性的要求,“適當”與否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和相關因素進行衡量。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設立和管理中如何做到適當顧及沿海國權利也需要具體從個案中考量。據此,在BBNJ國際協定原則性規定適當顧及沿海國合法權利的基礎上,之后BBNJ國際協定締約方大會通過的設立某一海洋保護區或采取特定養護措施的決議中應對如何適當顧及沿海國權利進行具體規定,以解決與沿海國權利沖突帶來的困境。
3.4 促進非締約方參與
如前所述,非締約方的忽視會導致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難以制定有效管理措施或起到實效。有學者指出,現有區域性法律框架下的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獲得間接地對非締約方的效力的可能途徑是獲得全球性的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的認可。(65)段文:“公海保護區能否拘束第三方?”《中國海商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40頁。全球公域的治理體制應有所有國家的參與。(66)Christopher C. Joyner, Elizabeth A. Martell, “Looking Back to See Ahead: UNCLOS III and Lessons for Global Commons Law”,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Vol.27, No.1, 1996, p.90.促進非締約方參與也是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協定制定的要點之一。BBNJ國際協定雖是《公約》下的多邊協定,但國際社會仍將存在BBNJ國際協定的非締約方。基于此,最新協定案文草案第十部分“本協定之非締約方”規定了鼓勵非締約方通過與協定條款一致的法規。(67)同①。這種鼓勵的具體落實需要通過促進相關國際條約或主管國際組織認可海洋保護區內采取的管理措施,使這些條約或組織的締約方或成員方都遵守這些措施,從而促進非締約方的參與。例如,如某一國家雖沒有加入BBNJ國際協定,但其是國際海事組織的成員方,就可通過促進國際海事組織在其職權范圍內認可BBNJ國際協定下海洋保護區的特定管理措施,使該國重視和遵守該措施。此外,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設立與管理以及相關國際合作中還應加強與非締約方的溝通和建立信任。加強溝通和建立信任可向非締約方傳遞信息,影響非締約方對包括締約方在內的其他國家行為的預期,鼓勵非締約方做出一定的承諾,甚至加入條約。(68)Anne van Aaken, “Behavioral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12, No.1, 2018, p.75.據此,通過BBNJ國際協定締約方會議或相關國際組織會議邀請非締約方參加以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非政府組織推動的民間交流或科學合作等方式加強溝通和建立信任也可促進非締約方的參與。
3.5 注重監測與評估
《公約》第192條原則性地規定,“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該條的要求不僅限于防止對海洋環境的可能損害,“保全”更意味著需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來保持或改善現有海洋環境的狀況。(69)Satya N. Nandan, Shabtai Rosenne, et al.,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Vol. IV,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1, p.40.通過包括海洋保護區在內的劃區管理工具促進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生物多樣性的養護和可持續利用,可被視作保全海洋環境的積極措施之一。但是盲目地設立起不到實效的海洋保護區不僅無益于保全海洋環境,而且會阻礙國際社會做出真正有效的努力。如前所述,現有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實踐面臨著監測與評估的困難,這也減損了國際社會設立保護區的意愿。注重監測與評估對于促進海洋保護區起到實際作用有重要意義。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協定制定應注重監測與評估,可規定一個常規的評估程序對海洋保護區及管理計劃中相關管理措施的有效性進行評估,確定管理措施是否在實現保護目標方面取得進展又或者需要對管理措施進行調整。評估過程中應考慮締約方、相關區域或部門性組織或者科學技術機構在監測中收集或提供的科學數據和信息以實現評估的真實有效。BBNJ國際協定還可規定,要求締約方提交的設立海洋保護區的提案中應包含針對擬議海洋保護區的監測與評估計劃,明確監測的要素、參數、時間、頻率、實施主體和方式以及資金來源等具體方面的內容。
四、結 語
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不被任何國家專屬管轄,是各國均可涉足的全球公域,(70)Kathy Leigh, “Liability for Damage to the Global Commons”, Australian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29, 1992, pp.130-131.其生物多樣性對全球環境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但當代國際法關于包括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在內的全球公域的原則和概念是呈現碎片化和不完善的。(71)Nico Schrijver, Vid Prislan, “From Mare Liberum to the Global Commons: Building on the Grotian Heritage”, Grotiana, Vol 30, No.1, 2009, p.206.當前,各國在對本國海域進行有效管控的基礎上,已開始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爭取海洋權益。(72)羅猛:“國家管轄范圍外海洋保護區的國際立法趨勢與中國因應”,《法學雜志》,2018年第11期,第91頁。擬定BBNJ國際協定既是在《公約》框架下完善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治理規則,尤其是其生物多樣性養護與可持續利用規則的過程,也是各國基于自身利益訴求和立場塑造新的國際規則的過程。在國際社會,規則和制度一旦建立,往往難以根除或做出重大調整,(73)何志鵬、李曉靜:“公海保護區談判中的中國對策研究”,《河北法學》,2017年第5期,第29頁。因此,我國應積極參與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治理規則的制定與完善,以助力建設海洋強國和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我國建設海洋強國的重要方面之一是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近年來,我國在大洋科考、深潛技術等方面有長足發展,為我國“走向深藍”和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是我國參與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立場與方案。(74)姚瑩:“‘海洋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意涵:理念創新與制度構建”,《當代法學》,2019年第5期,第138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注重海洋對人類社會的連結合作,而非分割孤立。在人類歷史上,海洋在便利人類交通與促進文明交流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過度的“海洋圈地”和無序的海洋保護區建設無疑會阻礙人類社會通過海洋實現便利交通與合作交流,影響現有海洋法原則與秩序,也不利于海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是BBNJ國際協定的核心議題之一。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設立和管理意味著對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中特定區域的開發利用活動的限制或禁止,將對各國在公海和國際海底區域的活動和利益造成顯著影響。我國應積極參與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國際立法,基于我國可持續利用海洋生物資源的現實所需以及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的迫切要求,提出具體建議,參與和引領相關規則的制定。具體而言,在構建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合法性基礎方面,我國應堅持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立法不能損害《公約》和習慣國際法等現行國際法確立的既有權利。這樣一方面可避免因與現有規則產生沖突導致海洋保護區難以設立或起到實效,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維護我國在既有國際法規則下享有的海洋權益。在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和促進非締約方重視方面,我國應積極參與國際海事組織、國際海底管理局、區域性漁業組織等在劃區管理工具方面的事務,影響其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并促進非締約方的重視。在適當顧及沿海國權利方面,我國應堅持適當顧及不意味著給予沿海國特殊權益,而是在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設立和管理的過程中合理考慮到沿海國的合法權益。鄰近沿海國在其管轄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開展活動時也應適當顧及BBNJ國際協定下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相關的養護、管理與監測活動。最后,我國應強調注重對國家管轄范圍以外區域海洋保護區的監測與評估,以評估實際的保護效果和決定是否需要對管理措施進行調整,包括是否在一定期限后撤銷或延續海洋保護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