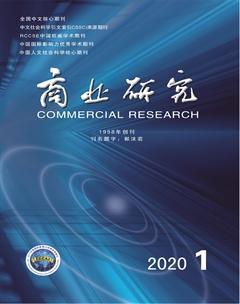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特征對定增標的資產估值的影響
李秉祥 黨怡昕 簡冠群



內容提要:標的資產“高溢價”導致上市公司業績下滑、資產承諾業績未達標事件激增,其中尤以定增并購標的資產與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關聯交易最為突出。本文以我國滬深A股2007-2018年對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實施過定向增發資產注入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分析終極控制權特征對標的資產估值的影響。結果表明: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呈“U”型關系,現金流權與定增標的資產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負相關,兩權分離度、控制權復雜度、定增前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正相關;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占據席位的比例越大,經理人由終極控制人任命或擔任的,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民營性質的相較于國有性質的終極控制人,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反映了機會主義行為動機下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地位顯著影響定增標的資產估值,虛增的注入資產價值加劇了定增并購中的業績承諾風險。終極控制人借助定增并購資產估值轉移上市公司財富行為更具隱蔽性,投資者和監管部門需關注定增并購資產估值環節,有效預防業績承諾風險。
關鍵詞:定向增發;終極控制權特征;資產估值
中圖分類號:F83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148X(2020)01-0103-10
一、引言
我國上市公司定向增發再融資方式助推并購浪潮自2014年進入快速上升期,加之2015年短暫的牛市行情助力,許多上市公司在定增并購中標的資產被高估十倍甚至百倍之多。隨著上市公司標的資產承諾業績未達標事件激增,2018年末至2019年初 A股市場頻頻“暴雷”,多只股票業績大變臉,大面積虧損的背后是大幅計提商譽減值,超高業績補償承諾誘發的風險被推到風口浪尖。定增標的資產高估值成為業績補償承諾難以實現的罪魁禍首,定增并購這片投資藍海也再一次引發廣泛質疑。
股改后資產注入這種特殊資本市場現象作為一把雙刃劍,其市場反應呈現出霄壤之別:促進產業鏈整合與企業價值提升的功能雖被大力宣揚,但是對于隱性利益輸送的質疑也甚囂塵上。那么以資產認購方式定向增發到底是提升公司價值的需求驅動,或是在終極控制人主導下的“隧道挖掘”甚至“掏空”的手段之一呢?目前,定增涉及的雙主體之間的關聯性普遍存在,這種契約安排下資產價值的公允性是界定其價值驅動還是利益輸送的關鍵,其評估增值率的合理閾值成為決定終極控制人是否涉嫌利益輸送以及利益輸送程度的核心標準。但是,實踐中評估市場信息不對稱,評估機構的求證式評估結果僅作為并購企業的參考意見,終極控制人有足夠能力和動機操縱資產評估;同時,業績承諾具有“保護傘”的效應,也促使上市公司愿意接受較高價格的讓渡,助長了終極控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基于主體參與視角,判定資產認購定向增發是否為難于示人的不道德交易就仍需從決策方終極控制權的特點上追根溯源,考察終極控制人的內在屬性及其影響。通過研究終極控制人在定增并購前的控制權特征,本文檢驗了終極控制人的“隧道挖掘”行為和對定增標的資產估值產生影響的機理,以揭示機會主義動機下終極控制權特征引爆業績補償承諾失效的行為路徑。
定向增發以其信息披露要求較低,政府審核簡易等諸多優勢備受市場青睞。2006年以來定增并購蓬勃發展,其中我國面向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的定增并購事件由最初的10家增長到2018年的427家。定向增發過程中涉及新老股東利益的再分配,使得終極控制人在參與定向增發時的角色更加復雜。定增并購雙方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資產流動和控制權轉換,終極控制人與上市公司之間的“雙重關聯交易”以其自身的隱秘性成為終極控制人攫取上市公司資產的有效途徑。特別在轉軌期制度環境下,股權集中度高、制衡度低的模式造成上市公司制內部治理環境失衡,一股獨大的情況下終極控制人在制定定增決策及并購交易時具有絕對話語權[1]。終極控制人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即使所持股份未來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受大股東定增股份三年鎖定期的影響,認購風險指數仍然很高。從主體參與視角出發,大股東定增注入資產肯定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則,勢必受到某種利益動機的驅使,或是出于分拆背景下盤活資產動機以促成整體上市[2],或是出于控制權私利動機以實現控制權的提高[3],或是出于政治目標及未來長期收益動機以保住“殼資源”[4-5],或是出于市值管理動機以期股價的良好表現[6-7]。
不同的利益動機使得學術界對大股東角色——“支持”或“掏空”的討論不絕于耳。有學者提出上市公司定增的重要動機是大股東的機會主義,市場的負面反應就是大股東直接轉移財富的證據[8]。特別是對雙重關聯交易下大股東的利益輸送行為預期更高,導致市場反應更加負面[9]。也有學者反對“大股東剝奪假說”,從短期投機收益視角看大股東利益輸送動機較強,向市場傳遞消極信號,但從長遠角度考察卻助益于上市公司資本配置效率提高和公司價值最大化,隨著控股股東的參與度提高,對公司的提升效果愈加明顯[1]。總體來看,大都傾向于支持大股東掏空這一觀點。基于此,已有大量文獻就定增資產注入中利益輸送行為展開研究:(1)定向增發高比例折價發行。定價的信息披露充分,更具“眼球效應”,由于信息不對稱、增量股權監督成本、大股東認購股份鎖定等,折價被認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認定增折價率與利益輸送關系密切,大多研究表明折價率越高利益輸送程度越高[10-12]。(2)通過注入劣質資產的方式侵害中小股東利益。對資產的質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對資產類型——是否與上市公司經營性資產高度關聯的討論[13-15]。(3)定增前的盈余管理及定增后的高額分紅等。上市公司會依據增發對象調整盈余管理的方向[16],在增發后往往表現為派發更多的現金紅利[17]。
但是,鮮少有人在對定向增發資產注入利益輸送行為的研究中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作為研究對象,僅有的相關文獻集中于對資產評估增值率虛高經濟后果的研究。(1)從股東財富縮水、資產評估公告的市場反應的角度出發:大股東私人收益與中小股東財富的嚴重背離降低了資本配置效率,催生股市泡沫[18];雖然有學者從資產提供方動機上肯定了大股東的“支持”行為,但是隨后的股價下跌致使企業財富和股東財富耗損,公告日后負宣告效應顯著[19];并且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市場反應來看,注入資產評估增值率始終與公告日市場反應呈負相關。(2)從企業未來績效表現的角度出發:面向大股東的定增并購本身就與上市公司的績效負相關,其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對上市公司績效也負向影響,印證了資產評估增值率與利益輸送間的隱蔽關系[20]。
準確定位標的資產高估值的影響要素是認定終極控制人利益輸送屬性的重要佐證,然而關于這方面的文獻鳳毛麟角。目前,有學者從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資產評級公司聲譽、標的資產的來源及地區市場化進程等角度展開研究,發現大股東絕對控股以及聘請“五大”資產評級公司評估的上市公司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較低,評估方法更具穩健性,從側面反映了資產評估機構并非中立,評估結果受到大股東不同程度的干預[21]。由于各地區市場化程度不同,資源配置中市場化機制發揮的作用受限,其注冊所在地市場化指數越高,定增標的資產的評估增值率越低,同時大股東參與定增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較高[22-23]。在諸多因素中,學者們就標的資產來源(即定增對象)的影響作用達成一致,充分論證了面向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定增并購中的畸高增值率,而這表象特征背后暗含的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特征作為內因才是破題關鍵。目前,從終極控制權特征視角來研究其對定增標的資產估值影響的文獻尚未見到,而終極控制人意志作為主要權變因素決定交易雙方對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值的博弈結果,聚焦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是如何影響注入資產評估增值率以實現利益輸送的,尤其是終級控制人所處的控制權環境(股東大會、經理層、董事會)對其注入資產的評估增值率的作用路徑成為驗證標的資產溢價生成機理的重要治理因素。基于此,終極控制權特征對標的資產估值的具體作用力仍是“黑箱”,尚有待研究。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終極控制人操縱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動機和能力受制于其所持有的控制權比例,其控制權比例會產生“管理防御效應”和“利益協同效應” [24-25]。當“管理防御效應”發揮主導作用時,隨著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的提高,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會隨之上升,掏空動機加劇[26];當“利益協同效應”發揮主導作用時,隨著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的提高,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會隨之下降,掏空動機顯著減弱[21]。進一步分析控制權背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應,透過兩權分離的表象,基于對控股成本與收益的權衡,終級控制人對中小股東利益侵害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其實取決于終極控制權的范圍,而這正是終極股東獲取控制權的關鍵動因所在。當其所擁有的控制權不足以形成控制力時,其有動機提升企業業績實現與其他股東的共享收益;在終極控制權較高形成絕對控制時,其作為企業的最大利益相關者實現了企業價值與自身利益價值高度統一,有動力并有能力做大做強公司;當終極控制人處于相對控制時,在控股成本和利益攫取的博弈之下呈現對中小股東利益侵占的“盤踞效應”,表現出強烈的私利動機[27]。鑒于我國上市公司中終極控制人達到絕對控制(控制權超過50%)的比例較低,處于相對控制狀態的仍占主導。可以推斷終極控制人的動機隨著其控制權力而動態變化,在此控制權區間內,隨著控制權比例的提高,終極控制人的表現由“利益協同效應”轉向“管理防御效應”。與控制權不同,現金流權代表所有者對企業的直接資本投入,現金流權越大,終極控制人獲取私有收益所付出的代價越高,相應承擔的風險也高,侵占成本的上升會減弱終極控制人的掏空動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1a: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具有“U”型影響。
H1b:終極控制人的現金流權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具有負向影響。
定向增發涉及大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格局重置,根據代理理論,一旦出現大股東與中小股東的利益分離,大股東就會想方設法獲取私人收益。在增發過程中,大股東認購定向增發新股后的持股比例與其原有持股比例的差值是反映大股東與中小股東利益分離程度的“晴雨表”[28]。通過定增并購,一方面大股東以新股東身份從較高資產評估增值率的認購中獲利,另一方面以老股東身份承擔部分共享損失,利益的天平會根據中小股東的利益分離程度而搖擺,分離程度越高,大股東越有動機抬高資產估值,將利益從沒有獲得增發機會的股東向自身轉移。因此,不同的控制權分離程度下,終極控制人在資產評估環節的利益追逐程度不同。終極控制人定向增發后獲得控制權的比例與其原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越大,越能反映出終極控制人自利行為的積極性,終極控制人就越有動機在定增并購中利用較高資產評估增值率進行自我利益輸送。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2:終極控制人定向增發后獲得控制權的比例與其原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越大,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越高。
金字塔式組織結構促進了公司資源的流動性和配置效率,但是其權益杠桿效應易引發與名義控制權不匹配的指數倍超額控制,特別是較長的控制鏈使得現金流權和控制權偏離引發的中小股東代理問題更突出,表現為強烈侵占效應[29-31]。因此,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的焦點是兩權分離,控股股東的控制權相對于現金流權偏離幅度越大,共享收益損失效率就越低,負面治理效應也越強,其轉移中小股東收益的意愿就越強烈。股東控制權假說在定增并購中依然成立,控股股東利用金字塔結構通過低價認購、向集團高價注入劣質資產等輸送利益,隨著定增公司股權的高度集中,兩權分離程度加大,控股股東謀取控制權收益的行為更加普遍,這些“隧道行為”嚴重損害了公司價值[32-33]。隨著金字塔層級和控制鏈條數量的增加,終極控制人的隱蔽性和安全性越高,更容易發生利益侵占行為[34]。因此,當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復雜度、兩權分離度較高時,盤根錯節的控制權結構更容易成為終極控制人利益輸送的“溫床”。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3:上市公司控制權復雜度越高,兩權分離程度越高,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
終極控制人不但可以通過建立錯綜復雜的控制權結構來掌握管理權和重大經營決策權,也可以通過影響企業內部不同層次的治理結構(董事會、經理層等)來主導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董事會結構是企業一系列契約組成的核心,往往被視為約束終極控制人的行為能力變量,是保證終極控制人對上市公司控制的重要手腕[35]。公司的終極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動人掌握的董事會席位越多或獨立董事席位越少,對中小股東財富的掠奪效應越強[36]。雖然經理層的自由裁量權很大程度受制于大股東和董事會的“威力”,但是其作為決策執行者仍然是深入企業運營方方面面的重要力量,甚至為降低代理成本,上市公司也會賦予其一定的控制權以示激勵。由此可以推斷,當終極控制人有動機提高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來侵害中小股東權益時,如果能實現對經理層和董事會的控制,那這種行為就會得到保證。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4: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和經理層控制度越高,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越高。
不同類型的終極控制人具有不同的經濟屬性,這決定了其在定增并購過程中不同的行為特征。由于民營性質的終極控制人為自然人,其從公司獲得的控制權私利可盡數歸于囊中,并有足夠的動力獲取最大程度的控制權私利,致使定增并購中標的資產的評估價格遠遠偏離其內在價值;不同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的最終控制人則是國家機關及政府等,不需要也不能存在掏空行為[37]。特別是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質量不高、約束機制相對不完善,金字塔股權結構及復雜的控制權鏈條又增強了終極控制人的隱蔽性,控制權真空及獲取控制權私利成本的外部性使得終極股東有更強烈的動機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缺乏政治背景的民營上市公司也很難搭乘融資及稅收便利的快車,其獲取私利的渠道受限,就越容易通過可操控的資產評估獲取私利,致使評估價格虛高,并對公司造成不良的影響。通過對比政府控制公司和家族控制公司的業績,也可知政府背景的公司治理狀況要遠遠優于民營背景的公司治理水平[38-39]。有學者考察不同類型終極控股股東的市場價值差異發現對中小股東利益侵害程度影響最大的是家族企業,其次是特殊法人,最后是政府[36]。因此,終極控制人的性質使得其在利益侵占方面存在差異,表現為民營性質的終極控制人具有更強的掏空動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H5:民營性質的相較于國有性質的終極控制人,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
三、研究設計與方法的設定
(一)數據選取
2006年證監會出臺相應增發制度,鑒于定增并購第一年還未全面展開,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以2007年為起始年份,選取我國滬深A股市場2007-2018年向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進行定增并購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基于對終極控制人的定增并購動機的探究,終極控制權特征及上市公司相關財務數據均取自上市公司定增并購事件前一會計年度。為了避免治理結構和治理環境特殊性的干擾、公告日前后重大事件對上市公司定增并購的影響、保證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有效性,本文作如下處理:剔除金融類、ST類、在樣本期內實施公開增發和配股、限售期內再次實施定向增發的、控制權小于20%以及定增并購前后發生控制權轉移的上市公司樣本,同時對變量進行Winsorize處理后共得到389個樣本。上市公司特征數據、財務數據來自于CSMAR數據庫,定向增發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部分從數據庫中難以獲得的定向增發標的資產評估相關數據(資產評估增值率、并購相關性、評估方法)、涉及終極控制人的相關數據(控制權、現金流權、在董事會、經理層的任職情況以及終極控制人的性質)由筆者查閱巨潮資訊網中定向增發收購資產公告、資產評估報告以及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后經手工計算、整理得到。本文數據處理和相關分析應用 EXCEL2010和SPSS 23.0。
(二)主要變量界定
1.資產評估增值率。資產評估報告中的評估價值是基于標的資產的內在價值,充分考慮影響資產價值的多重因素,通過合理的模型分析有效進行量化的結果,資產評估增值率是用來衡量定增并購資產賬面價值與實際價值之間的偏離程度[19]。標的資產評估作為定增并購的重要環節,其評估增值率越高往往反映出上市公司注入資產的虛增價值越高。本文借鑒畢菡(2010)、顏淑姬(2012)的做法,通過“資產評估價值和調整后資產賬面價值的差值/調整后資產賬面價值”來定義資產評估增值率。
3.控制變量的選取。控制變量的選取標準主要從影響定增標的資產估值及公司控制權環境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出發,盡可能使其滿足控制域,減少模型的誤差。其中,并購相關性(Relation)用以衡量并購資產與上市公司主營業務的相關性程度,其影響并購資產的質量高低,進而影響評估增值率的高低;并購資金占募資比重(Value)描述定增資金用于并購的比重,并購資金占比越大,表明定增的掏空動機越強,終極控制人操縱定增并購中標的資產估值的概率就越高;評估方法(Meth)會直接影響到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由于假設開發法和收益法都是對未來盈利的預測,其評估增值率會相對較高;注入資產規模(Inject)可以消除不同定增規模對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干擾;最后,公司規模(Size)、財務杠桿(Lev)、成長性(Growth)、股權制衡度(Balance)、行業(Ind)、年份(Year)也需要加以控制。研究變量的主要說明見表1。
四、實證分析過程
(一)控制權特征描述性統計
表2是關于終極控制權特征及資產評估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第一,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均值(321.98)遠高于其中位數(140.68),由此可知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值普遍偏高。其最大值為8242.15,雖然在合理范圍內評估價值高于賬面價值屬于正常增值,但是如此之高的溢價背后往往是與實際價值的背離,資產評估結果失真,可以預見未來業績承諾風險極高。第二,定向增發前一年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最大值為93.2,其平均值為43.39,43.39的控制權說明上市公司終極控制人在公司決策過程中占據相對較高的控制地位。現金流權與控制權在描述性統計特征上基本一致,但是從兩權分離度來看,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兩權分離度最大值為15.97,說明終極控制人以較少的資金成本獲得了企業的超額控制權,均值1.48說明上市公司大部分終極控制人仍是通過持有股份獲得相應的控制權。終極控制人的性質均值為0.44,表明所選樣本中終極控制人民營性質占到44%,終極控制人占據董事會席位的比例均值為0.38,經理人來源于終極控制人的比例均值為0.61,說明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和經理層的控制度普遍較高,對企業決策的控制力越強。第三,定向增發前后終極控制權變化的最大值為3.27,即終極控制人定增并購獲得的控制權是原控制權的3.27倍,均值為0.5,相當于定增獲取的控制權占原控制權的一半,可以判斷其分離程度較高,終極控制人具有較強機會主義動機,同時也表明并購資產中大部分是面向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的定向增發,研究終極控制權特征與定增標的資產估值高低的關系對剖析標的資產估值高溢價現象時更具有針對性。
(二)變量相關性分析
針對所建立的有關終極控制權特征與定增標的資產估值的多元回歸模型,為了有效驗證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并檢驗模型的相關性對實證結果的影響作用,本文對變量的相關系數檢驗如表3所示。終極控制人控制權比例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在1%的水平上負相關,控制權比例的二次項與其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說明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非單調的關系,而至于兩者之間的最終呈現出何種關聯還需進一步的實證檢驗。現金流權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在1%的水平上負相關,表明現金流權越高,在資產轉移過程中共享收益的損失越大,相應承擔的風險也高,侵占成本的上升會減弱終極控制人的掏空動機。控制權復雜度、兩權分離度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正相關,表明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程度越大,控制權越復雜,定增并購中的隧道挖掘行為越猖獗。定增前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變化率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表明終極控制人通過資產注入獲得的控制權與原控制權之間的差額越大,定增并購的資產溢價水平越高。終極控制人在經理層及董事會的控制度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分別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表明在資產評估過程中,終極控制人在經理層及董事會的控制度越高,對評估機構的評估結果的操縱能力越強。終極控制人的性質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分別在1%的水平上正相關,表明終極控制人是民營性質的上市公司在定增并購中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
(三)多元回歸結果與分析
為了探討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歸模型分析多維度終極控制權特征對定增標的資產估值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Ⅰ、Ⅱ檢驗了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現金流權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影響;模型Ⅲ檢驗了定增前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變化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影響;模型Ⅳ、Ⅴ檢驗了控制權復雜度、兩權分離度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影響;模型Ⅵ、Ⅶ檢驗了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和經理層的控制度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影響;模型Ⅷ檢驗了終極控制人的性質對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影響。
從表4中可以發現:(1)模型Ⅰ中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隨著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提高,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會有所下降;控制權的二次項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當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提高到一定程度時,隨著控制權的增加會引起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的上升,即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與上市公司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成“U”型關系;模型Ⅱ中終極控制人的現金流權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較高的資金投入成本有效抑制了終極控制人的自利行為,降低了定增并購中資產評估的價值泡沫,該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1。(2)模型Ⅲ中定增前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變化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定增前后的控制權分離程度越高,終極控制人自身承擔損失的風險越低,轉移中小股東的財富越多,其越有動機抬高資產估值。該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2。(3)模型Ⅳ、模型Ⅴ中兩權分離度、控制權復雜度分別在在1%、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程度,控制權結構的復雜程度助長了終極控制人的自我利益輸送行為,分離程度越大,控制權越復雜,定增并購中利用標的資產高估值的方式掏空就更具隱蔽性。該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3。(4)模型Ⅵ、模型Ⅶ中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經理層的控制度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隨著終極控制人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地位越穩固,對公司融資行為和評估結果的影響力越強,在其自利動機驅使下定增并購資產評估增值率越高。該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4。(5)模型Ⅷ中終極控制人的性質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國有性質的終極控制人受制于完善的監管體系,謀求控制權私利的愿望和能力顯著弱于民營性質的終極控制人,表現為定增并購資產評估增值率較低。該檢驗結果驗證了假設H5。
(四)穩健性檢驗
在定增標的資產評估過程中考慮到評估方法具有多面性且資產價值具有波動性,標的資產的評估價值與真實價值之間允許存在差異,合理的增值率是可以被投資者及市場所接受。為了避免回歸檢驗結果偶然性的干擾,本文通過替換被解釋變量的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借鑒宋順林和翟進步(2014)的研究,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的衡量標準由資產評估增值率(REV)替換為非正常增值率(ABREV),即選取“資產評估報告披露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與同行業同類標的資產的評估增資率中值間的差額”表示標的資產的高估程度 [21]。依次重復上述回歸分析的過程,得出的結論基本不變,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五、結論與啟示
伴隨超高業績承諾未達標現象在2018-2019年間井噴式爆發,標的資產高估值的“泡沫化”成為定增并購業績承諾未達標的根源。本文以我國滬深A股市場2007-2018年間面向終極控制人及其關聯方進行定增并購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定增并購注入資產中標的資產高估值的利益輸送問題。研究發現:(1)從大股東層面出發,終極控制人的控制權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間呈“U”型關系,現金流權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負相關,兩權分離度、控制權復雜度、定增前后終極控制人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與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正相關。(2)從董事會層面出發,終極控制人在董事會占據席位的比例越大,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越高。(3)從經理層面出發,經理人由終極控制人任命或擔任的,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4)從終極控制人性質出發,民營性質的相較于國有性質的終極控制人,定增標的資產評估增值率更高。
研究啟示如下:對投資者而言,雖然以往研究表明控股股東會利用定向增發折價、注入劣質資產、定增前的盈余管理及定增后的高額分紅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但是本文發現了終極控制人利用其控制權借助定增并購中資產估值轉移上市公司財富的行為,其隱蔽性不易察覺,提示投資者應對標的資產估值予以足夠關注;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如何確定定增并購資產評估增資率的合理性,如何認定定增并購中終極控制人的動機以及資產后續的減值測試、評估等等,從標的資產估值環節有效預防業績承諾風險應該成為監管部門繼續完善政策考慮的重中之重。本文的結論表明終極控制人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權地位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國上市公司定增并購的性質,揭露了我國資本市場高溢價、高業績承諾的定增并購活動背后隱藏的利益輸送的問題——終極控制人抬高定增標的資產高估值以虛增注入資產的價值,導致了資本市場中業績承諾未達標事件頻發。當然,并購標的資產高估值作為主要因素,而并非業績承諾未達標的唯一因素,終極控制人還可能配合定向增發折價發行、支付方式組合、禁售股解禁甚至定向增發前多次減持等方式進行財富轉移,作為后續研究的方向,也可以引入政府干預、市場化相對進程、機構投資者參與等外部變量做進一步深入探討,以豐富和充實本文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 李彬,潘愛玲,楊洋. 大股東參與、定增并購主體關聯與利益輸送[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36(8):107-115.
[2] 佟巖,華晨,宋吉文. 定向增發整體上市、機構投資者與短期市場反應[J].會計研究, 2015(10): 74-81.
[3] 王曉亮,田昆儒. 定向增發、股權結構與過度投資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16(6): 72-77.
[4] 章衛東,張洪輝,鄒斌. 政府干預、大股東資產注入:支持抑或掏空[J].會計研究, 2012(8):34-40.
[5] 章衛東,趙興欣,李斯蕾. 定向增發注入資產相關性與大股東認購比例及其公司績效[J].當代財經,2017(2): 114-121.
[6] 尹筑嘉,文鳳華,楊曉光. 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資產注入行為的股東利益研究[J].管理評論,2010(7): 17-26.
[7] 簡冠群,李秉祥. 市值管理動機下大股東參與定向增發與利益輸送[J].運籌與管理, 2018(11):163-175.
[8] 張鳴,郭思永. 大股東控制下的定向增發和財富轉移——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研究,2009(5):78-87.
[9] 王浩,劉碧波. 定向增發: 大股東支持還是利益輸送[J].中國工業經濟,2011(10): 119-129.
[10]Baek J S, Kang J K,Lee I. Business Groups and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by Korean Chaebol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6,61(5): 2415-2449.
[11]朱紅軍,何賢杰,陳信元. 定向增發“盛宴”背后的利益輸送: 現象、理論根源與制度成因——基于馳宏鋅鍺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8(6): 136-148.
[12]王志強,張瑋婷,林麗芳. 上市公司定向增發中的利益輸送行為研究[J].南開管理評論,2010,13(3):109-116.
[13]張憶東. 資產注入——價值再造之旅[J].股市動態分析,2007(6):12-14.
[14]章衛東. 定向增發新股、資產注入類型與上市公司績效的關系——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 [J].會計研究,2010(3):58-65.
[15]杜勇. 資產注入、大股東支持行為與公司績效[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2013(5):73-80.
[16]宋鑫,阮永平,鄭凱. 大股東參與、盈余管理與定向增發價格偏離[J].財貿研究,2017(10):86-97.
[17]趙玉芳,余志勇,汪宜霞. 定向增發、現金分紅與利益輸送——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1(11):153-166.
[18]張祥建,郭嵐. 資產注入、大股東尋租行為與資本配置效率[J].金融研究,2008(2): 98-112.
[19]畢菡.定向增發資產注入中的利益輸送問題探討——基于資產評估的視角[D].江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20]唐洋,孫文. 定向增發資產注入中的利益輸送的實證研究[J].特區經濟,2012(4):113-115.
[21]宋順林、翟進步. 大股東操縱資產評估價格了嗎?[J].經濟管理,2014(9):145-155.
[22]周勤業,夏立軍,李莫愁. 大股東侵害與上市公司資產評估偏差[J]. 統計研究, 2003(10):39-44.
[23]李姣姣,干勝道.定向增發資產注入、資產評估與利益輸送——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數據[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33(5):38-45.
[24]Morck,R.,A.,Shleifer and R.W.,Vishny.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cial analysi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8(20):293-315.
[25]Claessens S,Djankov S,Fan J,Lang L.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J].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6):2741-2771.
[26]原紅旗,王紀偉,楊靜. 上市公司股份制改制中的資產評估操縱的動機及經濟后果[J].香港: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8(3):64-111.
[27]馬忠,陳彥. 金字塔結構下最終控制人的盤踞效應與利益協同效應[J].中國軟科學, 2008(5):91- 101.
[28]徐壽福. 大股東認購與定向增發折價——來自中國市場的證據[J]. 經濟管理,2009,31(9):129-135.
[29]Bebchuk, Lucian A, John C, et al. The power of takeover defenses[R]. Working Paper, Harvard Law School and NBER,2003.
[30]朱冬琴,陳文浩. 控制權、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偏離度對并購的影響——來自中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財經研究,2010,31(2):121-131.
[31]Reese,W.,and Weisbach,M. 2002. Protect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 Interests,Cross-lis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Subsequent equity offering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2,65-104.
[32]王曉亮,田昆儒. 定向增發、股權結構與過度投資研究[J].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 2016,(06):72-77.
[33]La Porta,R.,F.Lopez-de-Silanes,A. Shleifer,and R. W. Vishny.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3-27.
[34]陳紅,楊鑫瑤,王國磊. 上市公司終極控制權與大股東利益侵占行為研究——基于中國 A 股市場的經驗數據[J].當代經濟研究,2013(8):31-37.
[35]孫健. 終極控制權與資本結構的選擇——來自滬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科學,2008(2):18-25.
[36]葉勇,劉波,黃雷. 終極控制權、現金流量權與企業價值——基于隱性終極控制論的中國上市公司治理實證研究[J].管理科學學報,2007(2):66-79.
[37]劉峰,賀建剛,魏明海. 控制權、業績與利益輸送——基于五糧液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4(8):102-110.
[38]李善民,王德友,朱滔.控制流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與上市公司績效[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6):83-91.
[39]顏淑姬. 資產注入——利益輸入或利益輸出[J].商業經濟與管理, 2012(3):75-84.
[40]La Porta,R.,F.Lopez-de-Silanes,F. and Shleifer,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Journal of Finance, 1999(54):471-518.
[41]Claessens S,Djankov S,Lang L. The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East Asian corporations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58):8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