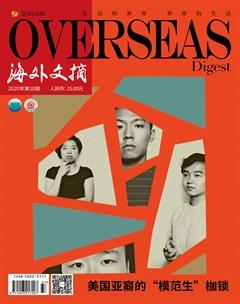絕望而死
□丁 穎

五年前,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凱斯和安格斯·迪頓向全世界介紹了“絕望而死”現象。越來越多的美國中年白人,特別是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人死于自殺、吸毒和酗酒。起初,人們還相信,在金融危機過后,隨著經濟復蘇,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會有所改變。然而,死亡率進一步攀升了,這是對美國社會的不滿和控訴。
死亡與醫療
實際上,美國死亡危機的出現要早于金融危機。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沒有文憑的美國白人死亡率就已呈現上升趨勢。但現在情況似乎變得更糟糕了。從2014年到2017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連續三年降低。要知道,上一次發生這種情況還是在20世紀初美國人深陷于戰亂和西班牙流感疫情之時。不斷增長的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阿片類藥物流行造成的,從最初的處方止痛藥,逐漸發展到后來的街頭毒品,如海洛因和芬太尼。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殺和酗酒導致的死亡人數也在不斷增長。凱斯和迪頓認為,阿片類藥物的流行和濫用無疑是在火上澆油。
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很復雜。失業率升高或不平等待遇增多等解釋,與上升的死亡率之間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凱斯和迪頓的觀點是,美國經濟從根本上的不公正,不僅導致了高度不平等現象之類的問題,同時也為死亡危機創造了先決條件。他們將矛頭對準醫療體系,指出混亂的市場管理,以及放任不作為的監管機構,讓美國民眾獲取了大量的處方止痛藥。
醫療行業也分得了大筆財富。在美國收入分配中排前1%的高收入人群里,醫生占到16%,而在前0.1%中,醫生占6%。美國在醫療行業的投入耗費遠高于其他國家,效果卻反而更差。雇主為員工提供的醫療福利占到了職工薪酬的很大一部分,而這其中有些錢原本能以工資的形式支付給員工以提高其收入。高額的福利負擔促使公司將工作外包出去,這導致更多的人難以得到有保障的穩定工作,看不到出路。美國的經濟運作并非全是如此,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能取得巨大成功,但低技能的美國人只能掙扎在行業底端,毫無未來可言。
根源在智庫?
美國資本主義極具掠奪性的原因尚不明確。問題的根源可能是在智庫里。參與這項討論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拉格拉邁·拉詹認為,美國落后地區的種種問題是由經濟誤讀造成的。他在《第三根支柱》一書中提到,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過于關注市場與各州層面上的問題,忽視了政策本身對城市和社區造成的影響。然而,城市和社區才是為人們提供實際社會支持的地方,幫助人們應對挫折,形成自我認同。但由于經濟學家未能重視貿易及技術變革給各地帶來的危害,被削弱的社區隨即便陷入了經濟和社會衰敗的循環,致使其成員更易藥物成癮和自殺。
文化的消亡
不過,死亡率增高的真正原因可能已經超出了正常的經濟學范疇。除了經濟衰敗以外,美國白人死亡率的不斷上升還伴隨著其他相關的趨勢,比如結婚率、教堂出勤率和社區組織入會率的降低。在羅伯特·帕特南2000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一書中,他曾指出,美國正經歷著長期而穩定的“社會資本”衰退期,而“社會資本”指的就是公民及社區的聯系強度。
在美式英語書籍中,“我們”一詞的使用率呈現出下降趨勢。
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帕特南對這一觀點的最新解讀是,若以更長的時間維度來分析,“絕望而死”現象是符合美國文化史的發展邏輯的。在經歷了20世紀初至60年代的上升期后,包括收入平等水平、跨黨派政治合作度、工會入會率、社區參與度及結婚率等在內的一系列指數,都在度過平穩期后轉為了下降趨勢。出版界的數據顯示,在美式英語書籍中,“我們”一詞的使用率也呈現出相同的走勢。帕特南認為,在20世紀上半葉,工業壟斷、經濟蕭條及戰爭爆發可能引發了美國人的文化共鳴,讓他們更能從集體的角度來思考和行動。然而,在隨后的半個世紀里,美國人似乎又回到了更個體化的狀態。
帕特南的觀點具有參考價值,但仍有爭議。如今,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等社會病態,已呈現出蔓延全球之勢,但美國的死亡危機并未出現在其他發達國家。難道它們都沒有經歷過美國這樣的集體精神衰退期嗎?
但倘若“絕望而死”現象并不能以文化的角度來完美解釋,那它仍然是社會科學家們急需努力弄清的一個問題。美國的死亡危機像一個信號,表明其制度存在嚴重缺陷。對于經濟學家們而言,只有打破領域束縛和固有思維,才能解決好這個問題。
[編譯自英國《經濟學人》]
編輯: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