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形”的繪畫觀
蔣正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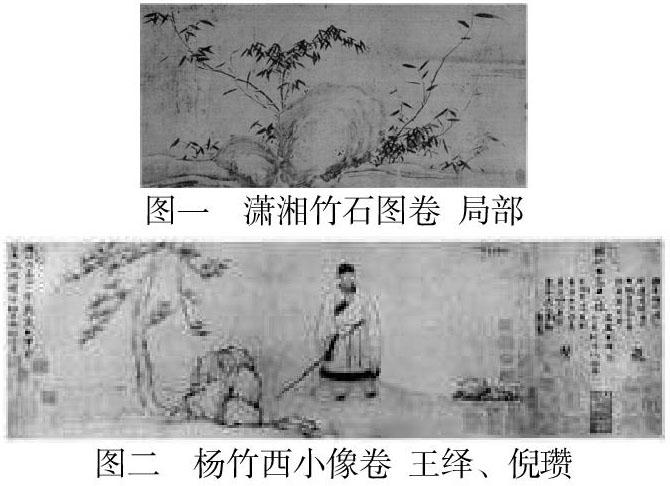
摘要:在日常生活中“得意忘形”是個貶義詞,通用詞意是因心意得到滿足而高興得失去常態。在繪畫活動中的"得意忘形"則是指得其意,即其思想精髓,而不必計較形,即表現形式內涵的一種繪畫的觀點。“得意”是繪畫藝術對意境的追求,是造型的靈魂,“忘形”是對形體的提煉與夸張,是忘與不忘的辯證統一。“得意忘形”,可以是一種人生狀態,也是一種藝術境界,在見到本性的時候,忘掉了形,盡情抒發自己的情感。同時“得意忘形”亦是一種取舍,取的是一種繪畫表現自由與審美自由的藝術境界,也是形與神、主體與客體高度統一的表征。而舍是我們常常糾結于尋常的眼光,為外在之形所累,不曾再去尋“得意忘形”本來的妙處。
關鍵詞:繪畫;藝術;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最早是用來形容魏晉時期著名詩人阮籍的,他與嵇康等七人經常聚在山陽竹林之下,閑談、狂飲、作詩、彈琴,高興時就縱聲狂笑,不高興時就痛哭一場,被世人稱為“竹林七賢”。在這七人當中,阮籍大概是最為瘋癲的了,尤其是在喝醉的時候,常常哭笑無常。因此史書中描寫他時說到“當其得意,忽忘形骸”。而得意忘形真正作為一種美學觀念,則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才正式確立的。在歐陽修的《盤車圖》詩云:“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而相關的論述沈括也說過:“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
一、從以形寫神到得意忘形
首先提出以形寫神的畫家是晉朝的名家顧愷之,后受到了南北朝時期的繪畫理論家謝赫的重視,在他的著作《古畫品錄》中著重論述了“形色”與“神氣”的關系。這個審美觀點經過不斷延伸,逐步從人物畫擴展到花鳥畫和山水畫。到了宋代,文人開始參與到繪畫創作中來,文人墨戲成為一種時尚。這個時候“傳神”被賦予了更多文學含義。它是古代畫家在創作中重要的審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歷代畫家都不斷嘗試用各種手法表現形與神的關系。神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神似,是內在精神氣質的刻畫。不過,宗旨沒有變,要“以形達意”。
再到后來,日益貶抑“形似”,將其打入末流。北宋蘇軾擅長畫墨竹,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圖一)等。蘇軾在畫竹時,一筆揮出一條線,從地起一直至頂,就是竹桿了。有人不明白:竹子明明都是一節一節的,怎么能畫成一條線呢?蘇軾回答:竹子也不是一節一節生長出來的呀。蘇軾畫竹,要表現竹子拔地而起的生長氣勢,而非竹子的外表是什么樣子。他追求的是竹子的“意”,而擺脫了竹子的“形”。蘇東坡有一句名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在蘇軾看來,藝術若求形似,就太小兒科了。表現形似,有賴于技巧,有造作和藻飾的嫌疑;“意”,是蘊于內在的氣韻,更接近本真。意,是無形的,卻是真正的奧妙所在;形象,則為其次了。高明的文人藝術,把“意”的表現放在首位。慢慢地,便將一切形象細節都忘卻,只留中心的一點性靈。于是,“得意”而“忘形”了。
二、從言不盡意到繪畫的意在形外
莊子說:“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荃、蹄是用來捕魚、兔的,得魚應忘荃,得兔應忘蹄。語言是用來達意的,得意應忘言。言是橋梁,是工具,是手段;意是歸宿,是結果,是目的。莊子提醒我們過了河,就要拆橋,不要混淆了工具和結果,手段和目的。手段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再完美的手段終究還是手段。“言”,是追尋“意”的工具。于是,得意之后,也就忘言了。在繪畫中的“形”和“言”一樣,都是模擬事物的手段。形只是表達意的橋梁。而意是繪畫藝術追求的靈魂所要,它不但蘊含了先賢的思想境界,還夾雜著中國發展史多元符號的進程。不僅體現了畫家的審美情趣和藝術修養,也決定了繪畫作品的藝術品味和思想格調。它是心與物的對話,是從主觀的形之外來證實情感和物象的統一問題。
當我們去刻意的表達物象的外形細節,并不利于意的傳達。因為,太執著于紛紜的物象,反而為其所蔽,把過多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形”上,而妨礙了我們對“意”的感受和表達。有時拋卻了“形”的準確和真實,反而更能得“意”了。物象只是物象,而意卻在物象之外。如同我們的生活,很多困頓和迷惘,來自于跟外在之形的糾葛。若要得心中之意,要先舍棄那些自擾的東西。
三、從隨心所欲到見萬物情
倪云林有云“吾作畫,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抒胸中之逸氣耳。”云林的逸氣何在?在寂寥,水無波興,林無花發,亭中無人影交雜,無涯無際的荒寒寂寞,淡卻色相,全無煙火氣,唯荒天迥地,從秋天回到秋天的蕭疏高曠,從冬天回到冬天的幽冷深寂。這是他的畫中之境,亦是他的心中之執。這種即興式的抒懷,是對“形”之束縛的擺脫,來自文人的瀟灑快意,也是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忘形”之后的“得意”,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緒,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玄妙。年幼時,我們總想明明白白的告訴別人,你看你看這就是我。長大后,我們總想清清楚楚的告訴別人,你看你看這是我做的。而只有真正的成長后,才知道一切皆虛妄。胃口得不到滿足就不知道饑餓,會覺得饞,覺得饑餓是因為品過了五味,品過了美好。對萬物起決定性作用的永遠不是具象看的見的東西,而是看不見的“道”。各個方面皆是如此。在美學里體現更是淋漓盡致,必須是“形式”決定“內容”。“意”雖無形而高于“形”。故有:雪的意,在清;月的意,在明;花的意,在馨;人的意,在情。“得意忘形”,是一種自由。“忘形”之后的“得意”,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情緒,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玄妙。徜徉其中,既享受情感宣泄后的快活,也構設了一場內蘊修煉之境。若是得意,那種感觸與激情,從來不會騙人。而停留于外形上的東西,卻永遠說服不了自己的內心。
參考文獻:
[1]?李玉琨. 論“得意忘形”的中國畫的繪畫觀 [J].時代文學,2018年01期
[2]?王永林. 中國畫意象表現中的“得意忘形”——從梅清黃山實景山水畫談起[J]. 《中國書畫》 2016年11期
(作者單位:云南工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