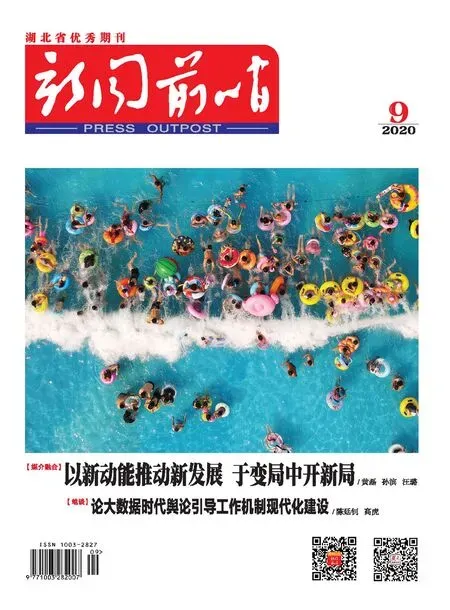網絡粉絲亞文化的“破圈”與“圈地自萌”
◎符邁予
一、 “破圈”與“圈地自萌”
近年來, 網絡用戶的圈層化與圈層傳播成為廣泛關注的對象。有學者將圈子定義為“以情感、利益、興趣等維系的具有特定關系模式的人群聚合”[1]。 但這種特定的關系模式并不是固定的,圈層是一個“多孔的、流動的、變形的彈性范圍和空間”[2], 粉絲圈層的邊界也具有開放性、 流動性和彈性。因此,在粉絲圈層網絡傳播過程中廣泛地存在“破圈”與“圈地自萌”現象。
(一)“破圈”過程中的沖突和污名化
“破圈”原本就是粉絲圈詞匯,近年來突破粉絲圈詞匯的屬性而被廣泛用于形容跨越圈層的傳播現象。 破圈對于粉絲圈層來說,既具有文化價值也具有商業價值,但粉絲亞文化的破圈過程中也面臨著沖突和污名化問題。
在粉絲亞文化的跨圈層傳播過程中, 粉絲行為常被學者、 大眾媒體或大眾污名化為一種病態的狂熱, 如詹森指出,粉絲往往被刻畫為兩種類型,一是“癡迷的個體”,另一種是 “歇斯底里的群氓”[3]。 以圍繞某一特定偶像的粉絲為例,粉絲通常有組織性地為偶像打榜、投票、應援或用消費的形式來支持偶像的作品和代言商品。 這些粉圈內部的活動本身并不至于導致沖突, 但因為粉絲行為的過度性和識別他者的困難, 在公共領域中行為常呈現出一種偏執的偶像保護主義。 他們對不利于偶像的聲音一律激烈對抗甚至上升到無視客觀事實的人身攻擊或濫用平臺舉報功能進行無差別攻擊。 這種過度和越界的行為損害了大眾在公共領域的體驗或直接損害大眾利益,引起不滿和沖突。 因此,粉絲亞文化的破圈需要解決控制好邊界開放或擴展的程度以減緩此類沖突,樹立正向的粉絲圈層形象。
(二)“圈地自萌”的自我封閉危機
與破圈的浪潮相對應的,粉絲圈層中廣泛地存在“圈地自萌”的現象,圈地自萌指對于一些非大眾的、個性化的觀點和愛好,不在公眾平臺爭論或宣揚,而利用標注符號將交流互動控制在相同興趣圈子內部的行為方式[4]。 例如,在bilibili 網站中許多up 主制作并發布主觀性內容時在標題或簡介中注明“圈地自萌,不喜勿噴”等字樣,這既是對圈層內部的一種保護機制也是對圈外大眾的尊重。
粉絲的圈地自萌能夠幫助粉絲圈層避免與外界的沖突,但同時也易演化成一種極端化的自我封閉。這種極端是對公共領域話語權的放棄, 對粉絲圈層與外部的交流和積極的碰撞的逃避。社會沖突論認為,社會沖突不僅僅是一種破壞社會穩定的單純因素,它對于社會整合、團結一致同樣具有重要的積極的促進作用[5]。在無政府狀態的網絡空間中雖然容易激發各種矛盾, 但通過沖突和碰撞同樣可以顯露出粉絲群體現存的弊端或不足之處。 由此可以為建構更完善的粉絲網絡社區提供改進方向, 也通過社會沖突漸漸演化出合適的溝通方式和傳播策略。因此,粉絲圈層的圈地自萌需要控制好邊界區隔或收縮的程度, 保留粉絲亞文化的生機與活力。
破圈與圈地自萌都是圈層邊界的流動, 但無論是突破圈層限制還是強化圈層的區隔性均需避免走向極端化。 無休止的沖突與固步自封都不利于粉絲亞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所謂邊界,是一種圈層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區隔性機制。因此, 粉絲亞文化合理把控好傳播的邊界首先需要探尋在網絡環境下富有開放性、流動性、彈性的粉絲圈層邊界是否存在可控的區隔性機制及該如何利用此機制。
二、模糊的邊界
從理論上,因粉絲定義的模糊,對粉絲亞文化傳播邊界的把控面臨著粉絲圈層邊界模糊而難以識別他者的問題。“粉絲”一詞源自英語單詞“fans",從廣義上來說,對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強烈的興趣或贊賞的人都可以被稱為粉絲[6]。目前學術界對粉絲一詞并沒有一個明確統一的定義。 德賽都(De Certeau)和詹金斯(Jenkins)將粉絲解讀為具有積極性和主動性的“文本盜獵者”和“游牧民”[7]。早期西方將粉絲解讀為病態的“歇斯底里的群眾”和“著迷的孤獨者”[8]。國內的粉絲亞文化研究大多建立在借鑒西方這兩種定義傾向的基礎上, 而這兩種傾向實際上都是對粉絲本質化和簡單化的解讀。
從粉絲主體的角度來說,首先,互聯網時代個體文化身份多元,可能同時屬于不同的圈層或趣緣群體,各種文化身份重疊交錯。粉絲群體內部也按投入程度、參與方式等多種方式細分,使粉絲群體內部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主體多元化造成了識別“他者”的困難,比如在肖戰AO3 事件中,進行同人創作的粉絲同樣歸屬于肖戰粉絲群體, 而同人創作者被“唯粉”排外處理,此時不僅是粉絲亞文化與同人文化之間發生摩擦也是粉絲內部的碰撞。其次,粉絲身份往往處在變動中且不斷自我調整。 費斯克(Fiske)明確指出“‘迷’和其他不太過分的大眾讀者的差別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質上的差別”。如今負載著多重文化身份的個體也普遍表現出一種“游牧式的主體性”,他們在社會機構的網絡間穿梭往來,并根據當下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社會效忠從屬關系[9],因此這種過度性和主體性都并非是固定不變的。
從網絡環境下粉絲研究的角度來說,首先,常用來對粉絲主體進行研究的方法往往具有局限性, 選擇的研究對象也是有限的。例如,網絡民族志的研究中用以論證或概括粉絲特點的粉絲實踐和粉絲生產的文本不僅具有粉絲話語特征也具有互聯網語境的特征, 且選擇作為觀察對象的網絡粉絲社區也受到其歸屬平臺場域的影響。 粉絲話語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不同的特點, 互聯網語境的復雜性使得粉絲定義的邊界難以劃分, 無法僅僅以對于某種語境的研究來簡單化地定義。其次,關于粉絲的研究易陷入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 陶東風認為: “本質主義是一種僵化、封閉、獨斷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生產模式,它假定事物具有超歷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質 ,這個本質不因時空條件的變化而變化”[10]。 忽略粉絲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流動性和內部差異性,以固化的視角來選擇粉絲群體中的較為突出的粉絲類型且從單一維度對粉絲進行解讀,無法全面、準確地定義粉絲。
三、傳播邊界的控制
如赫茲菲爾德(Michael Herzfeld)的評論所說,人類學意義上的疆界要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繪制在地圖上的疆界靈活得多[11]。 粉絲亞文化的邊界同樣是流動而難以識別的,從理論上無法準確定義粉絲或以僵化的標準為邊界的劃分依據。要緩解隨著粉絲亞文化話語地位逐漸上升,網絡粉絲亞文化傳播過程中越來越頻繁和影響廣泛的沖突, 應落實到粉絲亞文化傳播實踐中,發揮傳播雙方的主觀能動性,使其在法律范圍內自覺控制傳播的邊界。
從粉絲亞文化為主體的角度出發,需要在“圈地自萌”與“破圈”代表的邊界開放、擴展與區隔、收縮中找到一個平衡點。 圈地自萌的核心是對亞文化核心價值的堅守和對其他文化的尊重, 破圈的核心是不斷完善進取和交流的開放姿態。在亞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兩者并非不可兼得,且兩者核心的融合可作為粉絲亞文化在網絡環境傳播實踐中控制好傳播邊界的尺度。

第一,對于粉絲亞文化來說,對外傳播應建立在堅守自身文化價值的基礎上, 即使破圈也不意味著對粉絲主體性的放棄, 在商業化過程中如此也能一定程度上避免論為資本操控工具。 第二,在傳播過程中應保持開放的交流姿態,同時也增強內部的自我規范, 在不影響大眾網絡體驗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和傳播。第三,其中粉絲圈層內的意見領袖也應扮演好“把關人”的角色,認識到自身社會責任, 正確引導粉絲行為。 若粉絲是圍繞某一偶像建立的,那么偶像也應自覺引導粉絲,緩解沖突。
在傳播雙方的關系上, 粉絲亞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傳播必須建立在互相尊重、平等溝通的基礎上,應擺脫將主體間關系定義為對立或一方“扶弱”和教化另一方的偏見。以沖突最為明顯的粉絲亞文化與官方文化之間的關系為例,粉絲亞文化在構建過程中,“征用”和“重塑”了“官方文化中的某些價值和特征”[12]。 特定圈層創造的流行語在傳播過程中可能被其他圈層接納吸收, 成為最終形成的主流意義的一部分[13],粉絲圈層創造的文化也同樣以符號的形式滲透到官方文化中。 大眾媒介的傳播和學術界的研究應避免污名化和過于理想化的兩個極端, 客觀地看待粉絲亞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關系。
注釋:
[1]彭蘭:《網絡的圈子化:關系、文化、技術維度下的類聚與群分》,《編輯之友》2019 年第 11 期
[2]劉戰偉、李嬡嬡、劉蒙之:《圈層破壁、知識流動與破圈風險——以截屏與錄屏為例》,《青年記者》2020 年第18 期
[3]朱莉·詹森:《病態的粉都:類型化的后果》,紐約勞特利奇出版社1992 年版
[4]夏雨欣:《從粉絲“圈地自萌”看社會隔離》,《青年記者》2017 年第 14 期
[5]胡長青:《社會沖突論視角下網絡民意表達維護機制的構建》,《東南學術》2013 年第 5 期
[6]陶東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
[7]張晨陽:《新媒介環境下的中國迷文化:理論取向與現實觀照》,《江西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1 期
[8][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1 年版
9]馮濟海:《中華民族內群體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邊界問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 1 期
[10]陶東風:《文學理論基本問題》,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
[11]麥克爾·赫茲菲爾德:《什么是人類常識: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人類學理論實踐》,華夏出版社2005 年版
[12]王亞娜:《粉絲行為、心理特征及粉絲文化》,《青年記者》2014 年第 8 期
[13]劉明洋、王鴻坤:《從“圈層傳播”到“共同體意識”建構——基于2011—2018 年 “十大流行語” 的話語議程分析》,《出版發行研究》2019 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