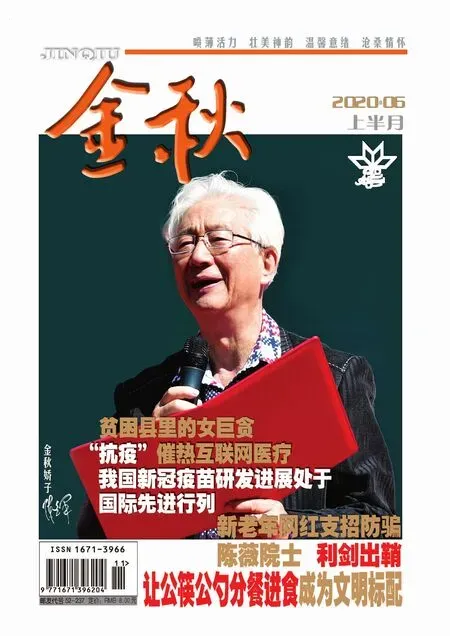我的三個夢
文/薛立強

我8歲開始放牛,12歲轉為放羊,父親是我的啟蒙老師,讓我死背硬記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名賢集》等開蒙書籍,所以我是白天放牧,晚上讀書。在上學前,我已經初通文字,會打算盤,能看古典小說。記得一個偶然機會,父親給了我一元錢,讓我和在家里干活的金拴叔一起到梁鎮去趕六月會。我用5角錢買門票看了馬戲,5角錢在書攤上買了一本《學生字典》。從此,那些個在小說里出現的“攔路虎”,被我使用字典一一掃除,似懂非懂的東西也因此迎刃而解。
1 9 5 6年,家鄉搞起了農業合作化,牲畜都集中起來,由大人們去經管,我們這些牧童都從放牧中解放了出來,有了上學的機會,圓了我的上學讀書夢。一開始,我在離家十多里的廟畔小學上學,由于有基礎,初小只念了兩年就跳班畢業考入了梁鎮完小。高小畢業在填報志愿時,我因牢記著偉大教育學家夸美紐斯的那句“教師是太陽底下,沒有再優越的職務”的話,所以就報了榆林師范——靖邊分校,做起了要當教師的夢。
然而當我在師范學校畢業滿懷希望地準備走向教師崗位時,卻趕上了國家困難時期,我們沒有得到分配,全部回鄉去務農。1963年,國家經濟有了好轉,我所在的村子用隊里的舊房子辦起了學校,我當選為民請教師。在這一人一校的學校里,我拼命地工作,實行復式教學、雙部制輪流教學,渴了喝一瓢涼水,餓了吃一把干炒米。我的努力使升學率連年百分之百,吸引了不少外公社的學生來此借讀。1972年,縣上組織教育大檢查,我的那個學校被評為先進學校,我被評為模范教師,出席了縣上的表彰大會。可是,當時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我校有個支書的女兒,爭強好勝打傷了同學,被我批評了幾句,她便向其父告了黑狀,這個土皇帝不問青紅皂白,借口我父親的一些歷史問題而罷免了我的民請教師職務。
1 9 7 8年改革開放后,恢復了高考制度,榆林地區招考教師,我以優異的成績在全區考了第一名,被錄取為公辦教師。由于我教學認真,多次獲得模范教師、模范班主任、先進教育工作者等光榮稱號,并由中小學教導主任做到了校長。調入教育局后,我任教育督導室科級督學,兩次受到縣人民政府的嘉獎,為教育的“兩基”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2005年,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不動煙酒、不沾麻將,唯一的愛好就是讀書、寫字,有時也寫點小塊文章。當我的處女作——《淺談陜北信天游》在《三邊文學》上發表后,鼓舞了我的寫作興趣。從此我的寫作逐漸多了起來,文史、散文、小說、詩歌,還有民間文學,十多年下來,居然寫了五六十萬字,其中好多都發表于本縣和部分省市級刊物上,有的還獲得了獎項。文章寫得多了,便萌生了著書立說的念頭。借著靖邊縣委和縣政府發出的“建設書香靖邊”的號召,經過我個人的不懈努力和諸多同志的大力幫助,終于完成了《黃土漢子黃土情》《三邊民間傳說》《閑云野鶴集》3本書,圓了我的著書立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