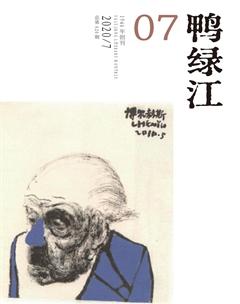現代化、后現代與“中國模式”
李佩侖 李雨蔚
摘要:“中國模式”或者所謂第三條道路很大程度無法擺脫單純經濟層面的考量維度。我國在在文化形態上的現代化還遠遠沒有完成,轉型期社會所呈現出的文化的豐富性并不等于后現代性。體制改革的最大瓶頸是對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認知的局限。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如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真正科學的發展觀,同時,如何擔當現代大國的社會責任,需要我們做出更成熟和理智的回答。
關鍵詞:現代化;后現代;中國模式
近段細讀了幾部有代表性的世界經濟文化學論著,分別是沃爾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貢當·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以及阿里吉的《亞當·斯密在北京》,結合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實際的思考,也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現就我們對東西方現代化、后現代以及“中國模式”的話題發表一下個人看法。
現代化的實現,除了包括擁有現代工業、商業文明以外,一個最根本的標志就是人性的覺醒和解放,或者說是現代精神文明的實現。西方經過文藝復興,實現了人的覺醒,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逐步走上了回歸和高揚人文個性、探索自由、公平、正義和寬容精神的現代文明之路。也正是這種創造力的解放使得西方近代社會獲得了技術上的和商業上的驅動力,建立起現代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并建成了與之相對應的現代文化。相比之下,我中華民族雖經百余年不懈流血革命和改革開放,卻至今尚未實現完善和完整意義上的現代化。尤其是在體制上、文化上,與張揚個體價值和追求自由精神的現代化目標仍有較大距離。而且,歷史驚人的相似性使我們不止一次地擔心改革會重蹈晚清洋務運動的覆轍。當年,那場為了挽救清王朝命運的改革也進行了三十年,但終因改革不徹底而歸于失敗。我們現在進行的這場改革運動,雖然在各項經濟指標上成績蜚然,也確實為上至國家下至百姓帶來了可觀的物質財富,但卻沒有建立起完善的現代經濟體制和現代政治制度,以至社會問題積重難返,改革路標搖擺不定。國家企業壟斷了相當規模的產業和資本,官商勾結造成最大的腐敗溫床,貧富差距日益懸殊,民主政治改革舉步不前,權力監督得不到保障,還有近一兩年來各領域的“國進民退”現象等等,都是明證。如果我國當前的決策者不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而僅僅滿足于經濟成就和樂道于“中國模式”,那么,體制上的最終局限必將成為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最大瓶頸和阻止中華民族復興的最大枷鎖。
事實上,“中國模式”或者所謂第三條道路,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在一個單純的經濟層面而被考量的。而客觀來講,我們的價值觀念和體制屬性從未被西方或者國際社會大面積認同。的確,我們的經濟發展道路對于西方來說是一條頗為新奇的軌跡——因為我們自身特殊的歷史和國情,而這種歷史和國情在很大程度上則由我們自身的多方面局限造成。和洋務運動一樣,我們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被迫行為。所以,國外的經濟學專家可以對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發展模式產生興趣,但絕不說明這種“模式”是整體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可資借鑒的準則。而在經濟之外,由于目下我國價值判斷體系的混亂模糊,普眾的信仰缺失和價值觀的日益世俗化,使我們還不具備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應該說,三十年來,我國取得了階段性的和經濟層面上的不小進步,但倘若不去繼續轉型和深化改革,而固守傳統執政理念,則會喪失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推動法治民主,從而解決各種深層次社會問題的大好機會。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如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完整而科學的發展觀,如何擔當現代大國的社會責任,需要我們做出更成熟和更理智的回答。而且,即便從社會經濟結構來看,我國的特色是否合理,是否能夠與國際接軌,都還是一個需要深入探究的問題。如我們的政府運作與市場經濟的要求到底有沒有距離?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是否制約社會公平?我們的權力體系與市場行為和利益是否依然勾連不清?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認識和解決,那我們的現代化之路就會變得艱難而漫長。
在文化形態上,我們認為其現代化的實現還遠遠沒有到來,更毋論后現代了。但前些年一些人持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特殊文化語境造就了一個特殊的后現代景觀,并常以最為發達的影視業作為自豪的佐證。而實際上,一個轉型期社會所理所當然呈現出的文化的豐富性(也包括由于價值判斷缺失所造成的“豐富性”)并不等于就是后現代性。我國當代的影視生產在本質上更具一種沒有任何文化意義指向界限和單純消費性的偽后現代性質。之所以說偽后現代,是因為中國電影的后現代語像仍然被挾持在一種純虛幻性的生產性的或者意識形態性的操作層面,是由直接的商業需求或者意識形態需求所界定的能指幻象。“國產大片”很多時候呈現的是空洞的唯美(甚至只是停留在視覺上)游戲,現代世界的物化和價值消解在中國影視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現(當然這一點并非影視作品生產者的主動性藝術表達)……一個缺失了意義與無意義的區分、中心與非中心的分辨、規則與無規則的界定、主體性確立與無主體性解構的標準的巨大狂歡圖景正在被我們所譜就和認可,并自命名為中國的后現代性。大家心照不宣地把一個仿真度極高的贗品當成了無價珍寶。于是,一個并不存在的后現代世界或者說并不完全真實存在的后現代世界,成了當代中國電影美學的“現實”性基礎。而許多導演和觀眾都有意無意地成為了一個虛幻式的后現代主義假象的共謀者。費瑟斯通說,“說起后現代性,就意味著一個時代的轉變,或者說,它意味著具有自己獨特組織原則的新的社會整體的出現。”可惜在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完整形態和特征的后現代(哪怕后工業)的社會仍未確立——我們不應忘記如阿多諾所說,一個較為全面的大眾社會形態的確立是以一種平民主義或民主的權力理論為前提條件的。因此,對于有人喜歡把《無極》、《十面埋伏》、《英雄》、《夜宴》甚至《功夫》等等代表作視為后現代式的自嘲性的展現,我們認為并不恰切。這并不是自嘲,相反,真正的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并不具備自嘲的清醒。
如果把東西方的文化觀念差異投放在斯皮爾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和馮小剛的《集結號》之間加以展開的話,對比度可能會更高些。我們都承認,八個救一個的故事是對尊重個體生命和個人價值的文化觀念的形象注釋。在一個以平民主義權力理論條件下確立起來的大眾社會里,個人的價值是絕對的,國家的價值是相對的,一個完整意義的現代社會(和國家)正是由一個個完整意義的現代人所組成的,而國家的存在也正是為每一個擁有獨立主體的現代人而服務,只有這樣的將個體生命和個人幸福視為至尊價值的國家,才值得人民為之不惜個我生命地去捍衛——而這一點才應該是英雄主義的真正源泉。這和為了一個架空的高高在所有個體之上的國家(或組織)概念而將整個民族拖入戰爭深淵的戰爭觀和英雄觀是有著本質差別的,這可以讓我們聯想到二戰時期的德國和日本。實際上,馮小剛的《集結號》雖然已時常將對戰爭的思考投放在個人視角之內,但整部作品始終貫穿了尋求上層意識形態的權力追認和權力尋獲的主線,這在大大消弱作品對個人價值的探索努力的同時,也恰恰反映了缺失了平民主義的社會形態的美學邏輯。國內評論界曾有人將此二部影片相提并論,只能讓人啼笑皆非。當一個社會的文化被一種虛幻的意識形態和更加虛幻的“后現代”雙重解構時,我們最終獲得的將既非“深度”的深度,亦必不是“無深度”的深度。因此,準確地說,我們在一個諷喻性的時代而恰恰缺失了反諷的力量,并以無深度的狂歡演繹和表征了利奧塔最深切的擔憂。
參考文獻:
[1]伊曼紐爾·沃爾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羅榮渠、尤來寅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
[2]貢當·弗蘭克,《白銀資本》,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9月。
[3]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6月。
[4]勞倫斯·E·卡洪,《現代性的困境:哲學、文化和反文化》,商務印書館,2008年1月。
[5]陳錦華,《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
[6]潘世偉,《中國模式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6年月。
[7]鄭永年,《中國模式》,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
[8]羅榮渠,《現代化新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4月。
作者簡介:
李佩侖,(1971年10月-)男,漢族,籍貫:河北邢臺,職稱: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研究領域:中外當代詩歌、跨文化研究與寫作,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文藝理論研究》《詩探索》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近著有《詩的復活:詩意現實的現代構成與新詩學》,曾獲第18屆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等獎項。
李雨蔚,(1996.11)女,籍貫:浙江杭州,學歷:英國諾丁漢大學國際教育專業碩士,職稱:英國西英格蘭大學英語文學專業學士。
課題基金: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國際中心平臺建設項目,項目編號4155C50217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