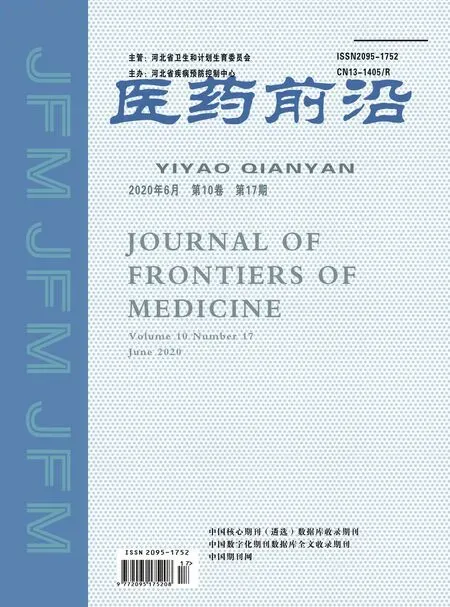單節段腰椎融合術后深部組織遲發感染治療體會
李海富 熊健 吳小川 劉翔
(中山市三鄉醫院 廣東 中山 528463)
腰椎融合術后遲發感染為非特異性感染,患者多臨床癥狀不典型,僅表現為術后數月患處疼痛不適,無術口腫脹、漏道形成,早期診斷困難。本院近2 年來收治5 例患者,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5 例患者,年齡49 ~72 歲,男性2 例,女性3 例,原發病均為腰椎管狹窄癥。所行術式單節段Mis-Tlif(管道下經椎間孔腰椎椎間融合術),其中L4/5 3 例,L5/S1 2 例,手術時間180 ~240min,開窗側留置術口引流管,引流量低于10ml 后拔除。感染發生于術后8 ~10 周。
1.2 臨床表現
患者首發癥狀為術后數周后覺腰背酸脹不適,無明顯強迫體位,術口均愈合良好,無紅腫、漏道形成,局部存在深壓痛,3 例患者搬腰骶部牽涉痛。所有患者均無高熱及下肢癥狀再發。早期血象檢查白細胞正常或升高,CRP、ESR 升高,PCT 正常或升高(圖1)。X 線檢查僅見術后改變。5 例患者深部壓痛最明顯處穿刺物培養均未見細菌生長。
1.3 診斷
CT 檢查融合節段同時存在骨吸收及骨痂形成,MRI 檢查椎旁軟組織T2 加權呈等信號或高信號,壓脂相呈高信號(圖2)。
1.4 治療
患者入院后早期靜脈使用抗生素,依據全身、局部情況,結合輔助檢查,后期改口服,其中1 例患者使用球蛋白2 周。同時根據“三證三法”,選擇相應方劑中藥湯劑治療,期間指導床上功能鍛煉。MRI 提示感染吸收,WBC、CRP 降至正常及局部癥狀消失3 周后停藥。
2.結果
患者均恢復勞動力,影像學提示鄰椎間骨橋形成。感染早期WBC 可正常或升高,CRP、ESR 不同程度升高,PCT 可正常。因椎間融合器支撐,X 線無特異性表現。CT 可發現終板微小局灶性骨吸收,MRI 見椎旁軟組織異常信號,感染控制后CT 下椎間出現骨橋連接,骨吸收停止并硬化,椎旁異常信號范圍縮小至消失。
3.討論
3.1 臨床特點
遲發深部感染的發生率約為2.44%[1],多與細菌感染有關,危險因素包括糖尿病、肥胖、高血壓、≥3 小時手術時間和輸血[2],而女性,年齡>60 歲,吸煙,自體骨移植,同種異體骨移植,預防性抗生素和類固醇治療等因素與發生無顯著關聯[3]。此類患者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多因術口可見的炎癥表現就診而發現,早期診斷困難,易漏診。本組病例就診時術口無紅腫、竇道形成、流膿等,患者自覺反復腰骶部酸痛,行走活動后可有加重,偶有低熱,由于堅強內固定支持,僅1例伴有下肢神經癥狀。出現影像學檢查異常后,隨即行實驗室檢查,最終考慮感染可能予以收治。因此,我們認為遲發感染與術后療效欠佳間不易鑒別,有必要早期CT 及實驗室檢查,警惕感染存在。
3.2 診斷要點
降鈣素原是一種炎癥標志物,手術生理損傷的程度并未改變其生物動力學,是術后即刻檢測手術部位感染最敏感、最特異的標志物,其敏感性和特異性分別為100%和95.2%[4]。雖然PCT 具有較高的陽性似然比12.4(95%CI,1.7 ~89.8),可以作為診斷納入標準,但總的陰性似然比達0.44(95%CI,0.25~0.78),即作為排除診斷標準有待考究[5],由于遲發性感染致病菌毒性相對較低,多伴有細菌外生物膜形成,可能不足以刺激機體產生大量PCT,本組病例在入院時、治療期間、出院時PCT 只波動于0.02 ~0.05ng/ml,表明此項指標對于診斷指導意義有限。ESR、CRP 雖然特異性較低,但敏感性高,對感染的早期診斷具有一定意義[6],如兩者降至正常后再次升高,在排除系統性感染及非感染性炎癥后應高度警惕遲發感染。但我科患者術后住院時間不超過2 周,ESR、CRP 尚未完全降至正常,動態監測兩項指標存在時間、其他因素及患者接受程度影響,以其指導診斷顯然存在缺陷,如能結合其他附加檢查可能價值更高。本組病例入院后ESR、CRP 數值雖然存在波動,但一直處于高于正常值范圍,期間CT 檢查可見椎體終板蟲噬空洞、MRI 軟組織高信號影有擴大之勢,感染得到控制后兩項指標降至正常,而影像學異常表現亦趨于固化或消散。綜上我們認為診斷遲發性感染應遵從三方面線索:(1)時間:一段正常恢復期后;(2)癥狀:反復腰骶部酸痛,開窗側術旁軟組織深壓痛。此處應注意患者焦慮情緒對主觀癥狀的影響,本組2 例女性患者在使用安慰劑后自訴癥狀完全緩解并維持2 天;(3)輔助檢查:單一檢查價值有限,但出現異常時需警惕,聯合實驗室和影像學能為早期診斷遲發性感染提供有力依據。
3.3 治療體會
內固定術后感染,手術清創為主,抗生素為輔。而最理想的選擇為內固定取出,徹底清創,避免病灶殘留,減少感染復發及多次清創的風險[7]。但需權衡以取出內固定物來控制感染與內固定物取出后可致矯形丟失和假關節形成、融合失敗之間的利弊。脊柱內固定術后感染病原菌中金黃色葡萄球菌占45.2%(其中MRSA 占15.5%),表皮葡萄球菌占31.4%[8],早期經驗經驗性使用萬古霉素聯合左氧氟沙星或頭孢哌酮舒巴坦可取得滿意療效[9]。本組病例未取得有效細菌培養支持,由于患者不能承受二次手術所致身心、經濟負擔,在考慮遲發性感染后早期靜脈使用萬古霉素+左氧氟沙星+頭孢哌酮舒巴坦,后期口服左氧氟沙星+利福平,根據影像學異常表現亦趨于固化或消散以及椎間隙骨橋形成,我們認為感染得到控制。關于免疫球蛋白及中藥對于療效的影響我們尚無明確證據,但其在增強免疫力及抑制內毒素誘發的炎性因子過度表達可能存在幫助。加強溝通,充分告知,保留內固定的綜合抗感染治療可以取得滿意效果,同時減少醫患矛盾。因為缺少大樣本治療經驗及長期隨訪,尚不排除感染復發及再次手術可能。這也提醒我們,圍手術期對感染危險因素控制及術后有效定期隨訪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