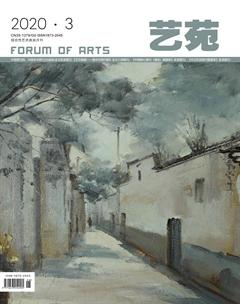法、儒、道家色彩觀比較研究


【摘要】 通過對法、儒、道三家原始經典名著的探索分析,描繪出三家的色彩審美觀,在比照與參量中,得他們的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從而分析出法家從周的色彩觀、儒家的倫理色彩觀以及道家的自我色彩觀,均對后來產生不同影響;同時對造物色彩的陳述也論證了三家色彩觀的關系,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據。
【關鍵詞】 法家;儒家;道家;色彩觀;造物色彩
[中圖分類號]J52? [文獻標識碼]A
“百家爭鳴”時期產生很多思想學說,在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獨特印記,法、儒、道三家的思想學說體系,受到原始思想文化影響,逐漸完善成為了獨立思想學說,而這三家的學說主張則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本原。[1]11-15其他學派的變遷發展,最終也歸流于這三大學派的思想文化中。色彩作為很直觀的因素,在法、儒、道家哲學思想中有一席之地,他們對色彩的獨特見解,對中國的色彩觀念產生了深遠影響,筆者借由三家色彩觀的比較研究,以窺探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
一、法、儒、道家色彩觀異同
(一)法、儒、道家色彩觀的相同
首先,用色彩觀表達思想本體論。論述色彩觀的相同點,自然避免不了思想學說影響,不論何種觀點、禮儀制度都是反映其思想本體論。春秋末年社會動蕩,一切處在一個混亂的情況下,孔子想要建立井然有序的制度,因此儒家學說的起點就是“禮”制,“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儒家是一種倫理思想,以“禮”來規范社會倫理等級制度。“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孔子以朱色為尊、黃色為貴、紫色為卑,而在齊桓公稱霸時,卻喜好紫色,不顧周禮的存在,這就是為什么孔子“惡”的原因。色彩也要合乎“禮”,無論是儀表、服飾、器物,無一例外,違背禮就是離經叛道的行為。道家以“愛己” “無為” “道”為最高原則,是反思想哲學[2]1-5,“愛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道家遠離時代,以個人天性、自然之性為標準,這就意味著必然不會與蘊含制約意味的五色產生關系,明確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老子·第十二章》),以此充分體現了以自我個性為中心的思想。法家作為統治者受歡迎的思想,其最大的特點便是不分軒輊,一斷于法,甚至強調以暴力推進法制,利用人欲推動社會發展,是強制的政權思想。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主張“不務德而務法”(《韓非子·顯學》),很明顯與儒家倫理思想是對立的,反對與倫理制約相關的統治方式,強調以法治國和權利的重要性。而法家在色彩上卻沒有做過多明確的規定,從“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管子·水地》)中能看出一二,拿色彩與準做對比,便是反映著權力制約這一思想本體。以本體思想作為基礎準則,制定的色彩體系無不體現著其思想特點,也可從思想反推其色彩觀。
其次,受周朝思想影響。“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明確表示了對周禮持肯定的態度,講究的色彩就是周之五色:青赤白黑黃。陰陽五行說是中國古代用來認識世界和解釋自然現象的哲學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老子之道也是從宇宙生成論開始的,形成了道家黑白陰陽觀。法家規范行為也是受了周禮的影響,在五色觀上還是有著一致性。但與儒家的禮不同之處在于,儒家是以倫理為基礎,法家是以統治者為中心。“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管子·形式解》),這里很明顯能看出,統治者即是權力中心,也是受制約者,作為君主必然時刻合乎禮儀,保持嚴肅才能向下貫徹政策法令,強調以君主為樣推行法治。
最后,三家思想服務不同的階級,但卻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治國為民理念。[1]11-15他們基于當時社會情況,對社會意識有獨特認識,提出了合宜的色彩觀,豐富自家學說。
(二)法、儒、道家色彩觀的不同
1.以法治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法家色彩觀
法家一直是持著積極從政的態度,法家代表人物都是從政,涉及軍事的。強調用暴力強制推進社會規范,法“為治之本也”“一任于法”(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采取“循名責實”的政治手腕,將“法” “術” “勢”緊密融合為一體,這是其不同于別家、受到統治者青睞的地方。
其一,從五行五色。“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韓非子·揆度第七十八》)韓非子這里所講的與周禮五色是一致的。五色與規章制度是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不可得也。”(《管子·權修》“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貂。”(《管子·立政》)法家在服裝制度上規定標準,在服飾顏色上沒有明確說使用什么顏色,但法家思想受到周禮影響,即可延續五色的觀點,天子的衣服一定要有文彩去彰顯身份,而平民的身份不得著有文彩的衣服,體現的均以統治者為核心的法治思想。“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管子·立政》)雖在原著中鮮有記載色彩的制定,但從“衣服有制”能看出顏色還是要有等級之分,與家族身份無關。“色者所以守民目也”,將其合為“二五”,而“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韓非子·揆度第七十八》),五色用來控制人們的觀賞,是作為統治的手段,若是缺失便會走上亡國道路,即便是顏色,也是用來統治的手段。
其二,從實用色。法家認為:“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管子·五輔》)這與法家講究實用、因地制宜的思想有關,不生產無用之物,人民才可富裕,得到治理。“是故博帶梨,大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管子·五輔》)君主若過分華麗,就會苛求人們,難以使人民親近。“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管子·立政》)女紅廣求采花文飾,國家就會貧窮。這里并不是徹底磨滅人的欲望,斷絕任何享用之物,而是提倡欲之有度,從實際社會情況為出發點,減少裝飾性,強調功能大于美學,遵循實用主義。
2.以禮治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儒家色彩觀
孔子曰:“非禮勿視。”可視不可視的原則是“禮”,倫理便是體現了美之所在。[3]13-15用禮規范人身關系,體現其神圣性和儀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以致敬于鬼神。”(《禮記·禮運》)在道德和自律的基礎上,依靠人的自覺性,同時用禮來規范人際關系,“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禮是具有強制性和權威性的。“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昭公五年》)儒家提出的禮核心都是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規范。儒家是積極的入世者,著眼于現實社會,解決實際性問題,在很多思想上是對周禮的肯定。
其一,以色正禮。“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荀子·大略》)禮制規定,大夫戴禮帽,而士只可戴皮制暗紅色帽子。“練而床,禮邪?”“非禮也。”(《荀子·子道》)“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荀子·富國》)“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論語·鄉黨篇》)“禮”與服飾顏色上,孔子講究的是正色所彰顯的身份地位,看重象征色,是合于“禮”的象征色,代表著等級秩序。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論語·陽貨篇》)“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孟子·萬章章句》)紫為間色,是對禮制的破壞和蔑視,是儒家所不能忍的。
其二,以色喻德。孔子的“喻德”多以物為載體,通過對物體色彩描述的解讀,以審美的角度體會道德品格。“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詩經·淄衣》)《召南·羔羊》有“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之語。就是說,品行內在與外貌裝扮是相稱的,只有純潔的德行才配的上這白色羊羔毛做成的衣物。《召南·野有死麕》有“白茅純束,有女如玉”之言,有女如玉。德如玉也,可贊譽女子之忠貞品行,也可解義為喻男子的美貌美德,如玉一般高尚潔凈,沒有受到過污染。
其三,色彩和諧。“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詩經·出其東門》)“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羔裘玄冠不以吊。”(《論語·鄉黨篇》)“公車千乘,朱英綠縢。”(《詩經·閟宮》)這些都是說在注重儀表服飾、正色正衣冠的同時要講究和諧之美,不單單是強調某一種顏色,而是在五色相生中尋求統一。“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論語·八佾》)這是在表達建立在“禮”的基礎上的色彩,才是美好的。[4]186-194
3.以出世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道家色彩觀
道家是避開現實社會的,以出世為態度,不從政,一切以個人為目的,潔身自好,明哲保身。“愛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同時道家也是否定“私”“自”,主張“利他”,“為我”謀求最佳處境。“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存其私。”(《老子·第七章》)。道家從解脫出世俗,同時反思討論社會與人,這是一種升華了的哲學思想。
其一,淡色觀。道家重視精神文明的發展,反對物質至上主義,貪圖享樂和財富對人只有消極作用,體現在色彩上就是提出了五色令人眼睛不舒服,旨在反對五色,減淡對顏色的重視。“五色令人目盲”(《老子·第十二章》)就是在反對周禮和儒家的五色觀。“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老子·第十九章》)。道家強調還原樸素之美,返璞歸真,也是反映道對個人生活和心靈的指導作用。推崇自然色和道家的意識形態很吻合。“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是說希望人也可以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本能和天性,就像生絹和原木一般,展現最原始的材質和顏色。
其二,黑白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說明“道”是不可分割的狀態,是成整體的。“道”無聲無形,是自然界中萬事萬物的運行軌跡,道就是世間萬物發展變化的載體。“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莊子·天選》)知白守黑的色彩觀,知白,即知道表象,守黑,即守住內在,要尊重自然內在規律,順勢而為,也可理解為是素淡的“道”之本色,指的是黑白不是視覺上所感知的顏色,也就不屬于五色之中,道之黑白內在蘊含著無限的自然色彩。道家很重視黑白這兩種自然顏色,站在哲學的高度去認識道之黑白,同時由于道家弱化物質的存在,所以這兩種自然顏色處于一個虛空的狀態,是萬物又不是萬物,道之黑色其實是天的顏色,而“天”在道家的思想中是獨一無二的。[5]69-78
二、法、儒、道家色彩觀互釋
首先,從意識形態上來看,道家反對周禮,法儒兩家肯定周禮。在色彩上,法儒兩家是肯定五色觀的,在這基礎上兩家又發展出了各自學派的色彩觀。道家反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主張取消知識,取消仁義道德。“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此;絕巧棄利,盜賤無有。”(《老子·第十九章》)道家在傳統文化上和儒家思想相悖。法家在某些觀點上與道家達成一致,均對仁義禮讓秉持批判的態度。儒家所倡導的正間色、“禮”色,對于道家是自我核心以外的事物,顏色甚至對道來說都是無用的,認為這種方位色有限,時空卻無限,即反對倫理色、五行方位色,而黑白色是“道”最好的表現。“是故駢與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莊子·駢拇》)
法道兩家都反對儒家的等級色。《老子·盜跖》指斥儒家觀點具有虛偽性和欺騙性,蒙蔽人性,各處強調禮制,是在限制人性,主張一切以原始狀態為最佳。《老子·漁父》指斥儒家的思想,并借此闡述了歸于自然的主張。法家認為,“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也強調自然的顏色。在這一點上法道兩家達成一致,講求本質色,和自然有關系。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也提到“繪事后素”,這個“素”也可理解為本色的和諧,在這個觀點上,可認為他們是一致的。孔子認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文質都不可偏廢。韓非子認為:“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后行者,其質不美也。”(《韓非子·解老第二十》)在審美觀點上,他們都認為不要過于華麗,文與質應該相對應。
三、以法、儒、道家色彩觀為取向的造物色彩陳述
在造物上,中國傳統工藝思想重視器物的倫理教育作用,必定包含著特定的寓意,會借助色彩、形制、尺寸、紋飾等規范行為,表達制度觀念。以造物的色彩去陳述法家、儒家、道家的色彩觀是論證方式,也使造物藝術的特點及其藝術風格形成,在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得到更深刻的解釋。由于缺乏考古彩色圖片資料,故部分內容以其形態方面闡述思想影響。
(一)服飾色彩
據考古戰國墓中出土的樂舞陶俑研究,長袖舞俑以紅色為主,臉部與長袍均為紅色,其中一個長袍有白點作為裝飾,另一個青灰色與黃色彩條相間,均露出黃色長裙。短袖舞俑也是以紅色為主,長袍青灰色紅點(圖1)。[6]44-59這些舞俑顏色豐富,裝飾性顏色也很多,筆者認為可以看出當時在儒家思想影響下,色彩運用方面以雜五色為主,而且搭配和諧、主次分明,達到了華麗裝飾性作用;但是,無論多么豐富的色彩,達到和諧統一才算主流審美,這里便是以紅色為主色調,輔以其他白色、黃色等,同時還有裝飾性,以達到華麗的效果,這種舞俑服飾色彩的表現,是維護社會秩序的一個標志,儒學的倫理等級的體現。
周朝在祭祀這類重大禮節時,著一種用野獸皮毛制成的服裝,名為大裘,在此衣外邊必須有一件與皮毛顏色相配的罩衣,[7]89-94在重大場合時服飾搭配顯得尤為重要。漢代規定冕服除圖案不同以外,在顏色上也有所區分,帝王的冕服(圖2),玄衣黑色,圍裳紅色,從服飾顏色、紋飾處理的和諧統一,表達了獨特的服飾色彩審美因素和審美愉快的原則,這種審美趣味也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
在漢武帝時期擯棄了道家學說,獨尊儒術,改正朔,易服色尚黃,也是嘗試通過規定服飾顏色來彰顯權威性。據記載山東博物館中館藏東平后屯漢墓壁畫,一號墓為東漢早期,繪在門楣、墓壁上的以人物畫像為主,描繪的大多都是宴飲、舞蹈等娛樂性的內容,漢成帝時規定青綠是作為民間常服的顏色,“紅衣為上服, 青綠次之, 吏卒衣黑, 平民衣白, 罪犯衣赭”[8]96-98,顏色作為文化的象征符號,以此區分身份等級是最為直接,最容易被感受到的方式。
(二)繪畫色彩
迄今為止的楚地帛畫,以《人物龍鳳圖》《人物御龍圖》最具代表性。兩者皆以白色絲帛為載體,設色以平涂為主。《人物龍鳳圖》中女子身著平常燕居的便服,臉部施墨,唇袖施朱,緣衣為黑色,道家追求的質樸體現的很明顯;《人物御龍圖》仍以墨線造型,而這種以金、白粉彩的繪畫顏色搭配方式初步奠定了工筆重彩畫基礎。[9]116-119在顏色上主要以墨色為主,這里值得說明的是兩幅帛畫所表達的人物神情與氛圍,均是閑逸狀態。當時楚地文化底蘊深厚,同時宗教崇拜豐富,莊子的個人意識充分體現在楚地美術作品之中,以表達個人的浪漫情懷,有著自然宇宙的宏大意識。由于這種思想的影響,在這段時期內我們看到的楚器物造型,大多是清奇、獨特的美學特征。[10]66-67
北宋時期推崇以文治國,確立“儒家思想”為實現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與當時的以華麗為特點的青綠山水藝術風格相比,道家以其追求自然質樸的行為,受到關注,同時黑白觀影響下的水墨畫便受到了文人偏愛。色彩不只是形式美,當它與心靈、權利相聯系,就有了特別的人文內涵。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無法入仕建功立業,最終只得退隱以求靜心的文人畫家,大多以水墨黑白之靜抒發心中之壓抑感,表達對自由的向往。如畫出《驢背吟詩圖》的徐渭、《木葉丹黃圖》的龔賢、《深山秋水圖》的石濤等等都是黑白文人水墨畫的代表。
(三)器物色彩
漢代青銅燈對功能的重視必然是受到漢代思想文化的影響,漢代“獨尊儒術”,使得更多的手藝人愿意去嘗試制作新形式的青銅器,隨著手工藝人經過長時間的摸索和實踐,對各種燈具的常用尺寸、造型美感、顏色搭配等等都有著不同的見解,而這些便是他們對器物的美感認知,從而構成了漢代青銅獨有的豐富造物美學[11]24-29,出現了長信宮燈、雁魚燈、錯銀銅牛燈等一系列供皇室、貴族階層,及有身份地位的人所用的照明器具。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道德經》)老子主張回歸自然之道,必然要對拘謹的陳規、壓抑本性的禮制進行堅決的否定,這種思想便影響著日常器物的制作中,創造出了很多看似怪誕的形象,道家不為道德倫理所束縛,超脫于現實規章制度下,在此影響下的器物都是以自然事物狀態為原型,加入手藝人自身的想法和審美,但即使在百家思想繁榮的大背景下,中原也沒有出現如此“出格”的藝術作品。[12]87-91
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作為祭祀等宗教功能減弱,而實用性要求便得以強調,它們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法家實用性主張的影響,在色彩上沒有過多華麗裝飾,在設計上少紋飾、重實用。比如現藏于湖北省博物館的駱駝人形燈,該燈具為戰國中晚期創制,以騎著駱駝的人為座,這樣合理的造型,沒有過多的裝飾性設計或者抽象處理,手藝人的個人特點并不明顯,僅僅作為一種燈具而使用,沒有其它明顯的附加意義。
四、總結
法、儒、道家思想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影響各不相同,但又有著共通之處,深入了解各學派的思想主張,就能對傳統色彩的認知更清晰,其積極影響與消極影響都同時存在。儒家思想讓傳統色彩一直禁錮于五形五色之中,以至于長期以來都會對某些顏色一直帶著偏見;道家補充了儒家所沒重視到的自我價值,豐富了水墨畫;法家支持擯棄過多的色彩,受到此影響便只重視器物實用價值,不強調藝術性和顏色的豐富性。但正是因為這些不同的思想學說的影響,才能形成獨特的東方色彩體系。
參考文獻:
[1]呂相康.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本原——儒道法整合論(上)[J].黃石教育學院學報,2004(01).
[2]呂相康.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的本原——儒道法整合論(中)[J].黃石教育學院學報,2004(02).
[3]孔麗波.教化與自然——儒家和道家色彩觀之比較論析[J].語文學刊,2013(10).
[4]王文娟.論儒家色彩觀[J].美術觀察,2004(10).
[5]王文娟.論道家色彩觀[J].美術觀察,2006(06).
[6]李曰訓.山東章丘女郎山戰國墓出土樂舞陶俑及有關問題[J].文物,1993(03).
[7]曾慧潔.先秦服飾考[J].中國藝術時空,2014(05).
[8]毛新華,董祖權.秦漢時期的服飾文化[J].安順學院學報,2009(03).
[9]陳锽.《人物龍鳳圖》與《人物御龍圖》簡論[J].美術,2015(05).
[10]韓雄.從《人物龍鳳圖》看楚文化藝術[J].藝海,2012(05).
[11]于亮.器以載道天人合一——漢代青銅燈的造物美學與環保意識[J].創意與設計,2012(05).
[12]吳文清,邵威華.兩周時期中原與楚器物工藝思想比較[J].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14(06).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設計人類學理論與實踐范式研究”(項目編號:18YJC760015)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李星星,北京交通大學2019級藝術設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視覺傳達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