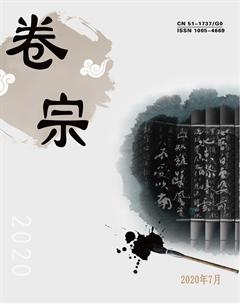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視角下的《中國哲學簡史》譯本對比研究
張芒 趙亞捷
摘 要:《中國哲學簡史》是當代大哲學家馮友蘭的作品,它用英文講述了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歷史,旨在為國外讀者普及中國哲學思想。本書的譯本在國內(nèi)也具有非凡的地位和影響力,成為中國青年了解中國哲學的入門書。這本書目前只有凃又光和趙復三兩個翻譯版本,本文通過譯者主體性的視角,從雙語文化能力、文本選擇、譯文接受者、譯者的詮釋空間和不同的翻譯策略幾個方面對比兩位譯者的不同翻譯特點,以期對以后的哲學翻譯帶來一定啟示。
關鍵詞:中國哲學簡史;譯者主體性;哲學翻譯
1 背景和文獻綜述
1.1 背景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作者自序中說:小史者,歷稽載籍,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學,而其識其才,較之學術巨著尤為需要。這本書的易讀性和權威性也體現(xiàn)在這三個方面。
首先,從學方面來看,馮友蘭精通中西方哲學,將全部哲學史了然于胸,他著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成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jīng)典,對中國現(xiàn)當代學界乃至國外學界影響深遠,稱譽為“現(xiàn)代新儒家”。其次,從識方面來看,馮友蘭結(jié)合西方讀者的實際情況,在繁復龐雜的中國哲學史中,選擇出了適合他們閱讀的經(jīng)典內(nèi)容。編者布德博士說當時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真實知識少得可憐,即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認知也只是停留在孔子與老子的印象中。而這本書堪稱是第一本對中國哲學進行全面介紹的英文書籍。最后,從才方面來看,《中國哲學簡史》經(jīng)過編輯布德的潤色與修改,使得本書更易于西方人理解,增強了其可讀性和趣味性。
本書包涵了很多哲學術語,所以需要譯者采用深入淺出的語言,使內(nèi)容通俗易懂。通過譯者主體性角度,能夠從社會和個人兩個維度分析出影響兩位譯者選擇不同翻譯策略的原因,對以后的譯者有所啟發(fā)。而如何避免因為譯者本身的原因影響翻譯的流暢度和準確度,是譯者和出版方都應考慮的問題。
1.2 文獻綜述
對于《中國哲學簡史》的翻譯研究較少,作者通過知網(wǎng)以關鍵詞“中國哲學簡史翻譯”查詢到2012年至2018年共8篇論文。傅張萌(2013)在《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看<中國哲學簡史>的漢譯》從譯者主體性角度分析了《中國哲學簡史》漢譯者的主體性因素。張瑞華(2015)在《簡評<中國哲學簡史>中的哲學翻譯觀》中,從西方解釋學的翻譯觀探討馮友蘭的哲學翻譯觀點,并分析其翻譯策略和翻譯觀點形成的原因。葉邵丹(2014)在《<中國哲學簡史>(節(jié)選)英譯中翻譯報告》中,從目的論的視角探討了此類文本翻譯過程中的問題和翻譯方法。聶家偉(2018)在《<中國哲學簡史>兩個中譯本簡要對比》中探討了本書兩個譯本翻譯策略的不同。常國華(2018)在《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兩種中譯本翻譯策略與實踐研究》中,從認知語言學的視角對比了兩個譯本的翻譯策略與特點。
從文獻綜述可以看出,目前對于這本書的翻譯研究,現(xiàn)有學者大多選擇從認知語言學、目的論等視角去分析其翻譯策略和方法。從譯者主體性視角對其研究的僅有一篇。本研究將從譯者主體性的雙語文化能力、文本選擇、譯文接受者、譯者的詮釋空間和不同的翻譯策略這幾個角度出發(fā),對比兩本譯著的不同。
2 譯者主體性
長久以來,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和傳統(tǒng)的翻譯觀念,學界一直認為翻譯沒有創(chuàng)造性,只是對原文的機械轉(zhuǎn)換,譯者的地位沒有得到重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受到西方語言學轉(zhuǎn)向和文化轉(zhuǎn)向的影響,翻譯主體性研究才開始受到重視,一些學者選擇主體性的視角進行翻譯對比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學的領域。學術界主要圍繞譯者主體性的內(nèi)涵和翻譯主體的界定進行探討。
關于誰是翻譯主體的問題,許鈞(2003:10)總結(jié)出4種觀點:“一是認為譯者是翻譯主體,二是認為原作者與譯者是翻譯主體,三是認為譯者與讀者是翻譯主體,四是認為原作者、譯者與讀者均為翻譯主體。”筆者認為譯者作為翻譯活動中貫穿始終的決定者,應是翻譯主體,但是在翻譯過程中需要考慮原作者的行文風格、目的和讀者的需要。
關于譯者主體性的內(nèi)涵,仲偉合和周靜(2006)嘗試對譯者主體性的內(nèi)涵做出總結(jié):譯者主體性是指在尊重客觀翻譯環(huán)境的前提下,在充分認識和理解譯入語文化需求的基礎上,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主觀能動性,它體現(xiàn)了譯者在語言操作、文化特質(zhì)、藝術創(chuàng)造、美學標準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覺意識,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chuàng)造性、受動性等特點。而譯者主體性可能會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可以具體到譯者的文化先結(jié)構、譯者的雙語文化能力、原作者以及文本選擇對譯者的影響、譯者的詮釋空間、譯文接受者等等。
3 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
《中國哲學簡史》在20世紀80年代由馮友蘭的學生涂又光翻譯為中文版本,由北大出版社發(fā)行,成為學術界的暢銷書,又于2003年經(jīng)由趙復三翻譯,目前市場上大部分版本都是采用的趙復三譯本,但是讀者對這兩個版本的評價褒貶不一。這兩個譯者都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具有良好的中英雙語能力和中國文化的背景,但是他們本身的哲學素養(yǎng)并不一樣,采用的翻譯策略也不同。兩位譯者都宣稱采取了直譯的翻譯方法,但是兩個譯本的內(nèi)容和風格大相徑庭,都體現(xiàn)出譯者各自的風格。下面將從幾個方面對比兩本譯著中譯者主體性的體現(xiàn)。
3.1 譯者的雙語文化能力
哲學翻譯中涉及了許多專業(yè)術語,復雜概念,而如何把哲學文本翻譯地地道,能夠讓目標讀者清楚地理解原文意思,并不容易。這需要譯者的非凡的雙語能力和對哲學的透徹理解。
涂又光于1927年生于河南光山塾師之家,從小學習中國文化,1949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文學院哲學系,在先秦儒學、楚國哲學史以及中國教育哲學研究上頗有建樹。作為馮友蘭的學生,涂又光在馮友蘭去世之后,整理其所有中、英文遺稿,編纂成14卷馮友蘭《三松堂全集》。涂又光個人曾著有《楚國哲學史》、《中國高等教育史論》、《文明本土化與大學》等。
趙復三1926年生于上海,是中國基督教“三自宣言”的發(fā)起人之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被聘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與趙樸初、趙紫宸合稱中國宗教學者的“三趙”。從事中外思想、文化、宗教史的研究,已出版學術專著和譯作多部。翻譯作品有《西方文化史》、《西方思想史》、《中國哲學史》。
從兩位譯者的介紹來看,涂又光和趙復三年齡相仿,都出生于20世紀20年代,那時社會動蕩,中國又處于變革時期,而兩位都受過高等教育,為社會主義和新中國的建設付出了一己之力,也為中國哲學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從他們的履歷來看,兩位的雙語文化能力和哲學造詣都很高。但是涂又光系統(tǒng)接受過哲學高等教育,又是馮友蘭的弟子,對馮友蘭的思想了如指掌,而趙復三主要從事的是宗教的研究,從這方面看,涂又光在哲學方面的造詣更勝一籌。在本文所研究的翻譯實例當中,可明確判定為翻譯錯誤的,只在涂譯本發(fā)現(xiàn)了13句共17處,遠遠少于趙譯本中的38句共42處(常國華,2018)。雖然兩位譯者都有誤譯的地方,但是明顯趙復三的錯誤更多一些。
例1:Absolute Freedom and Absolute Happiness
趙譯:終極的自由與快樂
涂譯:絕對的自由和絕對的幸福
在原文中,“絕對的自由與幸福”是與“相對的自由與幸福”對比闡釋的,只有超越萬物的限制才能得到絕對的幸福,在有限的范圍里只能得到有限的幸福。從哲學的角度來說,沒有絕對的絕對,因為宇宙是無限的,其中的未知因素占據(jù)了絕大部分。而終極指的是事物發(fā)展的端點狀態(tài),終極幸福也就是幸福的最終狀態(tài)。但是幸福是無限的,沒有限制,也就沒有最高點之說。所以此處趙復三的翻譯偏離了原文。
3.2 原作者以及文本選擇
根據(jù)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介紹,《中國哲學簡史》是馮友蘭親自指導翻譯并認可的唯一版本(常國華, 2018)。新出版方新世界出版社與《簡史》原譯者涂又光先生洽談沒有成功,轉(zhuǎn)而通過馮友蘭先生之女宗璞(原名馮鐘璞)(1928-)聯(lián)系到趙復三,委托其重新翻譯。兩年之后,趙復三翻譯完成,于2004 年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該出版合同到期后,后浪出版咨詢(北京)有限責任公司與宗璞在 2008 年簽署了趙譯本《簡史》的版權協(xié)議,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鐘華,2004)。
涂又光編纂和翻譯過馮友蘭的很多作品,比較了解原文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作品風格,他在哲學史的研究上頗有建樹,翻譯這本書與他自己的專業(yè)比較貼切,能夠更好地把握原文的寫作意圖,領會作者的表達。而趙復三是受到出版社的委托后才進行翻譯的,他對于哲學領域的翻譯不是很了解,這種被動選擇限制了譯者翻譯能力的發(fā)揮,有些地方?jīng)]有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并且出現(xiàn)誤譯。
例2:Tao is the “Uncarved Block”(pu),which is simplicity itself.There is nothing that can be simpler than the unnamable Tao.
趙譯:道就是“樸”之最,因為它連名字也沒有(《道德經(jīng)》第三十七章稱道是“無名之樸”)。
涂譯:“道”就是“璞”(“Uncarved Block”,未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樸”。沒有比無名的“道”更“樸”的東西。
原文在“璞”“Uncarved Block”后面標注了其拼音,是想體現(xiàn)“Uncarved Block”與“simplicity”的音與義對應關系。“璞”指的是未雕琢的玉,也是“樸”的諧音,就是簡樸的意思,涂譯正確傳達了原文的意思。而趙譯沒有翻譯出作者的原意,只是把這兩句話意譯了。
3.3 譯文接受者
涂譯的第一個版本里寫到“這本書由馮友蘭的學生涂又光翻譯過來,旨在作為教授和學習中學哲學史讀者的一本參考書”,可見涂又光譯文的目標讀者為有哲學背景和知識的學者,所以他的譯文僅僅是把很多原典譯成了文言文,沒有增加解釋,哲學術語也是照搬了過來,用語比較簡潔,即便這樣讀者也能夠理解。而趙復三譯文的目標讀者為大眾,所以他把原典回譯成文言文之后,增加了很多自己的解釋,用語更加通俗易懂和流暢,易于讀者理解,這也是很多讀者更偏好趙譯的原因。
例3:For example, one of his contemporaries said:“Great Indeed is the Master Kung! His learning is so extensive that he cannot be called by a single name.”(Analects,IX,2.)
趙譯:《論語·子罕》篇記載,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意思是說,達巷黨這地方有人說,孔子是個偉大人物,學問廣博,以至很難用某一方面的專長來概括他的成就。)
涂譯:例如,有一個與他同時的人說:“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
從例句來看,趙譯把孔子的同時代人翻譯為達巷黨人,也就是這句文言文的原話,并且附上了這句文言文的意思,使讀者能夠更好的理解。而涂譯是直譯了出來。
3.4 譯者的詮釋空間
20世紀80年代,涂又光首次將此書譯成中文,這個時期譯者主體性的概念才剛剛引入中國,譯者的地位開始受到重視。在此之前,譯者只是兩種語言轉(zhuǎn)換的一個媒介,是一個隱形人。而到了2000年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對翻譯主體和譯者主體性等概念進行界定,強調(diào)了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和主觀能動性,譯者的地位越來越高。譯者的詮釋空間說到底是一個“度”的問題。譯者詮釋原作的空間是有限的,譯者的最大詮釋空間被限制在原作框架之內(nèi),受到原作者創(chuàng)作背景、上下文語境的影響,不能天馬行空地任意發(fā)揮。畢竟譯者是“帶著鐐銬的舞者”,必然也必須考慮到“鐐銬”的束縛(仲偉合,周靜,2006)。受到當時學術背景的影響,為了增加翻譯的美感和流暢度,趙譯比涂譯發(fā)揮了更大的創(chuàng)造性,但是趙復三對于原文隨意增減,并且多處增加自己的理解,超出了對于原文詮釋空間的限制。
例4: Hence,judging from the nature of the works of these writers, this practice, as we shall see later, did not indicate any misunderstanding or distortion of Buddhism, but rather a synthesis of Indian Buddhism with Taoism, leading to the foundation of a Chinese form of Buddhism.
趙譯:它實際是對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國道家思想進行一種綜合的努力,由此而為中國佛學奠定了基礎。
涂譯:所以從這些著作的內(nèi)容來判斷,作者們繼續(xù)使用道家術語,并沒有造成對佛學的誤解或曲解,倒是造成印度佛學與道家哲學的綜合,導致中國形式的佛學的建立。
趙譯沒有翻譯這句話的前半部分,其中這句話的主語“this practice”指的是“使用道家術語”,趙譯也沒有翻譯出來,只是使用了一個代詞“它”,指代不是很清晰。趙譯無故出現(xiàn)多次隨意刪減和增加自己理解的情況,這就超出了對于原文詮釋空間的限制。涂譯雖然是直譯了出來,但是用詞不是很準確,“導致”和“造成”常用于不好的結(jié)果,而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融合不具有消極色彩,中國佛學的建立也不是消極的結(jié)果。
3.5 譯者主體性在翻譯策略選擇中的體現(xiàn)
兩位譯者都宣稱自己運用了直譯的翻譯策略,趙復三在譯后記中說“翻譯外文書刊,大概詩歌、哲學兩類著作最費斟酌。這兩類著作如果依循原著,逐字逐詞按字義翻譯,應不是十分困難;難的是在翻譯這兩類著作時,不能只滿足于形似,還要求其傳神”。傳神多用于中國畫中,指生動逼真地刻畫出人物或物的神情。可見趙復三并不滿足于僅僅把原文的意思轉(zhuǎn)換過來,還力求傳達原文的韻味。而涂又光幾乎是逐字逐句翻譯過來的,對于原著的句式幾乎沒有改動。
例5:It was not until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re arose two men, Han Yu (768-824)and Li Ao(died c.844), who really tried to reinterpret such works as the TA Hsueh or Great Learning and Chung Yung or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such a way as would answer the problems of their time.
趙譯:一直到唐中葉以后,韓愈(公元七六八至八二四年)和李翱(公元八四四年卒)才對《大學》和《中庸》作出新的解釋來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問題。
涂譯:直到唐代的后半葉,才出了兩個人,韓愈(768-824)與李翱(約844年卒),他們做出了真正的努力,為了回答他們當代的問題而重新解釋《大學》、《中庸》。
兩位譯者都采用了直譯的方法去呈現(xiàn)原文,但是涂譯完全是逐字逐句翻譯過來的,翻譯腔很重,而趙譯則酌情刪去了“出現(xiàn)了兩個人”和“做出了努力”這兩句沒有必要的翻譯,按照中文的習慣轉(zhuǎn)換句式。這樣的句式在文本中出現(xiàn)了多次,趙譯更流暢一些。
兩個譯本各有優(yōu)劣,涂譯的策略主要為直譯和異化。而趙譯的策略主要為直譯加意譯和歸化。這對于哲學翻譯也提供了一些啟發(fā),哲學翻譯應當以直譯為主,但是直譯并不是僅追求字對字的翻譯,應該發(fā)揮一定的譯者主體性,在準確傳遞原文意思的前提下,盡量做到通俗易懂和流暢。
4 結(jié)語
《中國哲學簡史》譯本旨在普及中國哲學和文化知識,但是通過讀者評價發(fā)現(xiàn),由于缺乏系統(tǒng)中國哲學知識,當代很多年輕人都覺得此書深奧難懂,這更加強調(diào)了翻譯的作用。作為讀者和原文的中介,譯者應該在準確傳達原文意思的基礎上,使其通俗易懂。本文從譯者的雙語文化能力、文本選擇、譯文接受者、譯者的詮釋空間和不同的翻譯策略角度對比了兩位譯者譯文的異同,發(fā)現(xiàn)涂又光的哲學背景更勝一籌,但是他的翻譯追求字對字的翻譯,喪失了一定的流暢性。趙復三的翻譯可讀性更高一些,但是又喪失了一定的忠實度。因此,譯者在翻譯前應評估自己的雙語文化能力和翻譯風格,考慮譯文接受者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翻譯策略,避免超出詮釋空間的限制,出版社也應從上述角度考慮去委托合適的譯者。
參考文獻
[1]常國華.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兩種中譯本翻譯策略與實踐研究[D].安慶師范大學,2018.
[2]馮友蘭著,趙復三譯.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3]馮友蘭著,涂又光譯.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4]馮友蘭著,涂又光譯.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5]傅張萌.從譯者主體性角度看《中國哲學簡史》的漢譯[J].海外英語,2012(13):167-168.
[6]聶家偉.《中國哲學簡史》兩個中譯本簡要對比[J].福建江夏學院學報,2018,8(02):95-104.
[7]許鈞.“創(chuàng)造性叛逆”和翻譯主體性的確立[J].中國翻譯,2003(01):8-13.
[8]葉紹丹.《中國哲學簡史》(節(jié)選)英譯中翻譯報告[D].南昌大學,2014.
[9]張瑞華.簡評《中國哲學簡史》中的哲學翻譯觀[J].中原工學院學報,2015,26(05):109-112.
[10]鐘華.有多少書可以重出?[N].科學時報,2004-4-15.
[11]仲偉合,周靜.譯者的極限與底線——試論譯者主體性與譯者的天職[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07):42-46.
作者簡介
張芒(1974-),女,陜西三原人,西安外國語大學旅游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翻譯學和語言學研究。
趙亞捷(1995-),女,漢族,山西臨汾人,西安外國語大學旅游學院翻譯學專業(yè)2018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譯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