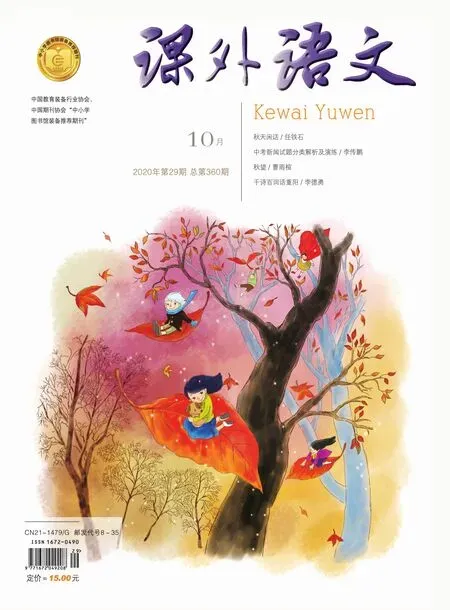千詩百詞話重陽
⊙李德勇(江蘇省連云港市崗埠電視臺)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從王維這首膾炙人口的重陽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可以看出,重陽節這一天在唐代是非常受重視的,而且人們有登高、插茱萸的習俗。而通過眾多古代文人騷客的詩詞,也可看出重陽節在古代的盛況和重要性。
重陽節登高插茱萸
重九起源甚早,舊以陰歷九月初九日為重九,南朝梁王筠詩:“重九唯嘉節,抱一應無貞。”又古以九為陽數,故又稱重陽。魏文帝《九日與鐘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故曰重陽。”而重九登高,最早見《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這段記述,雖近乎神話,但在那水旱的古代,居民有登高避災之舉,自亦頗合情理。
其時道家勢力遍及民間,曾倡議:“茱萸為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假此二物,以免陽九之厄。”(見道家古書所載)由是俗尚所趨,歷代相沿。
唯考諸古人登高行事,不獨九月九日為然。據《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登高賦詩。”《陔余叢考》亦云:“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于此可知,人日與上元日皆有登高之舉,不過,習俗相循,仍以重九登高,為人所重視,至今不廢。

登高遠眺吟九日
登高原為尋樂,當秋高氣爽,登高遠眺,逸興飛,才不辜負佳節。因之,古來文人雅士,每于登高之時,吟詠志盛,迄今留下許多佳句,傳誦不衰。如錢起:“浮云瞑鳥飛將盡,始達青山新月前。”張繼:“萬迭銀山寒浪起,一行斜字早鴻來。”唐彥謙:“云靜南山紫翠浮,憑陵絕頂望悠悠。”朱灣:“水將天一色,云與我無心。”以上詩句,皆是重九登高時乘興吟詠的,真情實景,描繪得淋漓盡致,及今讀之,猶令人遐思弗已!
歷代的重九詩文,經文人學者一致認為:文以魏文帝《與鐘繇九日送菊花書》為最早;賦以宋傳亮《九月九日登凌器館》為最早;詩以陶淵明《九月閑居》及《己酉歲九月九日》詩為最早。陶淵明在詩文上,處處顯示向往自然,如《歸園田居》:“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以及《歸去來辭序》:“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從此開啟了田園派的詩歌,并被人稱為“隱逸詩人之宗”的詩,為唐代表文字。
陶淵明之后,南北朝的重九詩,竟一反陶的風格,如謝靈運、謝瞻、蕭子良、王儉、梁簡文帝、沈約、丘遲、任昉、庾肩吾、何遜、劉孝威、王修已等,幾乎等于同一版本,皆屬侍宴應制之作。直至江總《于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賦韻》一詩,方才打破了侍宴應制的格調。江詩云:“心逐南云逝,形隨北雁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登高賞菊酒重陽
重九登高、賞菊、飲酒,原屬應節雅事,尤其是古今詩人,每每一手握筆,一手執壺,總是離不開酒,何況值此重陽,沒有名釀,如何度此佳節?
唐代重九登高,頗為盛行,連皇家也登高賦詩飲酒。唐中宗《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詩,句云:“九日正乘秋,三杯興已周。”其興致之沈,可以想見。而杜牧描述重陽醉酒詩《九日齊山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違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暈。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還有詩云:“重陽酒百缸。”所謂“酒百缸”,或為詩人筆下夸張之辭,但詩人在重陽佳節,乘興不停地飲酒,醉醒后再飲,其酒量亦足驚人了。
杜甫《九日》詩云:“重陽獨酌林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另有句云:“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老杜抱病時,還要登高獨酌,那無病時,自然就要任情醉酒了。至于飲酒飲到醉醺醺地連歸途都辨認不清的也大有其人,詩人張諤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九日郊游》詩云:“秋天林下不知森,一種清游事已均。絳葉從朝飛著夜,黃花開日未成旬。城遠登高能幾日?茱萸凡作幾年新。”
滿城風雨近重陽
重陽,古有小重陽與展重陽之稱。因以重陽遇雨,無法登高,如不舉行,未免掃興,于是,延至翌日補行登高,故稱小重陽。倘使遇到連日風雨,未能成行,便乃延一星期或十日,至九月十五日或十九日補行登高,俗謂展重陽。
然而也有興趣特濃,冒雨登高,即景抒懷的,如潘大臨傳誦千古的獨句詩“滿城風雨近重陽”。潘大臨閑臥休息,忽聞楓林風雨之聲,一時詩興大發,正握筆題詠間,突被催租人騷擾,打斷詩興,只得此一句。徐泫《九日雨中》:“目極暫登臺上望,心遙長向夢中歸。”他鄉作客,心系故里,大有“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親”的感慨!唐代女詩人薛濤《九日遇雨》詩又云:“萬里驚飆朔氣深,江城蕭索晝陰陰。誰憐不得發山去,可惜寒花色似金。”亦可謂深諳雨中登高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