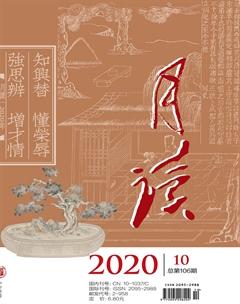《詞品》: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詞論專著
鐘岳文
南朝梁鐘嶸的《詩品》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理論批評專著(本刊2020年第2期“經典藏書”欄目已有專文介紹),它與同時代的《文心雕龍》堪稱“雙璧”。這部書以漢魏六朝的五言詩為評論對象,較為系統而又深入地評價了五言詩的作家和作品,其中體現出的詩學史觀、詩歌發生論、詩歌美學和批評方法論等都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我們常言詩詞,既然《詩品》是對詩歌理論的總結和評析,那么有沒有專門評論詞的專著呢?當然有,它就是明代楊慎的《詞品》。
一、詞學家楊慎
提到楊慎,我們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我們對《三國演義》的開篇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卻很熟悉。這首《臨江仙》正出白楊慎之手。
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今屬四川)人。他生活于明代中期,父親楊廷和是成化十四年(1478)進士,歷仕憲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內閣首輔,為一代重臣。楊慎自幼生活在仕途顯達、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里,十一歲便能作詩,十二歲擬作《吊古戰場文》《過秦論》,人皆驚為異才。大學士李東陽甚至讓其“受業門下”。楊慎的妻子也習詩通史,擅長詞曲,很有才隋。
正德二年(1507),楊慎科舉鄉試第一;正德六年殿試拔得頭籌,獲得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參與編修《武宗實錄》。其秉性剛直,事必直書。在武宗微服出居庸關時,楊慎上書勸諫,體現了一位忠臣的職守。明世宗繼位后,任翰林院修撰兼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廷臣“議大禮”,楊慎等三十六人上言直諫,因而觸怒世宗,被杖責罷官,謫戍云南永昌衛。楊慎居滇三十余年,曾率家奴助平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的叛亂。其間,他還往來舊朋,結交新學,教授生徒,尋幽探勝,一時傳為佳話。比如,他與舊友張含、李元陽、王廷表、簡紹芳、張佳胤等談論詩作,鑒賞文字;與新朋董難、葉瑞、葉泰、章懋等悠游山水,詩酒唱和。這種交游與學術活動,促進了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也為云南地區文化的繁榮做出了貢獻。嘉靖三十八年(1559),一代才子楊慎卒于永昌衛,享年七十二。隆慶初,追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謚文憲。
楊慎一生以博學著稱于世,他是明代三才子之一(另兩位是解縉和徐渭),而且是三才子之首,可見其文學造詣之深。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六中說“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用修”。《明史·楊慎傳》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余種,并行于世”。其詩文作品主要見于《升庵集》八十一卷和《遺集》二十六卷。存詩兩千三百余首,其詩雄渾蘊藉,綺麗雅致,沈德潛《明詩別裁集》評價說:“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絕麗之學,隨題賦形,一空依傍,于李(夢陽)、何(景明)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著述則涉及經學、哲學、史學、考古學、音韻學、文獻學、文學等多個領域。其詞學著作也十分豐富,詞集有《升庵長短句》三卷、《升庵長短句續集》三卷,詞選有《詞林萬選》《百琲明珠》《填詞選格》等,評點過《草堂詩余》,有詞論專著《詞品》六卷,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楊慎的詞學創作及詞學理論均對中國詞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他也成為集作詞、論詞、選詞、評詞于一身的著名詞學家,甚至有“詞家功臣”之譽。
二、《詞品》的主要內容
《詞品》為一部通代詞學論著,論析范圍從六朝訖于明代。這部著作撰寫于楊慎被貶云南期間,一般認為成書于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首次刊行于嘉靖三十三年。
今天所見的《詞品》共六卷,拾遺一卷,“拾遺”卷后附有陳秋帆據函海本所補四則。六卷基本按照時代順序布局:卷一多記六朝樂府曲詞,考證詞調來源,論述詞調與內容的關系,六朝樂府與詞體的用韻等。卷二以記述唐五代詞人詞作及閨閣、方外之作及故實為主,并解釋考證詞中出現的生僻字詞。卷三至卷六記述兩宋、元代及明代詞人詞作及故實。拾遺一卷多記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詞作及故實。《詞品》除了摘錄、引述他人的詞話外,共評論唐五代、宋、元詞人八十余人,涉及詞的源起、詞體特性、詞人故實、詞作品鑒、風格興寄、韻律字詞等眾多內容,在詞學史上具有較高的文獻與理論價值。李調元《雨村詞話序》評價此書說:“吾蜀升庵《詞品》,最為允當,勝弁州之英雄欺人十倍。”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也對此書給予了很高評價:“論列詩余,頗具知人論世之概,不獨引據博洽而已。其引據處,亦足正俗本之誤。……其他辨訂,淵該綜核,終非陳耀文、胡應麟輩所可仰而攻也。”
說到書名,我們知道,南朝梁鐘嶸《詩品》的“品”字,主要是“定品第”之義,因為作者對每位作家都定了品第,繼而以上、中、下三品品詩。唐代司空圖撰有《二十四詩品》,把詩歌分為24種不同的風格。縱觀楊慎《詞品》一書的內容,作者似乎沒有為詞的高下進行分品的意思,書名中的“品”字,更多的還是品評之意,還有揭示詞品與人品關系的用意。楊慎通過對歷代詞人詞作的品評,發表了自己對詞體諸多方面的看法。
《詞品》對詞學發展的貢獻
《詞品》全書有選有評,評述結合,比勘錯脫,具有較高的詞學價值。書中所涉及的理論較多,而且頗多精辟言論,足以啟發后人。
首先,倡導“詞源于六朝”,對詞的緣起進行了研究。
在中國詞學史上,關于詞的起源問題有不少探討,也產生了幾種不同的認識和看法,如源于《詩經》說,源于樂府說等。而楊慎在《詞品序》中開門見山地說:“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詞之體已具矣。”意在指出詞源于六朝時期。其實,南宋朱弁在《曲洧舊聞》中已經提及:“詞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濫觴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陳后主有《玉樹后庭花》,隋煬帝有《夜飲朝眠曲》。豈獨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吳越之錢俶,以工小詞為能文哉。”但是,朱弁只是說了自己的結論,卻沒有用事實加以考證。真正能結合六朝文學事跡而做細致考究的人,非楊慎莫屬。
我們看楊慎所列六朝諸篇,其實都是詩,它們與后世真正意義上的由樂定詞、依曲定體的詞體尚有很大差異。不過,這些詩在句式、結構、韻律和格調等方面已經與詞有相似之處。比如陶弘景的《寒夜怨》:“夜云生。夜鴻驚。凄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月樂府作日。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這首詩抒發了閨閣相思之情,屬于雜言體詩。但它用的是長短句,句式參差錯落,從形式上看的確與詞有—定的相似之處。另外,這首詩情致柔婉,與后世的詞特別是婉約詞具有相似的情趣、格調和氣韻。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楊慎在《詞品》的卷一、卷二中選錄了大量六朝及唐五代人的作品,較為細致地考察了這些作品與后世詞體的關聯。其中,多數內容又屬于詞與六朝文學關系的范疇。楊慎不僅認為詞之源在六朝,而且提出“大率六朝人詩,風華情致,若作長短句,即是詞也。……予論填詞必溯六朝,亦昔人窮探黃河源之意也”。
楊慎從詞調緣起、句式變化、故實紀傳、詩詞關系、韻律形式、字源詞典、風華情致等方面詳加考敘,對詞的歷史與發展進行了總結,這對于提高詞的地位、促進詞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也使我們對詞的演進脈絡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和理解。近代王國維《戲曲考源》也講:“詩余之興,齊梁小樂府先之。”
其次,考釋詞調,解讀詞體的演進過程。
詞調(或稱詞牌)是符合某一曲調的歌詞形式,是詞有別于詩的最重要的形式特征。每一個詞調都有其特定的內涵和體式要求,如調名、分闋、句式、韻律等。《詞品》對詞調的來源、表現形式和內容等進行了大量考釋,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比如關于詞調的來源,楊慎認為多來自古人詩句以及魏晉唐人的史志、筆記、小說甚至佛典等。《詞品》卷一中專有《詞名多取詩句》這個標題,其中說:“《蝶戀花》則取梁元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蝸‘春游雞鹿塞,家在鷓鴣天。《惜余春》則取太白賦語(按:李白《惜余春賦》有‘愛芳草兮如剪,惜余春之將闌)。《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按: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有‘浣花溪里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按:東漢張衡《四愁詩》中‘四思日: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霧霧,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菩薩蠻》,西域婦髻也。《蘇幕遮》,西域婦帽也……”
我們讀詞的時候,會有一個好奇心,就是詞牌的名稱是如何定下來的,或者出處在哪。《詞品》中的這一則可稱為“詞牌名小百科”,把主要詞牌的來源出處一一列出,使我們的疑惑頓時消解。
詞牌名稱之外,《詞品》對于詞調與內容的關系也多有推衍和揭示。楊慎認為唐代詞調多與詞作的內容相一致。如李后主《搗練子》“即詠搗練,乃唐詞本體也”,王晉卿《人月圓》“即詠元宵,猶是唐人之意”,“《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不過,詞調的來源和產生又是比較復雜的,并不是每一個詞調和所詠內容之間都存在必然的關聯。因此,楊慎又論析了“借腔別詠”的問題。如《干荷葉》本該詠荷,但劉秉忠卻用此調寫出吊宋之作,楊慎認為“此借腔別詠,后世詞例也”。楊慎的考論符合詞體創作的演進過程,對于探討詞體的承續與發展軌跡具有積極意義。
第三,尊隋抑理,推崇詞的本質特征。
楊慎所處的時代,正是理學統治文壇,復古之風大盛的時代,而他卻能獨立于這些思潮之外,不受其影響,在《詞品》中旗幟鮮明地贊美人之“情”,確實難能可貴。
詞是一種長于抒情的文學樣式,因此宋明理學興起之后,詞總是受到理學家的貶斥。因為在他們看來,“情”也就是欲,這與他們所尊崇的“天理”不相容。他們宣揚“情之溺人也甚于水”,認為情有害,必須根除。理學家這種把“情”簡單等同于欲,而要求禁絕的主張嚴重違背了文學發展的規律。古人說“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緣情而綺靡”,這些都是不刊之論,沒有感情的文學作品必然是蒼白的,沒有魅力的。
明代中后期,社會文化思潮開始對理學反撥,文人們也開始不遺余力地倡導尊情論。明代戲曲理論家沈際飛就提出:“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認為“情”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楊慎生活的時代比他們要早,當時尊隋論在文壇還未成氣候,因此《詞品》對“情”的禮贊可說是明代較早出現的尊情論,雖然不及晚明諸論令人有石破天驚之感,卻是獨具只眼,識見不凡,因而屢被后世論詞者所稱引。
《詞品》卷三“韓范二公詞”條引用了韓琦的《點絳唇》和范仲淹的《御街行》兩首詞,并就詞中的“情致”進行發揮:“二公一時熏德重望,而詞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已。宋儒云禪家有為絕欲之說者,欲之所以益熾也。道家有為忘情之說者,情之所以益蕩也。圣賢但云寡欲養心,約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嘗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雖戲語亦有理也。”清人王弈清編《歷代詞話》以及馮金伯所編《詞苑萃編》都收錄此條,僅略有刪節而已。可見人們對于楊慎詞學觀點的認同。
第四,既強調詞人的品行,又重視詞人的學識。
詞一般具有很強的娛樂性,因此被人視為“小道”。楊慎則認為,作詞者既需要高尚的品行,也要有深厚的學識素養。
《詞品》卷二“曹元寵梅詞”條就批評曹元寵(曹組)蹈襲蘇軾詞,并對此人的人品進行了抨擊和指斥。文中說:“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蘇句,其所謂掩耳盜鈴者。噫,奸臣丑正惡直,徒為勞爾。”曹組是宋徽宗時期的文學侍臣,而且是“近幸之臣”;楊慎鄙薄曹組的為人,因此對他有“掩耳盜鈴”“奸臣丑正惡直”的評價。而對于那些有氣節、品德高尚的詞家,楊慎則極力推許,褒揚有加。比如評價張元斡說:“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綱詞得罪,忠義流也。”張元斡詞有英雄之氣、悲憤之情,因此即使詞雖不工,“亦當傳”,“宜表出之”。由此顯示了楊慎對詞人品行的重視。
品行之外,楊慎對詞人的學識也多有強調。如《詞品》卷一“歐蘇詞用《選》語”記載:“填詞雖于文為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亦不能入妙。”認為詞人應多研讀《文選》《樂府詩集》等古代典籍,斟酌古語,取其精華,以此來增長才識,使詞作臻于妙境。楊慎認為,胸懷萬卷書是“填詞最工”的基礎。《詞品》中對蘇軾、秦觀、辛棄疾等人詞作中的用典、用韻乃至用語情況都進行了大量考論。
最后,兼容婉約與豪放二派。
明代雖有少數人對豪放詞進行了贊揚,但總的來說,明代詞風以輕綺側艷為主。詞論方面,也崇尚所謂的“香弱”,而貶斥豪放。《詞品》對豪放詞的看法,與同時代大多數人的論調有所不同,這是楊慎獨立于時代風潮之外,憑借自己的深入思考而持有的一個觀點。
“香弱”一詞,是明代王世貞提出的,是他對詞體基本特征的概括。清人沈曾植對“香弱”一詞又作了評價,意思是說“香弱”二字是明人所推崇的藝術風格。明人排斥豪放詞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明人論詞,也多以婉約為正宗,以豪放為別格。張綖就提出:“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大抵詞體以婉約為正,故東坡稱少游今之詞手,后山評東坡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總的來說,在楊慎生活的時代,論詞的傾向是崇婉約而抑豪放的。楊慎本人的詞作也常流于淺俗,屬于“香弱”一路,未能擺脫時代風氣的影響。但他論詞卻比張綖等人通達大度,并不囿于門戶之見,更不會“黨同伐異”,而是兼容不同風格的作品。
對于豪放派詞人蘇軾和辛棄疾,楊慎雖未直接評價,但他在評詞時,常以蘇、辛作為標的。如《詞品》卷五“岳珂《祝英臺》詞”先寫了岳珂北固亭《祝英臺近》的填詞,繼而說道:“此詞感慨忠憤,與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詞相伯仲。”《詞品》中還有對其他豪放詞的評價,如評鄧千江《望海潮》“繁縟雄壯”,評劉克莊“送陳子華帥真州”詞(《賀新郎·送陳真州子華》)為“莊語亦可起懦”,即嚴正的議論也可以振發軟弱無能者的豪氣。可以說,楊慎對豪放詞的肯定是毫無保留的。《詞品》中對豪放詞進行肯定的條目數量之多,是同時代其他詞論著作所不及。而楊慎的分析、評點全面透徹,也是同時代其他詞論家所不及的。
在稱贊豪放詞的同時,楊慎也肯定了婉約詞的長處。楊慎于婉約派詞人中,特別贊賞周邦彥。《詞品》評姜夔詞說:“詞極精妙,不減清真樂府。其間高處有周美成不能及者。”這就是以周邦彥為標的論詞,同時肯定了姜詞有勝過周詞的地方。
在當時詞壇推崇婉約詞的情形下,楊慎能夠從詞的本質和藝術角度出發,對豪放詞做了積極的評價,實在是相當通達的。他對豪放、婉約兼容并收的觀點,以及對蘇、辛詞的肯定,對詞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雖然他的觀點在當時并未引起強烈反響(這應該與其當時被貶謫的境遇有關),但對后人論詞無疑有著很大啟發。清代許多著名詞論家均認為婉約、豪放二派不可偏廢,楊慎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詞品》選讀
李易安詞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于閨閣也。其詞名《漱玉集》,尋之未得。《聲聲慢》一詞,最為婉妙。其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荃翁張端義《貴耳集》云:此詞首下十四個疊字,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下十四個疊字者。乃用《文選》諸賦格。“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此“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又“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四疊字又無斧痕,婦人中有此,殆間氣也。晚年自南渡后,懷京洛舊事,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后疊云:“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言語,度入音律。煉句精巧則易,平淡人妙者難。山谷所謂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卷二)
李易安詞
宋人填詞,李易安遠遠超出他人。假使她是縉紳,當與秦觀、黃庭堅爭雄,而不僅僅是女子中最杰出的。其詞名《漱玉集》,我尋找它沒有得到。《聲聲慢》一詞,最為婉轉優美。其詞言:“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荃翁張端義《貴耳集》言:這首詞首句下十四個疊字,是公孫大娘舞劍的手法。本朝不是沒有擅長寫詞之人,但未曾有句首下十四個疊字的。這是采用了《文選》中一些賦的手法。“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這個“黑”字沒有第二個人能押的了。又“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連用四個疊字又毫不造作,女子中有這樣的,大概是間氣(舊說英雄豪杰上應星象,稟天地特殊之氣,間世而出,稱為間氣)。晚年自南渡以后,懷想京城舊事,賦詠元宵《永遇樂》詞言:“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經工巧精致。至于“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韻和風格更好。后疊言:“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都用普通的言語,選取合適的音律。推敲詞句使之精巧是容易的,但運用平淡詞句而能達到神妙之境就難了。山谷所謂的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易安先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