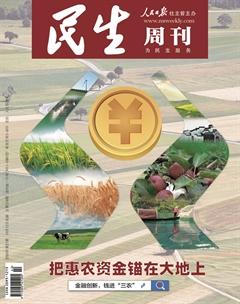我們需要怎樣的農信社?
鄭智維

作為我國農村金融的主力軍,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在支持地方經濟、扶持農業發展、緩解中小企業資金困難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有數據顯示,我國目前共有4607家銀行機構,農商行有1478家,還有722家農信社,兩者加起來占據了銀行系統的半壁江山。
如何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農村信用社如何才能發揮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如何更好地服務于鄉村振興?
對此,長期在農信社系統工作的申厚(化名)有著深入的思考:“要更好地服務于鄉村振興,農村信用社改革依然需要深化,當務之急是管理體制亟待理順。”
隱憂頻現
“名義上是獨立的法人單位,是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縣級農商銀行的管理體制則完全不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模式。”申厚說。
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是股東大會,公司的管理、監督機構是由股東代表大會選舉出的董事會、監事會,再由董事會選舉董事長,最后由董事會提名、聘任經營管理層的行長、副行長等。
現實情況是,各級農商行的董事長、行長、監事長、副行長等的產生是先由省聯社指定人選,再由農商行按照所謂程序選舉確認的。
作為出資人的股東,在公司的組織架構和經營管理中卻毫無發言權。
“無論日常經營,還是重大事項,銀行的實際管理者均不會主動向出資人通報。經營好壞、存在問題大小,出資人無法了解,更談不上對公司的監督。”申厚說。
讓申厚感到擔憂的是,封閉的運行體系,缺乏有效監督,容易滋生腐敗。
“失去約束的權力,勢必造成腐敗,特別是手握強大資源的金融企業,包括省聯社和各級農商行屢屢曝出相關問題。”
在此背景下,一些更為嚴重的隱性問題難以避免。早在數年前,申厚就注意到壞賬率居高不下。2016年末至2017年末,貴陽農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由4.13%突升至19.54%,河南修武農商銀行由4.5%升至20.74%,山東鄒平農商銀行則由2.43%增至9.28%。
“越改越行政化了”
談及問題的根源,申厚認為,現行的管理體制與農商行自身發展不協調、不匹配。
“真正的出資人無法選出代表自身利益的管理人員,省聯社與農商行股東權力和利益之間始終是一對很難調和的矛盾。”
2004年前后,各地陸續成立了縣一級統一法人單位的縣聯社。由省域內各家縣級聯社出資入股成立,省聯社的職能起初被定位為協調、指導、服務各縣級聯社。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省聯社職能逐漸演變為對縣級聯社進行領導與管理。
如今,省聯社為縣級聯社的上級行政管理部門。2005年后,全國陸續出現了由縣級農信聯社改制成的農商銀行,但其由省聯社領導和管理的模式并沒有變。
按照有關規定,縣級聯社改制成農商銀行,其法人地位不變,實行的是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自我約束的公司治理結構。
由于省聯社的強勢介入,上述公司治理結構形同虛設。
“省政府將省聯社當作一個全省統一法人主體進行追責,即無論轄內哪一級農商行(農信社)出了問題,都要由省聯社負責處理,問題嚴重的,則要追究省聯社的領導責任。”申厚說。
該機制倒逼省聯社將自身職能轉變為對轄內農商行的行政領導與管理。
“現行體制下,省聯社的管理寬嚴皆誤。管理寬松,沒有權威性,經營者隨意作為,甚至恣意妄為;管理嚴格,又容易出現層層造假。”申厚說。
談及10多年的省聯社去行政化改革,申厚評價說:“省聯社對農商行的約束和管理越來越嚴,對農商行的人、財、物的控制也就越來越緊。越改越行政化,改革走向了上級要求的相反方向。”
可能的改革方向
“和城商行一樣,實行省級農商行一級法人管理體制,各市、縣則變為分行或支行,省級農商行由省政府出資控股,取消行政級別。”申厚提出。
其優勢是,上下一體,政令暢通,便于管理,且防控風險能力較強。
然而,這與當下的改革方向要求相違背。有專家分析,當下的改革,不愿意讓縣級農商行失去法人地位,主要是擔心農商行不再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
“這種擔心并無必要。”在申厚看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農商銀行深耕“三農”、支小支微的動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其他市場已被別的金融機構占領,農商銀行勢必會堅守農村市場這個主陣地。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農村金融市場會越來越活、越來越大。
申厚提出另一個改革思路:省聯社徹底退出行政管理角色,回歸到服務職能上來。“省聯社要加大科技研發,強化科技支撐,充分發揮平臺作用,對農商行真正起到協調、指導、服務的職能,實行對農商行的有償服務。”
其優勢是,管理體制得以理順,最大限度地發揮投資人的監督管理作用,地方監管機構則要肩負起強監管、嚴監管的職能。同時,這種改革思路也符合中央的現行政策:農商行的縣域法人主體地位不變。當然也有其問題,單個農商行的抗風險能力較弱。
“就當前來看,每種改革方向都有其優劣。”申厚說,“先不要爭論對錯,對錯要在實踐中檢驗,不妨先從試點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