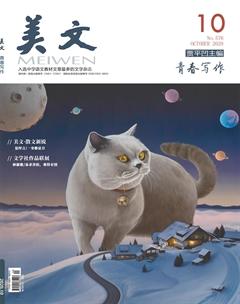你當在書里百煉成鋼
朱思穎
讀書是藉智者之眼觀究世界肌理的哲學,而哲學(philosophy)在古希臘文中的本義正是“愛智”。對智慧的愛慕孕育了人們經由書籍對知識孜孜以求的近乎浪漫的酒神精神,也同樣使冷靜且追求秩序的阿波羅在讀之有道、習之有方的人們身上“顯靈”。
而當我在與人類璀璨群星的凝眸中越來越清晰地看見一個青澀者修煉出沉穩(wěn)妥帖的氣息時,我開始漸漸明白讀書的過程終其本質就是對“解構”二字的演練——對前賢珠玉文章進行思維解釋和融合,化外在知識為內在知識,是為“解”;從瓦詞石句起家搭建私我新屋,將己之理解訴諸表達,法見為新的外在知識,是為“構”。而細究“解構”,就當以三昧真火烹之燒之,從而拾階而上,直抵智慧深處。
真火其一:知其字確,聽其音美
讀書當有“形—音—意”的三維視域。
速讀,泛讀得多了,讀得太流熟,一目十行, “讀不知字”? 其實是會心虛的。文章由字或句搭建,因此,讀書首先要“識其字”,逐字逐句地讀出它的所有文字,完整地讀準每個句子,“不知為不知”,用簡單、安靜、素樸的態(tài)度,安分到在紙面或屏幕的字典上慎重端正地會晤新字,其實是一件令人肅然起敬的事。
象形抑或字母,文字皆鏗然有聲。《楚辭》里有“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的楚地獷調;宋詞里有“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的金石之聲;阿城的小說于短促、白樸中見力度;周曉楓的散文在繁復曲折的音樂游戲中驚心動魄;西方古典作家則精于在悲喜劇的對話中刻畫人類的輾轉悲欣。“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從見形到聽音,從單維到二維,亙古與寥遠的情感形諸音韻,令我們了悟字字珠璣的審美愉悅,更讓我們察思感受力的細膩厚腴。
真火其二:直譯入書,意譯入己
準確理解文意,當避免不求甚解、“舊瓶裝新酒”式的曲解原意。詞句的多義性、文章的連貫性和語言的歷史性都決定著舊瓶只能裝著忠于作者原意的佳釀老酒。“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要讀出以梅自喻、一語雙關的凜然正氣;“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要小心斷章取義的慣性陷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入時入人,了明所謂“愚民政策”的時代之音。如此入幽察微,方可稱于“解”道上愈精愈熟。
然而,聞樂要聞“弦外之音”,聽話要聽“言下之意”,讀書也要讀“文外之書”。由直譯獲得的未經思維加工的知識,難免泥沙俱下、雜質橫陳,經由觀照自我的省察和與他人雙向的釋疑解惑 ,讀者才能去蕪存菁,去偽存真,覺悟出新觀點與新見解,從一個篇章中同時得到堪稱真知灼見的“原意”與“啟迪 ”,如此便是對原文的“意譯”,亦是“學以致用” 從“學”到“用”的轉折點 。
真火其三:以文化人,發(fā)人未發(fā)
康德“心中的道德律”直指讀書旨歸——學得文化,習得道德。知識內化為素質再外化為行動,是我們“以文教化”自己,而當我們運用自身的人格力量、知識素養(yǎng)來影響別人,就是我們“以文教化”他人。
令人玄思之處在于教化乃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教化他人的同時,我們也會根據(jù)他人的反應來審視、檢驗和修正自己的行為,完成對自身的“再教化”。內外相長,互促互進,相得益彰,如此還原讀書本義,使自身的道德素質日益臻進。
“聞一以知三”,在文字中讀懂原意,讀會啟迪,更要讀出新篇,才能到達“發(fā)人所未發(fā)”這一“構”的最高階。讀有所得,思有所悟,博聞強識,是為構建自我知識體系打下根基。將所吸收的知識融會貫通,藉由寫作、創(chuàng)新,寓讀于寫,讀寫相長,進行“化內構新”,卻是讓我們牢牢掌握了學以致用中用的關鍵方面,讓我們相信自己有能力表達不凡的思想,超越卑微與瑣屑的漩渦,來使得全人類的知識圣殿異彩紛呈。
作為歷史上所有愛書者最可靠的間接經驗來源,書籍讓我們習得微縮宇宙與俯瞰人類的飛鳥視域,讓我們感悟思想的歷久彌新的光芒,在由外而內再由內而外的“譯、化、發(fā)”的解構中,人類可以知曉學習使人智慧,人因此而獲得永不可摧毀的自尊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