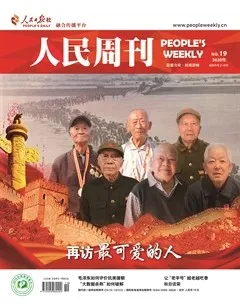雙循環格局下城鎮化發展新動能在哪
鄭新鈺
“2019年底,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0.6%,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進城就業生活的人數還將繼續上升。”在近日于北京召開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0”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推進城鎮化工作辦公室綜合組組長吳越濤表示,城鎮將成為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重要載體空間。
當城鎮化發展進入新階段,其道路也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尤其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如何激發城鎮化新動能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城鎮化是補齊城市短板的重要抓手
據了解,目前,我國城鎮化率每年平均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這就相當于每年有1000萬人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
雖然我國城鎮化率已突破60%,但學界普遍認為,城鎮化的動力依然強勁。
“從2019年來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是7.1%。與此相對應,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就達25.1%。”吳越濤說。
對于農民工來說,“市民化”后可以享受高質量的教育、醫療、養老和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幸福感、安全感和獲得感都能得到顯著提升。那么對于城市來說,農民進城又有怎樣的意義?
“促進農業轉移人口進城就業,必將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住房等方面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吳越濤說,我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人均資本存量相當于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20%—30%。這表明,城鎮化是補齊當前突出短板弱項的重要抓手。
吳越濤認為,通過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特別是加強補齊公共衛生短板,以及防水防澇設施等弱項,能提升各級城市和城鎮的綜合承載能力。
完善戶籍制度改革機制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近年來,我國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消費需求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給出了一組數據:目前我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GDP總量占世界的16.3%,但是我國最終消費只占世界的12.1%。從這個數據中可以看出,我國消費潛力還需進一步被激活。
消費潛力從哪里挖掘?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保持了居民收入和GDP的同步增長,且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高于城市居民。
“我國有40%的人住在農村,但是他們在居民消費中只占22%。”在蔡昉看來,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是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60.6%指的是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近16個百分點。
蔡昉認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統計了所有的外出農民工,但如果這些人沒有城市戶口,也就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由于他們收入不穩定且就業也不穩定,加之沒有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務,這就抑制了他們的消費。

“有研究表明,如果把農民工戶籍轉化為城鎮戶口,即使工資沒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費。”蔡昉提醒,“就地變更戶籍身份”無法帶來實際效應,新型城鎮化落腳點應該著眼于進入到城市的農民工。
雖然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收益有目共睹,但不容回避的是,改革仍存在較大障礙。
對此,蔡昉認為其原因在于,對于地方政府來講,要支付戶籍制度改革成本,卻不能獲得全部改革收益。面對困局,他建議,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要對改革成本和收益作出明確安排。
打破農業要素不匹配狀態提升農業回報率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表示,在“十四五”期間,我國新型城鎮化工作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鄉村問題上。
劉守英認為,我國快速城鎮化階段出現的一大反常現象是,農業回報率非常低,主要農產品的農業利潤率呈下降趨勢。
“我們的農業類別比較單一,農產品成本上升,產業融合層次低,導致整個鄉村的功能價值被窄化。”劉守英說,“從上一輪中國城鎮化的經驗來看,如果農業沒有找到出路,城市可能又要回到農村。所以在城鄉融合的階段必須找出農業發展的出路。”
中國海外控股集團黨委副書記、副總裁許均華也持有同樣觀點。他認為,在農業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之前,新型城鎮化不能以削弱農業的基礎為代價。
“如果沒有強大的農業,城鎮化就會有后顧之憂。”劉守英說,對于目前而言,重大的理念變化就是農業工業化的過程,在“十四五”期間要解決整個農業回報率上升的問題。
此外,劉守英表示,實現農業現代化還要注重改變當下農業要素,即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利用不經濟的現狀。制度變革是推動農業產業革命的力量,要通過制度變革打破要素不匹配的狀態。
關于農業的規模經營,蔡昉認為,不充分的戶籍制度改革也會制約農業規模經營。“必須讓勞動力比較徹底地轉移出去,才能擴大規模,提高農業效率,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蔡昉說。
(《中國城市報》202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