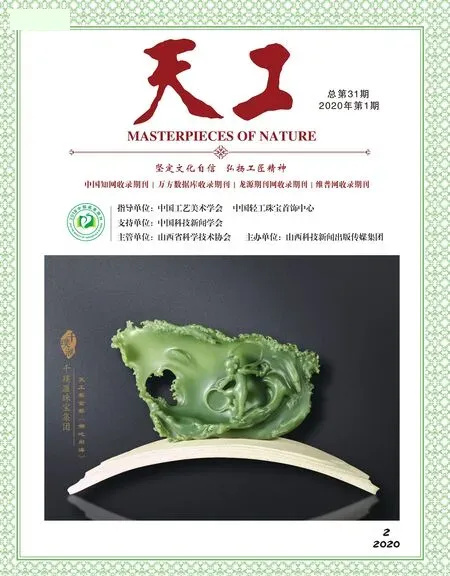牌匾立體雕刻法角度探索
文 邵學軍
一、古人制作牌匾的局限性
1.古人沒有X 光學儀器,無法了解人體“眼球結構”,無法證明所看到物體的正確直視點、最佳焦點范圍度和“余光”的最大限度。
2.古人沒有照相機,不知道照片中的物體會有空間立體感。所以,在繪畫中,無法將平面紙張上的物體“立體”起來。同樣,古人在牌匾雕刻中,對雕刻的深度、角度“不得法”,完全憑師傅個人感覺進行,造成雕刻出來的字“死板、扁平”,視覺效果差。(見圖1、圖2、圖3)
3.古人對“雕刻角度”認識水平普遍偏低,肉眼“看不出問題來”。而當代雕刻者,有繪畫基礎,嚴格訓練過繪畫當中的“一點透視”法,知道物體的透視、比例、結構以及體積感、重量感、空間立體感。我們用現代科學知識掌握的技能,面對古人平視的“散點透視”雕刻法,自然得心應手。牌匾不僅要從正面看,還要從左、右、上、下、中五個方向看,不僅是看到字本身,還要能感受到“活靈活現”的動感。
二、牌匾雕刻時“陽刻”與“陰刻”
雕刻時,對于牌匾陽刻的“凸鼓”,究竟凸多少才算凸呢?對于陰刻,究竟凹進去多少才對呢?筆者反復試驗了十幾年,不斷改進刀法,終于獲得訣竅:人體120°視覺 “立體雕刻法”。
透視學所講的“平行透視,成角透視”,科學地告訴我們“一點透視法”①“一點透視法”,就如相機鏡頭里看到的物體“近大遠小”。而“散點透視”則是古人在國畫中,想在哪里作為視點就在哪里畫一座山幾座房子,完全是按心理需求隨意發揮,根本無透視關系,而古人雕刻時也如此操作。在視平線上的視點、消失點,同時也告訴我們人的視野范圍在90°~120°為最佳。
根據這個原理,得出牌匾雕刻角度的要素:
1.雕刻字的筆畫,視野角度大于120°,就屬于人眼視野余光范圍,在這個角度雕刻的字,視覺效果就“扁平”不立體,因此決不能超過這個范圍。
2.視野角度小于110°的字就“瘦窄”,而小于100°,視覺上就更瘦小。古人刻牌匾時即會有這樣的誤差:不是大于120°,就是小于100°。

圖1 視線與成像角度范圍

圖2 人視野角度范圍

圖3 最佳視野角度與余光范圍
三、從業中的突破與發現
筆者在實際操作中發現其中奧秘,又反復實踐,得出最終結論:
1.“凹型”字雕刻角度,必須控制在110°~120°之間。再依據書法字的筆畫輕重,寬窄肥瘦,在“一點透視法”的角度范圍內靈活調整,深度隨著起伏變化而變化,將二維平面創作為有深度空間的三維立體感。
牌匾懸掛起來時,字形處處清晰,字的各個受光面充分均勻,讓人在不同角度看起來,都有呼之欲出的強烈立體感。
這一重大突破,糾正了古人“散點平視”雕刻缺陷,填補了千百年牌匾史空白。(見圖4)
2.“半球形凸鼓”字。由于它是沿著字的輪廓線,一邊向下刻,一邊逐漸將字“留”出筆畫的凸鼓形,在左右上下觀看字時,木板表面輪廓就遮擋了一側部分筆畫,甚至另一側半邊看不到,造成筆畫“瘦細”,好像字被縮水的感覺。
因此,在字本身的輪廓線之外,還要根據字大小,向外擴一條附加輪廓線,也就是另外增加一個斜角,這個斜角,就是保證左右看時,必須一眼看到字底本身輪廓線。換句話,就是筆畫凸鼓處,與附加輪廓線要形成一個夾角。
古人的夾角太大了,再加上筆畫最高處,基本是木板本身的平面,因而顯得非常死板。而筆者將夾角嚴格控制在120°以內,同時,筆畫的弧線與半球形吻合,最高處是飽滿的“滿弓”半球形。(見圖5)
這個半球形,不是圓規劃出的,也不是尖三角,而是類似于射箭的“滿弓”。這個飽滿度,正是多年反復試驗出來的“120°弧線合體”。當牌匾懸掛起來觀看時,立刻出現了“活靈活現”的感覺。
牌匾雕刻看似簡單,卻蘊含了歷史文化和歷代匠人的心血。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代,我們理應運用科學,使這項古老技藝發揚光大,科學傳承。

圖4

圖5

圖7 陰刻

陰刻字,字形絲毫不走樣,又由于字里的凹面完全能看到,各個反光面交相輝映,在近處看是凹的,越遠看越凸鼓,使人產生撲朔迷離的陰陽交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