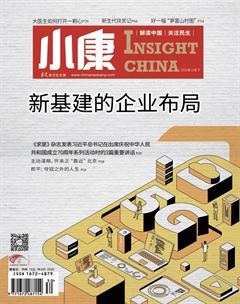董然:用心打開一顆心
郭玲

“每一顆心臟都是獨一無二的,有的肥胖,有的苗條;有的厚實,有的纖瘦;有的跳得快,有的跳得慢。沒有兩顆心臟是相同的。我經手過12000顆心臟,它們大多病得厲害,搞得患者精神苦惱,胸部劇痛,總是疲倦,還會有程度可怕的喘不過氣。”英國著名心臟外科醫生斯蒂芬·韋斯塔比所著的《打開一顆心》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這是每一個心臟外科醫生都擁有的經歷與感受,甚至有些習以為常。但是,對每一位患者來說,卻是生命中艱難而重要的時刻。
作為全國心臟外科領域的佼佼者,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臟外科中心收治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病患,他們在這里等待治愈、康復甚至“重生”。心臟外科主任董然,每一天都在這里見證著這種治愈、康復甚至“重生”,從醫以來,他經手過的心臟超過16000顆,而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以心相托”是他的動力
無影燈下的手術臺上,躺著一位年過六旬的男子,時針指向午夜12點,董然和他的同事們正在竭盡全力挽救男子的生命。就在一周前,這位患者在外地的醫院植入了心臟支架,沒想到,術后一周發生了心臟破裂。急救車奔馳上百公里,將他緊急送到安貞醫院,入院時已是心源性休克,情況危急。董然深知這種情況不能等,于是連夜進行手術,為病人“修補心臟”,歷時6小時,手術終于結束,患者進入監護室。董然才發現,天已經亮了,又是一個不眠之夜。
“心外病房每一周都有驚心動魄的時刻,每一次手術都可能是驚險的挑戰,時刻不能松懈。”安貞醫院心臟外科中心第十一病區主任辦公室里,董然坐在我們對面,平和地講述著發生在幾天前的故事,那一夜的緊張,只有他和他的同事知道。
桌子上沏好的茶早就涼了,從早上到中午,董然都沒來得及喝上一口。采訪當天是第三個中國醫師節,董然的這個節日和平日沒有任何差別,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手機里收到很多祝福短信,但是他并沒有時間細細閱讀。早上7點半進醫院門;7點半到9點,查房;9點到9點半,到重癥監護室查看剛剛做完手術的病人病情;10點,到手術室完成一臺手術;直到中午12:50左右回到辦公室接受我們的采訪。病區當天一共7臺手術,除了需要親自完成的,董然還要隨時關注其他醫生的手術,為他們提供指導與意見。
心臟外科,是外科領域各分支中較年輕的一個學科,主要是以手術治療心臟病,如心臟搭橋術、先天性心臟病手術、瓣膜置換術等。所治療的常見心臟病包括先天性心臟病、瓣膜性心臟病、冠心病、胸主動脈瘤、心包疾病、心臟腫瘤等。
近十幾年,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走進醫院做手術的人多了,心臟外科的手術量增加迅猛。“很多七八十歲的冠心病患者,過去在這個年齡很少再做這種手術,但是目前做得很普遍。”董然說。
在全國的心臟外科中,北京阜外醫院排名第一,安貞醫院排名第二。作為全國心臟外科領域的佼佼者,安貞醫院心臟外科中心收治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病患。董然所在的心臟外科中心第十一病區,負責全科室60位病人的診療與手術,而他,正是這一病區的負責人。“我們一個病區60個床位,去年手術量達到1837例,單病房手術量全國第一。”
董然的病人中,年齡最大的90歲,最小的20歲。董然查房過程中,常會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屬拉著他的手,跟他說“董主任,我就把命交給您了”。病人的“以心相托”“以命相托”,是心臟外科醫生的壓力和動力。
另一個擺在心臟外科醫生面前的現實是:兇險的手術越來越多,董然稱其為“病人越做越困難”。“過去在心臟內科做完冠狀動脈造影,適合放支架就放支架,不適合放支架就送到心外。現在,隨著支架技術的發展進步,很多病人的病癥都可以在心臟內科解決了,送到心臟外科的,都是非常兇險的狀況,要么手術非常緊急,要么病人身體差,要么心臟功能已經衰竭,這都意味著手術難度很大。”
“打開心臟是心臟外科大夫的入門手藝,也是標準動作。這是一項高難度、高風險的職業操作,具有決定生死的神奇轉圜意義。”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王一方在為《打開一顆心》作序時如此寫道。
一顆破了的心到底是什么樣子?董然形容那很像血豆腐,非常脆弱,必須及時將破口縫合,否則這顆心的主人就會因此送命。從醫以來,董然一共打開過16000顆心臟,他的一雙手,曾經一次次拯救病人于危難。
勇敢面對手術的“兩面”
知乎上有人評論,心外手術是“最帥的手術”,因為那是“刀光劍影中的妙手仁心”。董然深以為然。
不同于其他很多手術,心臟外科需要非常強大的團隊協作。一般需要三到四個手術醫生、一個巡回護士、一個器械護士、兩個麻醉醫生、兩個體外循環醫生,近十個人通力協作去完成一臺手術,拯救一位病人。“沒有團隊協作,再優秀的醫生也沒有辦法獨自完成。”
一位心臟外科醫生的成長與成熟需要漫長的積累過程。因為只有讀到醫學博士才有資格進入醫院,這就意味著已經30歲,他的職業生涯才剛剛開始。此后循著住院醫生、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這樣一條職業發展生涯走下去,成為手術中的關鍵人物——主刀醫生,至少需要十年的時間。十年磨一劍,一些人通過努力成為主刀醫生,另一些人則止步于此,與主刀醫生無緣。“我認為,那種所謂的帥,是時間磨出的奇跡,其實,心外醫生,甚至醫生這個行業,是個很殘酷的選擇。”
在這個殘酷的職業選擇中,董然無疑是成功的,是脫穎而出的。
他與醫學結緣,是因為哥哥。董然還在上高中的時候,他的哥哥就考上了醫學院。受到哥哥影響的董然,同樣走進了醫學的大門,成為眾多醫者中的一員。從山東醫科大學畢業后,他從住院醫生、住院總醫生做到主治醫生,此后做到副主任醫師、主任醫師,成為這一領域的專家。
在董然看來,心臟外科的手術,除了考驗醫生的手之外,還更考驗腦。“手的操作重要,更重要的是治療的思路,決斷的能力,長期依靠臨床治療積累的經驗。”針對每一個病人,董然都要帶領團隊為他們量身定制手術方案,因為每一顆心都不一樣,每一個病人的病情都有其特殊性。
面對病人或者家屬的一些不理解,董然覺得,家屬有困惑或疑慮是正常的。“他們不是胡鬧,而是不懂,他不了解你要干什么。”因此,手術前的手術風險,醫生都會給家人和病人詳細交代。董然曾經遇到一位心衰病人,當時沒有任何癥狀,從北京站可以自己走到安貞醫院,結果在病床上等待手術的時候猝死了。“這種情況其實是過度的代償導致的,這是我們從專業角度來解釋的,但是病人家屬看到的就是人好好地走進醫院,結果卻死掉了。”
“手術室本是非常之地,既是解除病痛的地方,也是咀嚼苦難和孤獨、遙望生死的地方;既是追求生命希望的地方,也是體驗悲劇與悲情,思考生存意義的地方。”
一顆心臟的打開,就像硬幣的兩面,一面是希望,一面是失望。作為醫生,董然經歷過眾多拯救病人的喜悅,也經歷過一些遺憾。“作為醫生,我不能因此而不前,因為還有很多病人需要我去救治。”在董然看來,醫生的另一個意義,就是面對。不論此前經歷了什么,只要走進手術室,就需要全心全意去面對眼前這個生命。
在董然的從醫生涯中,做過的最長的一臺手術,前后超過34小時。手術中,病人心臟中的血管幾乎全換了。“那應該是2009年,我剛剛從國外回來,就做了這樣一臺手術。雖然說是34小時,但是感覺時間過得很快,上臺以后覺不出累,下臺才覺得腰酸背痛。”那臺出奇漫長的手術有一個非常好的結果:病人被救活,并健康地出院。“病人當時也就40多歲,如果沒有其他的意外,他現在一定活得很健康。”說這話時,對面的董然,語氣更溫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