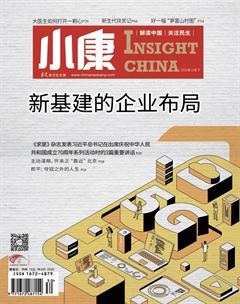《掬水月在手》:演繹弱德之美
馬春靚

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10月16日開啟全球公映,其主題內容、人物設定與拍攝手法的平靜感,在喧囂的大眾娛樂中仿佛一股清流涌向觀眾的視線,讓觀眾對女性美的認知范疇、人生價值與意義等方面有了重新的思考。
女人的美該如何定義
紀錄片《掬水月在手》拓寬了大眾對女性美的認知范疇。同樣是記錄成功女性主題的作品,很多影視劇作品或綜藝節目通過炫目的燈光、震撼的音響、跌宕起伏的劇情和華麗的場景等豐富的創作手段,讓觀眾目不暇接,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仿佛擁有無限力量的女性形象,她們學表演、能經商、事業與家庭兼顧……擊垮困難、勇往直前、無所畏懼、無所不能。但這部文學紀錄片《掬水月在手》的主角是一位年近百歲的女人,在96年的歲月中,她面臨生活的困惑與不幸,卻秉持著一種平靜、淡定與從容的處世態度。在特殊的年代,她不畏生活的艱辛和環境的惡劣,不辭辛苦地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輾轉,孜孜不倦地傳播中國古典詩詞、弘揚民族文化。電影中沒有使用絢爛而復雜的藝術手段,幾個場景、幾段音樂、幾種自然風景將影片主人公自創的名詞——“弱德之美”進行了演繹與闡釋。“弱德之美”就像中國武術中太極的以柔克剛、以弱勝強,用平靜迎接巨浪,正如影片中無處不在地彰顯出一種默默的承受與堅強。
同樣是女性的主題,乘風破浪的迅猛與弱德之美的平靜產生了鮮明的反差與對比,在乘風破浪的喧囂之后,弱德之美的平靜卻讓人震撼與難以忘懷。這種震撼是劇中人物以一種平靜淡定的姿態面對人生重大創傷后,還保持一種自謙、高尚的品格,云淡風輕般地對待人生的種種苦難。這種精神是對女性主題的重新書寫與全新定義,即在外界的強壓下,如何默默地承受痛苦,并堅持內心的高尚與操守,不張揚、不放棄。這種精神在大多數現代人看來仿佛是一個生活上的弱者,處處妥協、永不反抗。但當我們看到劇中主人公在自己的學術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時,又讓人由衷地敬佩。劇中的主人公是葉嘉瑩(號迦陵),1924年7月出生于北京的一個書香世家,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加拿大籍中國古典文學專家,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曾任臺灣大學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并受聘為國內多所大學客座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名譽研究員。影片中先后通過采訪鏡頭與寫意畫面進行配合的方式講述了主人公婚后遠離故鄉、與夫分離、政變被捕、女兒去世等苦難經歷,這與她所取得的事業上的成就形成極大的反差。也因此,讓觀眾體會到女人可以擁有的另一種品質——“弱德之美”的深刻含義。
在這里,華麗的“乘風破浪”仿佛與當今社會快速發展的節奏一樣,是一首動感的交響樂,給觀眾帶來了聽覺與視覺的沖擊力,讓人有一種饕餮盛宴后的滿足感和力量感;而“弱德之美”卻像一首經典的鋼琴曲,看似單一,卻飽含著直抵人心的震撼與共鳴,使人在平靜與安寧中品味其中的美妙,帶給我們的回甘也會有一絲獨特與不同。
弱德之美的兩層含義
紀錄片《掬水月在手》是對另一種人生經驗的觸摸,對女性的社會價值與意義進行了寫意式的表達。西方哲學家齊澤克認為:事件是不可預計發生的東西。它會打破原有的秩序,并生成新的事物。事件擁有終結現在、消滅現在的能力。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中,導演用灰蒙蒙的城市、荷花池中枯萎的蓮蓬、被殘雪包圍的神像和水泥墻邊的一顆孤零零的小草等形象對主人公坎坷的人生遭遇進行了寫意式的呈現,其中講述了背井離鄉、與愛人分離、女兒去世等事件,而主人公內心的孤獨、凄涼、寂寞也通過電影的形象,特別是在低沉的背景音樂的襯托下傳遞給觀影者。但在每組凄涼的畫面之后,出現的是面容慈祥、語氣平靜的主人公形象,在影片中,她就像在講述別人的故事一樣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歷。低沉的畫面和輕松的對話在這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讓觀影者看到了一位平靜、溫和的學者和詩人。影片中的主人公用一種超乎常人的理性回溯性地講述人生的遭遇,這讓我們看到了弱德之美的第一層含義,即理性直面事件的勇氣。這種理性,不僅體現在主人公的生平當中,在電影的制作上,也采用了這樣的理性視角。影片中,以整體的灰色調的畫面配合單色的老照片、土黃色的草原、雪花飄落的場景,靜靜地轉化,并在中間穿插了留白。這些習以為常的自然物、天氣、照片和低沉的音樂構成了一種現實中不可抗拒的事件性,即殘酷的現實在電影的畫面中被呈現,任何人無法改變,只能默默地承受它的到來。藝術手段的簡單明了向我們呈現了事件不可抗拒的張力,更加凸顯出主人公超出常人的理性魅力,從而引發了“弱德之美”的第二層含義,即在事件發生后化悲傷為詩句的創造力。在這里,我把它稱為“生成情動的創造之美”,指的是當事件發生時,主人公沒有退縮與躲閃,直接面對事件,將內心悲傷、孤獨的情緒化為詩歌,字句之間都彰顯出驚心動魄的情感,而這種情感也通過主人公對詩歌反復的誦讀得到了消解,通過創作詩歌時對美好畫面的憧憬得到了安慰。因此,大多數人聽過主人公苦難的人生和看到她安靜且有些羞澀的外表時都會覺得驚嘆。我們能夠在電影中看到,每當主人公讀詩或詠詩的時候,是非常投入、開心的,似乎她的人生是沒有創傷且完美的。殊不知,這份寧靜與祥和是通過不斷創作詩句、記錄人生換來的,也正是這些經歷和情感令她成為蜚聲海內外的詩人和學者,從而使人生變得精彩紛呈,創造了韻味無窮的生命價值。詩中有我、我中有詩、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化悲痛為力量的樂觀的生活態度和以創作滋養人生的至高追求。

表達。《掬水月在手》采用寫意的拍攝手法,將導演對主人公的敬仰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用浪漫的鏡頭記錄與呈現。
無論怎樣都很美
德勒茲在《差異與重復》中提到,“每一個事物、每一個存在都應當看到自己的同一性被差異所吞沒,因為每一個事物、每一個存在都只是諸差異之間的一個差異”。差異是在對歷史的循壞與重復中產生,但重復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重復的過程中生成差異。差異消解了統一性與相似性,打破了傳統的定見,創生新的可能性。《掬水月在手》的主人公作為一名知識女性,她的人生在時間的車輪中跌宕起伏,但是她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是女性,就向命運低頭,或者因為是女性就重復前人的人生,而是在不斷的創作中尋找更好的自己。在電影的一開始,導演使用了仰拍平推拍攝壁畫的人物和文字,表達了一位教師、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敬仰。其中涵蓋了主人公專注于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態度與傳播中國古典詩詞的決心和艱辛的歷程。同時,鏡頭如流水般緩慢移動、一個水波紋緩緩地展開的畫面和鏡頭的留白,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外表柔弱、卻內心堅強的女人如何用詩歌書寫不凡的人生故事。《掬水月在手》沒有像傳統的紀錄片一樣,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客觀地記錄事件的發生,而是采用了寫意的拍攝手法,將導演對主人公的敬仰,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用浪漫的鏡頭將其記錄。盡管影片的內容大多描寫了主人公內心的凄涼與孤獨,但通過鏡頭,我們可以感受到影片的畫面宛如一張中國的山水畫,形式與內容相互襯托,時間與空間相互交錯,留白的鏡頭給觀眾無限的想象,從而將一種悲涼的美展現在觀眾的面前。
與此同時,紀錄片通過這些鏡頭和場景的拍攝,創造了一個在悲涼中尋找動力、用詩歌釋放內心情感和改變人生命運的知識女性形象。影片中出現大量的主人公創作的詩句,其中不僅凝聚了她的個人情感,也將人類共同存在的情感,或者說,將歷史變革給人類帶來的情感凝結在這些詩句當中,其中凝聚了集體的記憶與個人的情動。這種情動是內心深處原發的激情與沖動,就是德勒茲所提到的“差異的生成”的原動力。首先,差異的生成體現在劇中的主人公沒有被女性這個概念所限制,盡管從整體上來看,她的人生和其他的女人一樣,結婚、生子、工作。但當她面臨家庭變故時,她沒有像其他人那樣責備與埋怨,而是選擇默默地接受與面對。她的人生態度打破了傳統對女性的定見,沒有高昂的口號與標語,沒有喧囂的關注和掌聲,更沒有優越的環境與空間,她只是隱忍著內心的痛苦,在平靜中尋找可能,成就了不一樣的自己。影片中主人公平靜地面對人生的遭遇,不氣餒、不抱怨,從容地面對世界。其次,因情動而原發的創造力體現在主人公創作的詩歌和對詩歌的研究成為德勒茲所提到的“情動”的種子,將內心的真實的情感轉化為一首首美妙的詩篇,播撒在詩歌的土地上,生根發芽,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滋養出一片肥沃的土地,不僅記錄了歷史與時代,也為讀者的生活帶來了無限想象。而今年已96歲高齡的葉嘉瑩,還堅守在講授中國古典詩詞、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工作上,她的事跡創生了中國女性無論是社會價值還是人生意義上的新境界。
當乘風破浪遇見弱德之美,我們看到了人生的多種可能性。在大眾媒體異常火爆與迭代更新的今天,能在影院中看到以如此清澈與平靜的畫面來記錄一個時代人物的紀錄片,實在難得。影視劇作品對女性不同角度的描寫,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女性的包容,也彰顯了女人對高尚品德的追求與向往。女人既可以選擇乘風破浪,也可以追求弱德之美。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以從容淡定為文本立意,寫意的拍攝手段、簡約的記錄方式仿佛夏日里的一杯綠茶,需要細細品位,其中對人生的價值與意義的隱喻耐人回味與反思。與此同時,影片也警醒我們,在多種美并存的今天,女性應該拋棄對傳統女性的定義和偏見,嘗試擁有更多的選擇性。無論是乘風破浪,還是弱德強韌,我相信:總有一款適合你。